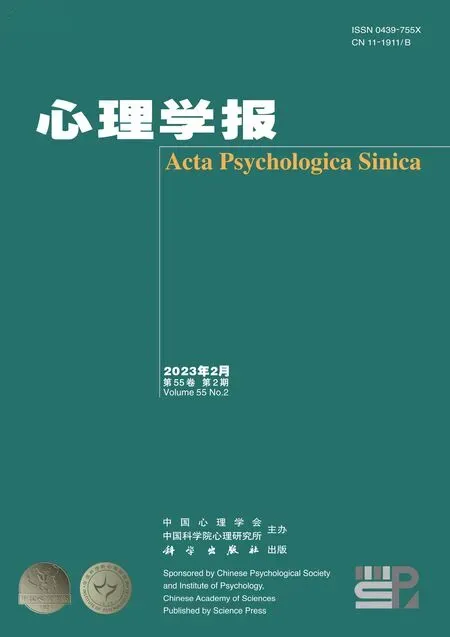情緒調節靈活性對負性情緒的影響:來自經驗取樣的證據*
王小琴 談雅菲 蒙 杰 劉 源 位東濤 楊文靜 邱 江
(1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認知與人格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重慶 400715) (2 浙江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金華 321004)(3 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武漢 430079) (4 廣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桂林 541004)
1 前言
情緒調節(Emotion Regulation,ER)是指個體根據調節目標并基于不同的調節策略改變自己或他人情緒的主觀體驗、生理反應及行為表現,從而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過程(Gross,1998)。成功的情緒調節對個體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同時情緒調節能力也被認為是不同精神疾病的保護因子,包括抑郁癥(Joormann & Quinn,2014)、躁狂癥(McGrogan et al.,2019)、廣泛性焦慮障礙(Thayer et al.,1996)和社會焦慮障礙(Werner et al.,2011)等。考慮到不同調節策略與心身健康及精神疾病之間的關系,早期學者強調策略具有固定的積極或消極的調節效果,并傾向將策略劃分為適應性策略(Adaptive ER strategies,例如:認知重評和問題解決)和非適應性策略(Maladaptive ER strategies,例如:沉浸和表達抑制) (Aldao et al.,2010;Aldao & Nolen-Hoeksema,2010)。近幾年,這一研究框架遭到質疑,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策略的調節效果在不同情境中并不存在一致的調節效應(Webb et al.,2012),如已有研究表明:認知重評能力(通過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或看待情境和自己的情緒來減少負面情緒)在不可控的生活壓力中與抑郁情緒呈顯著負相關,而在可控的生活壓力中與抑郁情緒呈顯著正相關(Troy et al.,2013);二是研究者強調情緒調節過程應該考慮不同調節策略與生活情境的交互作用,即情緒調節的效果依賴于特定策略和不同情境特征的匹配(Cheng et al.,2014)。綜上,情緒調節靈活性(Emotion Regulation Flexibility)是指個體根據不斷變化的情境需求靈活地部署調節策略的能力,也是衡量情緒調節能力個體差異的主要指標之一(Aldao et al.,2015;Bonanno & Burton,2013)。
以往研究情緒調節靈活性的方法包括平衡的策略庫剖面結構(Balanced profile)、跨情境變異程度(Cross-situational variability)、策略-情境匹配程度(Strategy-Situation Fit)和主觀報告的情緒調節靈活性等(Blanke et al.,2019;Wang et al.,2021;張少華 等,2017;王富賢 等,2016)。一項元分析結果表明基于策略-情境匹配程度和主觀報告兩種方式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和心身健康之間關系的效應量最大(Cheng et al.,2014)。考慮情緒調節靈活性強調了策略與情境之間的動態變化屬性,基于策略-情境匹配研究情緒調節靈活性相對上述其他研究方法更加客觀有效。本研究重點探討基于兩類策略使用程度(認知重評和分心)與情境負性程度匹配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對個體負性情緒的影響。
認知重評和分心策略作為兩種廣泛用于下調負性情緒的情緒調節策略(Gross,2002;Morawetz et al.,2017,2020),涉及不同水平的認知資源的卷入(Sheppes & Meiran,2008)。已有研究從行為、生理和神經層面證據表明,使用認知重評策略相對于其他策略(如分心和接受等)會產生更高的認知損耗、交感神經系統反應和更活躍的前額葉腦區激活
(Goldin et al.,2019;McRae et al.,2010;Sheppes et al.,2009)。大量研究基于策略選擇范式(ER choice paradigm)證實了個體傾向于在高負性情境中選擇分心策略,而在低負性情境中更傾向使用認知重評策略(Sheppes et al.,2011,2014)。潛在解釋有:認知重評策略涉及的認知改變過程需要較多認知資源卷入,可以產生持久的調節效果,因此在低負性情境中使用更具有優勢。分心策略通過無關刺激代替情境需要較低認知資源卷入,但只能維持短時的調節效果,因此在高負性情境中使用更具有優勢(Sheppes,2020)。已有研究基于情境負性程度的操控與兩類策略選擇(認知重評和分心)的匹配,測量個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并進一步發現個體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調節了消防員的創傷暴露程度和創傷應激障礙之間的關系(Levy-Gigi et al.,2016),并與不健康的代償行為(如過度運動和洗滌行為)有關(Dougherty et al.,2020)。以上研究證據一定程度表明基于情境負性程度與兩類策略(認知重評和分心)的匹配可以有效評估個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
情緒調節靈活性對于個體適應不斷變化的內部和外部環境是至關重要的(Kashdan & Rottenberg,2010;Sheppes,2020)。盡管上述研究基于策略選擇范式發現個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與不同的心身健康行為存在關聯,然而實驗室環境中基于圖片操作的高低負性程度不同于真實生活中的情況。其次,在現實生活中個體可能會嘗試使用不同策略,而不是完全僅采用單一的策略。因此,為了提高研究生態效度,本研究基于經驗取樣方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探討情境負性程度與兩類策略使用程度的共變程度以表征個體情緒調節靈活性,并進一步考察個體在不同負性程度的情境中靈活使用認知重評和分心策略是否與其負性情緒(抑郁和焦慮情緒)有關。經驗取樣法旨在減少由于長時間回憶帶來的記憶偏差,從而提高測量的生態效度。因此,對于日常情緒相關體驗的測量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并被認為在情緒調節靈活性研究領域具有一些獨特的優勢(Aldao et al.,2015;English & Eldesouky,2020)。首先,相比于實驗室研究測量情緒調節靈活性(Bonanno et al.,2004;Hay et al.,2015;Levy-Gigi et al.,2016;Orejuela-Dávila et al.,2019),基于經驗取樣法可以捕獲生活中豐富的生活情境。其次,豐富的時間點允許對情緒調節策略的動態屬性進行刻畫(Hollenstein et al.,2013;Ram & Gerstorf,2009)。因此,本研究利用經驗取樣方法來記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負性事件并評估其負性程度。此外,新冠肺炎(COVID-19)作為一個集體的重大創傷事件,給群眾的生活帶來一定程度的負性情緒體驗。在第二個樣本中采集了在新冠肺炎最嚴重時期(2020 年3 月7~13 日),生活在湖北省的隔離群眾日常負性情緒體驗程度和相關策略的使用程度。這一與疫情相關的生活背景對人們情緒經歷的影響已被大量研究證實。基于中國樣本的縱向研究結果,民眾在疫情時期確實比日常生活中體驗了更高水平的負性情緒(如抑郁、焦慮、擔心和恐懼等情緒) (He et al.,2021;Li et al.,2021)。由此可見,疫情這一特殊時期給個體的消極情緒體驗提供了充分不必要條件。所以本研究選擇疫情下的消極情緒作為情境負性程度的評估方式。進一步,本研究基于多水平模型擬合分心和認知重評兩類策略使用與情境負性程度在個體內水平的共變程度(斜率估計值),作為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的指標,然后通過跨層交互模型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對經驗取樣后個體負性情緒(抑郁和焦慮)的影響。
情緒調節靈活性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是該領域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其適應性通常是指情緒調節靈活性的調節效果與個體情緒健康之間的關系(張少華 等,2017)。以往研究表明心理僵化是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癥狀表現之一(Kashdan & Rottenberg,2010;Stange et al.,2017)。例如,他們在很多生活情境中都無差別地體驗空虛和無意義感,反映了對環境的不敏感性(Abramson et al.,1978;Buchwald et al.,1978;Telner & Singhal,1984)。其次,抑郁癥患者常用的情緒應對方式—沉浸,不僅反映了一種習慣性的循環思維模式,也代表著僵化的、不靈活的調節模式。抑郁個體難以從高強度負性刺激中解離可能意味著無法靈活地從沉浸的狀態切換到其他更有利于減少負性情緒的策略中(例如,分心),這種不靈活的行為模式可能會加劇抑郁情緒的強度(Kashdan & Rottenberg,2010;Koval et al.,2012;Rozanski & Kubzansky,2005;Stange et al.,2017)。臨床上不同亞型的焦慮障礙也表現出類似的情緒調節障礙,即傾向于使用某種單一的調節策略。例如廣泛性焦慮障礙(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的個體會過度擔心(Thayer et al.,1996),社交焦慮障礙的個體傾向于隱藏自己在社交情境中的感受或避免與社交情境相關的刺激(Heeren & McNally,2018;Hofmann & Bitran,2007;Schneier et al.,2011)。此外,焦慮情緒與注意力解離策略的偏好有關。采用注意解離的策略(回避或分心)以避免與情緒刺激接觸在前期可能對緩解焦慮情緒有幫助,但持久的注意解離會錯失克服焦慮情緒或解決問題的機會,無法根本上消除焦慮情緒(Campbell-Sill & Barlow,2007)。情緒調節靈活性強調了個體依據情境變化而靈活部署策略的能力,而抑郁和焦慮障礙個體對某一種特定策略的過度使用與適應不斷變化的情境需求是相矛盾的。因此,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過低,包括策略-情境不匹配以及單一僵化的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策略偏好)是引起高抑郁和焦慮情緒體驗的主要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對個體負性情緒的影響。在方法上,我們結合策略使用剖面結構和策略-情境匹配兩類方法,從靜態和動態的兩個角度評估個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首先用策略使用剖面結構評估個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假定個體在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疫情影響時有單一策略使用偏好,則表明其具有更低的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其負性情緒水平(焦慮或抑郁)相比具多個策略使用偏好的個體更高。其次,我們進一步基于不同情境特征(負性程度)與策略(認知重評和分心)的匹配程度評估個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我們提出假設:個體的情境負性程度-分心策略使用程度的共變程度(斜率估計值)要高于情境負性程度-認知重評策略使用程度的共變程度,表明其有更高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其抑郁和焦慮情緒水平更低。相反,如果個體的兩類策略使用程度與情境負性程度的共變程度比較呈相反趨勢,表明其有更低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其抑郁和焦慮情緒水平更高。
2 方法
2.1 被試及樣本
以往研究表明情緒調節靈活性和心理健康的回歸分析達到顯著性水平(0.05)時的效果量一般為0.12~0.32 (Cheng et al.,2014)。在樣本1 中,根據經驗取樣的設置確定每個被試的采集時間點(負性事件報告次數)不低于 7 次,采用 R 語言包“wp.crt2arm” (Zhang & Yuan,2018)計算樣本量,結果顯示若要達到0.8 的統計檢驗力(α=0.05)需要199 名被試。因此在西南大學一共招募了有213 名健康被試。樣本1 的采集時間為2019 年9 月份上旬。只提取在測量期間發生負性事件的時間點數據,其中2 名被試的負性事件數量不超過7 次,無法納入統計,因此剔除。最終提取211 名被試數據(117名女),平均年齡為19.80 ± 1.37 歲。在樣本2 中,首先確定每個被試的采集時間點不低于24次,采用R語言包“wp.crt2arm”計算樣本量,結果顯示若要達到0.8 的統計檢驗力(α=0.05)不低于108 名被試。樣本2 數據采集發生在新冠肺炎期間(COVID-19,2020 年3 月7~13 日),通過網絡招募了在湖北省居住的115 名被試,其中15 名被試因為完成度低(N=10,大于30%的數據缺失)和缺失其他重要變量數據(N=5)數據被剔除。最終有100 名被試數據(64名女性)納入統計分析。被試年齡范圍為18~26 歲,平均年齡為20.73 ± 1.87 歲。兩個樣本在招募初期通過問卷排除精神疾病患者以及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然后對達到要求的被試通過電話說明實驗內容和數據采集規則。所有被試在正式參加經驗取樣數據采集前簽訂了知情同意書。完成經驗取樣問卷之后被試需要填寫一份包含一系列情緒健康的調查問卷,最后實驗結束后獲得一定數量的報酬。
2.2 數據采集
2.2.1 經驗取樣程序
兩個樣本都是指導被試通過智能手機在問卷星平臺(https://www.wjx.cn/)上完成。樣本1 的經驗取樣基本設定為:每天5 次,連續持續10 天,問卷發布時間從上午10 點到晚上10 點。每兩次測試之間的最小時間間隔是120 分鐘。被試在每次接收到問卷填寫消息時被要求在20 分鐘內完成。被試需要完成50 次問卷(5 次每天,持續10 天)。為了讓錯過5 次以上的被試達到足夠的問卷填寫數量,我們將程序延長了3 天。因此讓16 名錯過5 次以上的被試達到最低限度的問卷填寫次數(35 次),161 名被試在額外的3 天完成了超過50 次問卷填寫。在經驗取樣的數據采集階段一共收集了11545 次數據。被試平均完成54.53 次(SD=5.41;范圍: 39~65)。被試完成50 次及以上測試被認為100%的完成率,平均完成率為98.1% (SD=0.04;范圍:78~100%)。
樣本2 的經驗取樣問卷基本設定為:每天填寫7 次,一共持續7 天。為了讓錯過7 次以上的被試達到足夠的問卷填寫數量,我們將程序延長了 3天。在經驗取樣的數據采集階段一共收集了3462次數據。被試平均完成34.21 次(SD=6.97;范圍:27~57)。被試完成49 次及以上測試被認為100%的完成率,平均完成率為70.33% (SD=0.133;范圍:55.10~100%)。問卷發布時間從上午9 點30 到晚上10:30。被試需在20 分鐘內完成每次測試,每兩次測試最小間隔時間為90 分鐘。
2.2.2 經驗取樣測試內容
樣本1 中使用的經驗取樣數據包括:1)填寫姓名和編號;2)評定是否發生負性生活事件以及負性程度評定(從0 到100;0 表示一點也不負性,100 表示極度負性);3)評定7 類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程度(從0 到100;0 表示完全沒有使用,100 表示一直在使用)。7 類情緒調節策略(包括分心、沉浸、認知重評、接受、表達抑制、情緒表達和社會分享)的選定基于被廣泛接受的情緒調節過程模型(Gross,1998,2015),分別反映了情緒調節過程模型不同階段的調節方式。具體而言,我們選擇了發生在注意部署階段的分心策略、發生在認知變化階段的認知重評和發生在反應修正階段的表達抑制。同時,我們也納入接受、情緒表達以及社會分享三個常見的調節策略(Flett et al.,2003;Forman et al.,2007;Vincke & Bolton,1994)。沉浸作為一種對負面情緒或負面事件的自我關注的調節策略也被包括在本項實驗中,因為這種策略被證明是重度抑郁癥患者的一種常見的應對方法(Cooney et al.,2010;Papageorgiou & Wells,2003)。樣本2 中使用的經驗取樣數據包括:1)填寫姓名和編號;2)評估當前積極消極情緒程度,情緒詞條選定依據來源于本土化修訂的積極消極情緒量表(PANAS) (Watson et al.,1988;邱林 等,2008)。其中平均的消極情緒用于評估情境的負性程度;樣本2 對PANAS 的評分方式進行了改良,即采用了0~100 評分方式。其原因在于考慮經驗取樣法需要被試在短時間內對多道題項進行評估,為了減少被試由于不同評分方式轉換付出額外的認知努力,我們將經驗取樣所涉及的測試內容評分方式均設置為0~100。其次,目前為止,基于經驗取樣法測量情緒條目的評分方式尚未達成一致,常用的評分方式包括:0~100、0~7、1~4和 1~5,其中 0~100 最為常用,詳見元分析(Dejonckheere et al.,2019;Houben et al.,2015);6)評定8 類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程度(包括:分心、沉浸、認知重評、接受、表達抑制、情緒表達、社會分享和問題解決) (從0 到100;0 表示完全沒有使用,100 表示一直在使用)。情緒調節策略的選定依據與樣本1 保持一致。考慮到以上策略均屬于情緒中心的策略,因此納入問題解決中心的策略。兩個樣本完整的經驗取樣內容請詳見網絡版附錄1。
本研究包括兩個主要分析:潛在剖面分析和多水平回歸模型。潛在剖面分析使用了兩個樣本中所有策略使用程度的數據。多水平回歸模型僅用到一部分數據,包括兩類策略使用程度(分心和認知重評)和情境的負性程度評估,詳細內容請見表1。在樣本1 中,情境的負性程度是通過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報告的生活事件的負性程度獲得;在樣本2 中,由于收集了居住在湖北省的群體在疫情關鍵時期(2020 年3 月7~13 日)的情緒狀態,情境的負性程度是通過積極消極情緒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Watson et al.,1988;邱林等,2008)中的消極情緒平均值所獲得。統計分析納入了所有時間點數據。在這部分分析中,僅關注使用了認知重評和分心策略的使用程度,并將這兩類策略編碼(認知重評=1;分心=2)以探討情境負性程度和策略類型的交互作用。

表1 多水平模型數據使用概況
2.2.3 測量問卷
貝克抑郁量表 兩個樣本中個體的抑郁情緒都通過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BDI-II)測量。該量表從認知、動機、情感和軀體癥狀等維度評估個體在過去一周內的抑郁情緒嚴重程度(Beck et al.,1996)。貝克抑郁量表一共包含21 個題項。被試對量表中的每個題項進行從0 到3 的4 點李克特量表評分,總分范圍為0 到63。分數越高表示更嚴重的抑郁傾向。在兩個本樣本中,該量表均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其克倫巴赫α 系數分別為0.93 和0.86。
貝克焦慮量表 在樣本1 中,個體的焦慮情緒采用貝克焦慮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該問卷一共包含 21 條項目,其中大部分條目與DSM-III-R 中診斷驚恐發作的標準一致。其中13個條目描述了生理的焦慮癥狀(如頭暈),5 個條目描述了認知方面的焦慮癥狀,3 個條目描述了生理和心理層面的癥狀(如恐慌)。被試對量表中的所有題項進行四點李克特量表評分(0 代表一點也沒有;3代表幾乎無法忍受)。總分范圍為0 到63,分數越高表示更嚴重的焦慮傾向。本樣本中,貝克焦慮量表的克倫巴赫α 系數為0.90,表明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狀態焦慮量表 在樣本2 中,個體的焦慮情緒采用斯皮爾伯格狀態焦慮量表(Spielberger State Anxiety Scale) (Spielberger,1971)。斯皮爾伯格狀態焦慮量表用于測量群體狀態性的焦慮程度。該量表有20 道題,讓被試根據過去一周時間的恐懼、緊張、憂慮和神經質的體驗或感受進行4 點評分,1表示“完全沒有”,2 表示“有些”,3 表示“中等程度”,4 表示“非常明顯”。得分越高,表明焦慮水平更嚴重。本樣本中,斯皮爾伯格狀態焦慮量表的克倫巴赫α 系數為0.94。
2.3 統計分析
潛在剖面分析 為了驗證個體對某一種特定策略的過度使用是否可用于評估個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并進一步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對個體負性情緒體驗的影響,本研究采用R 語言包“tidyLPA”在兩個樣本中進行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 (Rosenberg et al.,2018)。潛在剖面分析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聚類方式,這種方法根據觀察到的變量之間的相似性對個體進行分類,并且假設分類反映了潛在群體在變量上的異質性(Muthén,2004;Nylund et al.,2007)。該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探討是否存在僵化或靈活的情緒調節模式(Chesney & Gordon,2017;Dixon-Gordon et al.,2015;Lougheed&Hollenstein,2012)。本研究通過個體在多個策略(如分享、分心、認知重評、接受、沉浸、表達抑制、情緒表達、問題解決)的使用程度識別潛在的不同情緒調節組別。為了進一步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與個體負性情緒水平(抑郁和焦慮)的關系,我們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比較不同情緒調節組別在負性情緒水平(抑郁和焦慮)是否存在差異。
多水平回歸模型 由于兩個樣本數據均為嵌套結構,采用R 語言包“lme4” (Bates et al.,2015)擬合多水平混合線性模型,并用R 語言包“effectsize”估計模型中的效應量f2。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通過策略類型×情境負性程度的交互作用體現,如交互項系數(斜率估計值)為正,表明個體隨情境負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隨情境負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即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更高。如交互項系數(斜率估計值)為負,表明個體隨情境負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分心策略;隨情境負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即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更低。然后將負性情緒分別放在兩個模型的第二水平,通過驗證負性情緒與策略類型×情境負性程度交互作用的關系,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對負性情緒的影響。具體如公式(1)所示,在水平1 模型中,我們用情境負性程度(事件負性程度或平均消極情緒程度)預測策略使用程度。

因變量(策略使用it)反應了被試(i)在時間點(t)的策略使用程度。截距(β0i)表示被試(i)的情境負性程度的平均水平。斜率β1i反映了個體內情境負性程度和策略使用程度之間的關系。rti代表被試(i)在時間點(t)的情境負性程度無法解釋的誤差項。在第二水平模型中,在控制掉性別和年齡后,公式1 中的所有參數在個體間水平被允許隨機變化。公式(2)和公式(3)擬合了策略類型(認知重評=1;分心=2)、負性情緒和情境負性程度的交互項。

在公式(2)和公式(3)中,截距項因子γ00和γ10代表了公式1 中個體內水平變量的估計參數。斜率項因子γ01和γ11反映了策略類型(認知重評或分心)與水平1 模型中情境負性程度的相關。斜率項因子γ02和γ12代表了個體間負性情緒(抑郁水平或焦慮水平)與水平1 模型中情境負性程度對因變量的交互作用。參數u0i和u1i反應了無法被個體間變量解釋的誤差項。模型中,如果負性情緒水平×策略類型×情境負性程度交互項系數為負,則表明個體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越高,其負性情緒水平越低。
3 結果
3.1 描述統計
兩個樣本用于潛在剖面分析的情緒調節策略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呈現在表2 中。基于多水平驗證性因子分析計算情緒調節策略的復合信度(omega),結果顯示樣本1 的omega值為0.864,樣本2 的omega值為0.942,表明情緒調節策略測試內容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2 情緒調節策略使用程度的描述性統計信息
樣本1 一共提取2860 次負性事件,被試平均的生活事件數量為13.55 (SD=4.58),范圍為7~33。樣本2 一共提取3491 次時間點數據,被試平均回答次數為34.91 (SD=6.89),范圍為27~60。多水平模型中所有變量的被試內平均數的均值和標準差呈現在表3 中。

表3 所有變量的被試內均值的描述統計
3.2 潛在剖面分析結果
在樣本1 中,根據不同被試應對日常生活負性事件的策略使用程度,潛在剖面分析結果表明五大類別的擬合指數最佳(AIC=3597.30,BIC=3751.48,Entropy=0.84,BLRT_p=0.009,網絡版附錄表 2S),分別為:適應組(Adaptive ER,占比9.48%),即傾向使用適應性策略,如社會分享、認知重評、接受和分心等策略,而較少使用非適應性策略,如表達抑制和沉浸策略;平均組(Average ER,占比30.81%),即各類策略使用程度比較均等;表達抑制偏好組(Supress Focus,9.01%),即更傾向使用表達抑制策略;沉浸偏好組(Rumination Focus,37.91%),即更傾向使用沉浸策略;不活躍組(Inactive ER,占比12.80%),即各類策略使用程度均比較少(見網絡版附錄圖2S a)。進一步對樣本1中的5 個情緒調節組的負性情緒水平(抑郁和焦慮)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樣本1 中的5 個情緒調節組在抑郁(F(4,206)=5.44,p〈 0.001) (見圖1a)和焦慮水平(F(4,206)=5.68,p〈 0.001) (見圖1b)上均存在顯著性差異。方差齊性檢驗結果表明抑郁情緒在不同組別的方差不等(F=3.05,p=0.018),因此采用蓋姆斯-豪厄爾(Games-Howell)進行事后兩兩比較。結果表明,沉浸偏好組(M=11.90)比平均組(M=8.31,t=3.95,p=0.025)的抑郁情緒水平顯著要高。表達抑制偏好組(M=15.84)比平均組(M=8.31,t=7.53,p=0.035)的抑郁情緒水平顯著要高。表達抑制偏好組的抑郁情緒水平略高于適應組(M=8.40,t=7.44,p=0.077)和不活躍組(M=8.81,t=7.03,p=0.076),但差異未達到顯著水平。方差齊性檢驗結果表明焦慮情緒在不同組別的方差不存在差異(F=1.82,p=0.126),因此采用最小顯著差數法(LSD)進行事后兩兩比較。多重比較結果表明:沉浸偏好組(M=9.49)要顯著高于平均組(M=6.80,t=2.69,p=0.027),與適應組的差異邊緣性顯著(M=5.95,t=3.54,p=0.051)。表達抑制偏好組(M=14.53)的焦慮情緒水平要高于適應組(t=8.58,p〈 0.001)、平均組(t=7.73,p〈 0.001)和不活躍組(M=6.63,t=7.89,p〈 0.001)。其它組別的抑郁和焦慮情緒無顯著差異。

圖1 不同情緒調節策略組別的抑郁和焦慮情緒比較
在樣本2 中,根據不同被試在疫情期間的策略使用程度,潛在剖面分析結果表明六大類別的擬合指數最佳(AIC=1595.19,BIC=1754.71,Entropy=0.95,BLRT_p=0.001,網絡版附錄表2S),分別為:適應組(Adaptive ER,占比9.91%),即傾向使用適應性策略,如社會分享、認知重評、接受和問題解決等策略,而較少使用非適應性策略,如表達抑制和沉浸策略;接受偏好組(Accept Focus,5.94%),即更傾向使用接受策略;沉浸偏好組(Rumination Focus,19.80%),即更傾向使用沉浸策略;分心偏好組(Distract Focus,占比37.62%),即更傾向使用分心策略;活躍組(Active ER,占比12.87%),即各類策略使用程度均比較多;不活躍組(Inactive ER,占比13.86%),即各類策略使用程度均比較少(見網絡版附錄圖2S b)。進一步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表明:6 個情緒調節組在抑郁(F(5,95)=2.74,p=0.024) (見圖1c)和焦慮水平(F(5,95)=2.98,p=0.015) (見圖1d)上同樣存在顯著性差異。方差齊性檢驗結果表明抑郁(F=1.94,p=0.096)和焦慮情緒(F=0.82,p=0.537)在不同組別的方差不存在差異,因此采用最小顯著差數法(LSD)進行事后兩兩比較。進一步多重比較結果表明,沉浸偏好組(M=11.58)比分心偏好組(M=4.53,t=7.05,p=0.001)、適應組(M=4.80,t=6.78,p=0.019)和不活躍組(M=4.50,t=7.08,p=0.007)的抑郁情緒水平顯著要高。在焦慮情緒水平的多重比較中,沉浸偏好組(M=48.58)要顯著高于分心偏好組(M=42.25,t=6.33,p=0.030)、活躍組(M=38.45,t=10.12,p=0.010)、不活躍組(M=39.79,t=8.79,p=0.016)和適應組(M=35.10,t=13.48,p=0.001)。其它組別的抑郁和焦慮情緒無顯著差異。
3.3 情緒調節靈活性與抑郁情緒關系的多水平回歸模型結果
預分析結果表明:模型中所有變量的組內相關系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值均大于0.059,因而適合進行多水平模型分析(見網絡版附錄3.1)。表4 呈現了抑郁情緒水平與情緒調節靈活性(基于策略使用-情境匹配程度)關系的主要結果。如表4 所示,樣本1 中,個體水平的抑郁程度與日常情緒調節策略使用程度沒有顯著關系,事件負性程度與策略使用程度顯著相關。策略類型和事件負性程度的交互項系數顯著(B=0.11,p=0.002,f2=0.04),表明個體隨情境負性程度降低更多使用認知重評策略,更少使用分心,隨情境負性程度提高呈現相反的策略使用傾向(高策略-情境匹配程度)。最重要的是,抑郁水平、策略類型和事件負性程度的交互項系數顯著(B=-0.01,p=0.047,f2=0.03),表明個體抑郁情緒水平與策略-情境匹配程度(情緒調節靈活性)有關。為了進一步探討抑郁情緒水平和策略-情境共變程度之間的關系,我們基于R 語言“interactions”包(Long,2019)進行簡單斜率分析,檢驗策略-情境匹配程度在抑郁情緒水平為平均值的±1 SD 時是否差異顯著。如表5 所示,當抑郁水平為-1SD時,策略類型和事件負性程度交互作用顯著(B=0.14,p=0.003,f2=0.09,見圖2a),表明抑郁水平低的個體隨生活事件負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隨負性程度降低則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即高情緒調節靈活性)。然而,在抑郁水平為+1SD時,策略類型和事件負性程度交互作用不顯著(B=-0.01,p=0.846,見圖2b),表明抑郁水平高的個體在所有負性生活事件中均使用更多分心策略(即低情緒調節靈活性)。

表4 抑郁水平、策略類型和事件負性程度預測策略使用的多水平模型固定效應估計值

表5 抑郁水平對策略類型-情境負性程度斜率的簡單斜率分析
與樣本1 不同的是,樣本2 中我們用疫情期間經驗取樣每個時間點的平均消極情緒評估不同情境的負性程度。該分析完全重復驗證了樣本1 的核心結果:1)策略類型和平均消極情緒的交互項系數顯著(B=0.10,p〈 0.001,f2=0.04),表明策略使用-情境負性程度匹配現象在群體中普遍存在;2)抑郁水平、策略類型和平均消極情緒的交互項系數顯著(B=-0.01,p=0.017,f2=0.03),表明個體抑郁情緒水平與策略使用-情境負性程度匹配(情緒調節靈活性)有關(表4)。進一步的簡單斜率結果表明:在抑郁水平為-1SD時,策略類型和抑郁水平交互作用顯著(B=0.13,p〈 0.001,f2=0.09,表5 和圖2c),表明抑郁水平低的個體隨消極情緒提高使更多用分心策略,而隨消極情緒降低則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即高情緒調節靈活性)。然而,在抑郁水平為+1SD時,策略類型和事件負性程度交互作用邊緣顯著(B=-0.12,p=0.064,表5 和圖2d),抑郁水平高的個體的策略與情境共變呈相反趨勢,即隨消極情緒情境提高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而隨消極情緒降低使用更多分心策略(即低情緒調節靈活性)。

圖2 抑郁水平對策略類型-情境負性程度斜率的簡單斜率分析
3.4 情緒調節靈活性與焦慮情緒關系的多水平回歸模型結果
表6 呈現了焦慮情緒水平與情緒調節靈活性(基于策略使用-情境匹配程度)關系的主要結果。樣本1 的結果表明個體水平的焦慮情緒與日常情緒調節策略使用程度沒有顯著關系,事件負性程度與策略使用程度顯著相關。策略類型和事件負性程度的交互項系數顯著(B=0.07,p=0.033,f2=0.03),表明了策略使用-情境負性程度匹配的現象。然而焦慮情緒水平、策略類型和事件負性程度的交互項系數不顯著(B=-0.00,p=0.591),表明個體焦慮情緒水平與策略-情境匹配程度(情緒調節靈活性)沒有顯著關系。如圖3a 和圖3b 所示,在高低焦慮群體中,策略類型-情境負性程度的關系呈現相同的趨勢。在樣本2 中,我們用疫情期間經驗取樣每個時間點的消極情緒平均值測量情境的負性程度,并用斯皮爾伯格狀態焦慮量表測量了個體的焦慮情緒水平。其結果部分重復驗證了樣本1 的結果:1)策略類型和平均消極情緒的交互項系數顯著(B=0.43,p〈 0.001,f2=0.05),表明策略使用-情境負性程度匹配現象普遍存在;2)焦慮情緒水平、策略類型和平均消極情緒的交互項系數顯著(B=-0.01,p〈0.001,f2=0.05),表明個體焦慮情緒水平與策略使用-情境負性程度匹配程度(情緒調節靈活性)有關。進一步的簡單斜率結果表明:在焦慮情緒水平為-1SD時,策略類型和平均消極情緒交互作用顯著(B=0.26,p〈 0.001,f2=0.11,表7 和圖3c),表明焦慮水平低的個體隨消極情緒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隨消極情緒降低,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即高情緒調節靈活性)。當焦慮情緒水平為+1SD時,策略類型和平均消極情緒作用顯著(B=-0.17,p=0.007,f2=0.08,表7 和圖3d),表明焦慮水平高的個體隨消極情緒提高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而隨消極情緒降低使用更多分心策略(即低情緒調節靈活性)。

圖3 焦慮水平對策略類型-情境負性程度斜率的簡單斜率分析

表6 焦慮水平、策略類型和情境負性程度預測策略使用的多水平模型固定效應估計值

表7 焦慮水平對策略類型-情境負性程度斜率的簡單斜率分析
4 討論
本研究首次基于高時間分辨率和生態效度的經驗取樣方法評估了中國大學生群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結合策略結構和策略-情境匹配程度表明情緒調節靈活性現象普遍存在,并可以顯著預測個體的負性情緒水平。單一策略使用偏好反應了僵化的情緒調節模式,即更低水平的情緒調節靈活性。與已有研究結果保持一致(Chesney & Gordon,2017;Dixon-Gordon et al.,2015;Lougheed & Hollenstein,2012),單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達抑制偏好)的個體在負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間經歷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慮情緒。研究以健康大學生為被試,在兩個獨立的樣本中重復驗證了基于策略-情境匹配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對減少負性情緒(抑郁和焦慮)的積極影響。具體而言,無論在生活事件中或疫情期間,個體隨情境負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隨情境負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即具較高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其后續的抑郁情緒更低。然而,如果個體的策略使用和情境負性程度匹配呈相反趨勢(即具較低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其抑郁情緒更高。此外,我們部分重復驗證了情緒調節靈活性與焦慮情緒的關系,即在新冠肺炎期間,個體隨消極情緒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隨消極情緒降低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即具較高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其后續的焦慮情緒更低。然而基于策略使用和日常生活負性事件的匹配程度與個體的焦慮情緒沒有顯著關系。以上結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策略-情境匹配理論,強調了個體根據不斷變化的情境特征靈活使用與情境需求匹配的策略對個體情緒健康水平具有更適應性意義(Aldao et al.,2015;Cheng et al.,2014;Sheppes,2020)。綜上,本研究基于兩類方法共同驗證了情緒調節靈活性對減少大學生個體負性情緒的積極作用。
4.1 基于策略-情境匹配的情緒調節靈活性特點
Bonanno 和Burton (2013)提出的情緒調節靈活性成分模型對本研究核心結果具有重要的解釋意義。該模型表明情緒調節靈活性依賴于情境敏感性(context sensitivity),策略有效性(repertoire)和反饋反應性(feedback)三個主要成分的相互作用(Bonanno & Burton,2013)。其中情境敏感性是指個體覺察情境改變所引發的需求或機會,并引導個體選擇情境匹配的策略,并包括對有利于情境適應的調節策略的覺察(Cheng,2001,2003;Cheng & Cheung,2005)和情緒刺激線索的覺察(Gross et al.,2011;Gross & Feldman Barrett,2011)。策略有效性是指個體使用多種策略來適應由情境改變所引發的需求或機會的能力,包括個體掌握策略的數量(Orcutt et al.,2014)、策略使用隨時間的變異性(Gall et al.,2000,2009)和不同策略類型間使用的變異性(Bonanno et al.,2004)。因此策略有效性為策略-情境匹配提供了策略庫的重要基礎。反饋反應性是指個體內在生理信號(Füst?s et al.,2013)和社會信號(Eisenberger et al.,2003)的反饋對當前情緒調節效果的監控,并通過保持和切換有效策略、停止無效策略等行為改善調節效果的能力。本研究結果表明低策略-情境匹配的個體具有更低水平的情緒調節靈活性。考慮到基于策略-情境匹配的情緒調節靈活性依賴對情境負性程度的感知、策略間的靈活切換和及時的調節效果反饋。由此可見,低策略-情境匹配可能意味著個體在任意成分中存在障礙,且有可能在不同成分間之間存在不協調,從而可能導致個體無法基于情境需求靈活地切換策略,實現有效的情緒調節過程。此外,情緒調節成分模型同樣給單一僵化的策略使用偏好提供了理論基礎。沉浸和表達抑制策略的使用偏好表明個體有可能忽略情境的需求,僅僅使用常用或優勢策略。也可能反映個體無法從一種策略的認知過程切換到另一種與情境需求相匹配的策略。個體對當前策略的調節有效程度的反饋錯誤也會導致個體持續性采用相同調節策略,甚至無法意識到單一的調節方式可能產生了更消極的情緒影響。然而以上潛在解釋仍需要進一步的機制研究探討不同成分如何作用于個體的策略-情境匹配和平衡的情緒調節策略剖面結構。
此外,情緒調節拓展模型(the Extended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的評估系統對于理解基于策略-情境匹配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具有重要啟示(Gross,2015)。該模型由一個三階段的循環系統(perception -valuation -action (PVA) processing cycle)組成,包括感知階段(perception)、評估階段(valuation)和行動階段(action)。具體而言,感知階段負責輸入各種刺激。評估階段是指根據當前的目標、背景和類似刺激的已有經驗,動態評估情境刺激的價值。行動階段包括產生與評估相適應的反應。在這個理論框架下,第一個PVA 產生了情緒,第二個PVA 對上一個PVA 進行感知和評估,并針對上一個PVA 產生行為的過程便是情緒調節的過程。PVA 循環中的三層評估系統(核心、情境和概念)一定程度決定了調節行為的輸出。在不斷變化的生活情境中,個體需要不斷刷新評估系統,引導其做出適應性策略行為。具體而言,在高低負性情境下對認知重評和分心策略的使用涉及到個體對自身認知能力、生理反應和與情緒刺激相關等背景信息的評估(Beedie & Lane,2012;Raio et al.,2013)。因此,研究強調了情境特征的評估系統在情緒調節靈活性中的關鍵作用。
4.2 策略-情境匹配理論的拓展
本研究豐富了策略-情境匹配理論。早期對策略-情境匹配的研究集中在情緒聚焦性策略(emotion-focused)和問題解決聚焦性策略(problemfocused)與情境可控程度的匹配(Cheng,2001,2003)。具體而言,認知重評(情緒聚焦策略)在不可控的情境下具有較高的適應性,因為在無法采取其他行動措施的情況下,情緒是唯一可以改變的東西。然而,當遇到相對可控的情境時,解決情境中的問題(問題聚焦策略)會更有優勢。因此,根據情境可控程度采用認知重評或問題解決策略體現了較高的情緒調節靈活性(Cheng,2001;Cheng et al.,2012)。后續研究從認知重評能力和認知重評策略使用與情境可控程度的匹配驗證了情緒調節靈活性與心理健康呈積極的關系(Haines et al.,2016;Troy et al.,2013)。而本研究基于情緒調節過程模型,證明了發生在不同調節階段的策略(分心和認知重評)與情境的負性程度之間的匹配同樣可以表征個體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大量的行為研究表明基于圖片刺激操作的情境負性程度影響個體對注意解離(分心)策略和認知重評策略的選擇(Levy-Gigi et al.,2016;Sheppes et al.,2011,2014)。在本研究中,我們通過負性事件和新冠肺炎期間的消極情緒兩種方式表征情境的負性程度,表明情境的負性程度不僅包括情緒信息的效價,還包括個體對情緒信息的主觀反應(Sheppes,2020)。近期,有研究表明,情境的社交屬性(如與他人親近程度)會影響不同情緒調節策略的選擇(English et al.,2017)。此外,調節目標和人格特質也是影響個體情緒調節過程的重要因素(Eldesouky & English,2019a,2019b;Millgram et al.,2019)。因此,未來研究應該拓展基于策略與不同情境特質以及其他因素(如調節目標和人格特質)的匹配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行為對心身健康的重要作用。
4.3 情緒調節靈活性與抑郁和焦慮情緒的關系
基于情緒調節靈活性與抑郁和焦慮情緒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情緒調節靈活性是具有一定適應性的。缺少情緒調節靈活性(如單一策略使用偏好和策略-情境不匹配)導致大學生經歷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慮情緒,其潛在原因可能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注意力偏好導致的情境特征評估偏差:如抑郁癥患者對負性刺激的注意加工偏向和解離困難(Beck & Bredemeier,2016;Disner et al.,2011),而焦慮障礙患者則是對威脅刺激的過度警覺(Campbell-Sills et al.,2007)。而對情境特征的評估誤差和局限性將很大程度影響由情境需求導向的策略選擇,從而形成單一的策略使用傾向(如抑郁個體傾向使用沉浸策略,而焦慮個體傾向使用擔心策略);2)策略使用習慣單一化:單一策略的使用傾向和優勢加工將不易于個體基于不同情境需求提取不同的策略進行情緒調節;3)認知控制資源的缺陷有可能是焦慮癥和抑郁癥患者存在負性情緒調節靈活性缺陷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見,情緒調節不靈活性很有可能是抑郁和焦慮情緒的情緒調節障礙的原因之一。這一研究結果對于情緒障礙疾病的治療和干預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以往的臨床干預聚焦在提高個體認知重評和分心等策略的能力。而本研究結果表明干預不僅應該關注提高策略使用的能力,而且應該訓練個體在不同情境中使用與情境匹配的策略的能力(Mennin,2004,2006)。具體而言,基于策略-情境負性程度匹配的情緒調節靈活性干預目標旨在提高個體對情境負性程度的敏感性,同時幫助個體理解認知重評和分心在不同類型情境中使用效果差異,從而學會根據情境需求靈活部署調節策略。此外,提高個體情緒調節策略庫的廣度為其在不同情境中靈活的策略切換提供了基礎,避免單一僵化的策略使用偏好。
4.4 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盡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仍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的結論是基于健康的大學生群體,因此研究結論的普適性具有一定的局限。考慮到情緒調節僵化可能是臨床精神疾病的情緒調節障礙的主要表現之一,未來研究可以在臨床樣本(如抑郁癥、焦慮障礙等)進行重復驗證,以探明情緒調節靈活性在精神疾病中的情緒加工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作為潛在有效的跨臨床診斷方法之一。此外,未來研究需要關注其他年齡段(如兒童、青少年和老年)的群體在情緒調節靈活性表現的差異,以解釋情緒調節靈活性的發展規律。第二,本研究僅基于認知重評和分心策略在不同負性程度情境下使用的成本和效益,然而現實生活的情境是豐富和復雜的,其特征屬性也是多樣的。因此探討這兩類策略與其他情境特征之間的匹配(如、情境的可控程度、社交屬性等)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適合特定策略使用的情境以及策略-情境匹配理論在實際生活中對調節效果的作用(Eldesouky & English,2019a,2019b)。第三,本研究沒有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的心理機制。早期的情緒調節靈活性成分理論強調了不同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但缺乏整合的研究視角(Bonanno & Burton,2013)。近期研究強調基于情緒調節的決策行為,例如確認是否需要情緒調節,如何從已有的情緒調節策略中挑選最佳策略、停止無效策略和切換到有效策略等,可以深入探討情緒調節靈活性的認知過程(Sheppes,2020)。此外更有研究者提出從認知控制的角度探討不同階段情緒調節靈活性的心理機制。具體而言,當個體意識到無需調節的時候,需要使用認知控制中的抑制能力。在選擇階段,個體需要在不同策略之間進行有效切換,因此會涉及認知控制中的切換和刷新能力。當個體意識到調節策略是有效的,則需要抑制其他策略,從而維持有效策略的使用(Pruessner et al.,2020)。由此可見,認知控制對于理解動態變化的情緒調節靈活性認知過程是至關重要的(Dreisbach & Fr?ber,2019;Goschke & Bolte,2014)。此外,為了更進一步提高該方法收集數據的可靠有效性,未來研究可通過設置注意陷阱題和隨機打亂問卷測試內容的順序,以確保被試認真完成每次測驗,從而提高數據質量。
5 結論
本研究首次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結構和策略-情境匹配證明了情緒調節靈活性可以顯著預測大學生群體的抑郁和焦慮情緒。具體表現為:(1)具有單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達抑制偏好,即低情緒調節靈活性)的大學生群體相對其他策略剖面結構(如平均組、不活躍組等)在負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間經歷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慮情緒。(2)基于策略使用(認知重評和分心)與情境負性程度(負性生活事件和COVID-19)的共變關系,可以有效測量大學生群體日常生活中的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并發現情緒調節靈活性的普遍存在。(3)高情緒調節靈活性水平的大學生群體(隨情境負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隨情境負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認知重評策略),經歷了更低水平的抑郁和焦慮情緒,表明情緒調節靈活性對大學生的情緒健康水平具有積極作用。本文研究發現一方面支持了策略庫廣度和策略-情境匹配作為情緒調節靈活性研究領域的重要理論基礎,提供了有效的測量個體情緒調節靈活性的手段;另一方面,加深了對臨床精神疾病患者和重大集體創傷事件(如疫情、地震等)背景下民眾的情緒調節障礙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