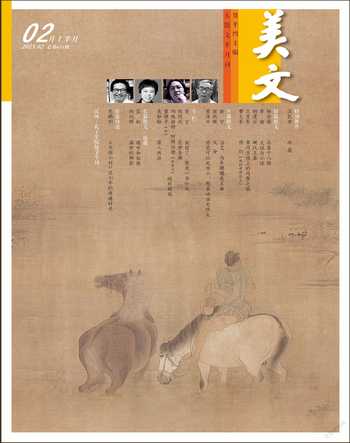奴去也,莫牽連
探春——漂泊人生亦清明
探春的生母是趙姨娘,對比同父同母的弟弟賈環在賈府的境遇,就知道她贏得賈母、王夫人及眾姐妹的喜愛有多難。
第三回,黛玉初到賈府見到的探春是“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這樣的小女孩兒會給你什么印象?對,氣質好。氣質好的女孩一般不笨,探春確實聰明,智商高,情商也高,是不多見的雙商在線,寶釵也雙商在線,但功利心太強,算計太深,探春的生存之道要清明得多。
她的判詞是: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
探春有才、有志、有情、有心,壓過賈府一眾男性,只因女兒身便有無限遺恨:“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 第五十四回,“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探春管家,趙姨娘為爭二十兩銀子辱罵探春,探春羞、愧、氣、憤,說出了這番話,是躲無可躲逃無可逃的無奈。當她真的遠嫁離開賈府時,面對的是骨肉分離之痛。紅樓夢曲她對應的是“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以探春本性,她是能作為時絕不逃避,無能為力時旁觀好了,看你們能爛到什么程度,到時能救則救,不能救,各自安好吧。“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探春是灑脫通透之人,她知道什么事什么時候該為、可為、能為,她也知道什么事不能為,只能任其自然。“一任南北東西各分離”,是面對命運的豁達,也是她處世的原則。與迎春的佛性不同,迎春是無助下的順從;與黛玉的放棄也不同,黛玉是無望后的舍棄,與惜春的出世更不同,惜春是了悟后的遁世;探春則試圖主宰自己的命運, 她是洞察情勢后的有為。
探春清楚自己在賈府的處境,生母趙姨娘是賈府的萬人嫌,《尚書大傳》有“愛人者兼及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余。” 漢王充 《論衡·恢國》中有:“惡其人者,憎其胥余。”所謂“愛屋及烏 ,憎及胥余”,探春和賈環都是趙姨娘的“胥余”,賈環是從賈母到王夫人再到奴仆無一人不憎惡嫌棄,雖他本人不堪,但把嫌惡趙姨娘之心移到他身上也是不爭的事實。探春帶著不討喜的身份,讓別人尤其是王夫人在厭惡她生母的同時喜歡她, 登天的難度。第五十四回,熙鳳生病,探春協助李紈管家,趙姨娘因兄弟之死想多要銀子鬧得不可開交,探春傷心,李紈等“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探春對趙姨娘說:“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鳳姐說:“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里卻是和寶玉一樣呢。”興兒說她:“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鴰窩里出鳳凰。”透著惋惜,更有抑制不住的贊美。可見趙姨娘的俗行惡語會反噬到探春身上,像帶泥的雨點,總會在身上留下印痕,她要驅散烏云才能做到明月清風。
探春很能發現矛盾的根本所在,賈府的男人不管內宅事,權威人物是賈母、王夫人和鳳姐,而鳳姐在情感上與賈母親厚,在血緣上與王夫人近密,雖然陰毒卻也不是蠻橫無理之人;賈母喜愛孫女,更喜愛聰明、敏銳、脫俗之人,探春天生如此,無須費心討好,雖說黛玉比三個孫女更得賈母憐愛,但探春與迎春和惜春還是有所不同,這個孫女上得臺面,況賈母的愛不是求來的,是自身優秀贏來的,什么樣的心思手段能誆得住賈母?寶釵費盡心機還不是多次被打臉。王夫人是嫡母,作為女兒,只需得到她的認可,即可安枕無憂,探春做到了,做得滴水不漏。
王夫人少有自我,她壓抑著自己,賈政面前藏著情感,賈母面前守著規矩,晚輩面前嚴肅木訥,唯有在兒子這里表露情感,那般溫柔而熾烈。第二十五回,在王夫人房里,寶玉“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說了幾句,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里。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搬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道短的”。此時寶玉十三歲,在當時已是婚配之齡,也算成年之人,王夫人猶親密如此。寶玉是王夫人的命,是她全部的寄托,所以照看眷顧寶玉最能得其歡心,但不能像賈母那樣奪走寶玉對母親的依賴,更不能像黛玉那樣讓寶玉嬉笑怒罵皆為她一人。既要體現對寶玉的好,又不能過于親近,讓王夫人有剝離感,這點寶釵做到了,把寶玉交給她,王夫人依然是寶玉最親密之人。探春也做到了,作為妹妹她有天然優勢,但趙姨娘是天然屏障,利用優勢克服屏障,探春做的巧妙無痕。她把錢交給寶玉代買“輕巧頑意兒”,既是對寶玉審美的信任,也是關系親近的體現,更是她回護寶玉的借口,堂而皇之地為寶玉做鞋,在別人有微詞的時候回懟一句:給誰做是情分,不是本分,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管你什么親的庶的。這樣親密仗義的言行到了王夫人那里自然會感嘆:“這孩子真懂事。”
讓王夫人感到溫暖的還有貼心小棉襖薛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的寶釵在賈府大得人心,探春與之親近也不稀奇,多數情況下,探春都以她便利的身份維護寶釵。
第二十九回,賈母帶人在清虛觀打醮,道士們給了寶玉一盤子金玉法器,賈母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眼熟,只是想不起來誰戴過,這時寶釵說:“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不僅記得誰有,還記得是什么樣子,很是詳細。寶玉道:“他這么往我們家去住著,我也沒看見。”氣氛有點尷尬,探春解圍了,說:“寶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記得。”人家又不是只記得這一件事,是事事都記得。雖然不像黛玉說的,“他在別的上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但對“金玉”更為關注也是事實,別人不是沒看破,只是不說破,探春出面維護,使寶釵、王夫人沒那么難堪,王夫人怎不另眼相看。
第三十七回大家結社寫詩,李紈說寶釵的含蓄渾厚好過黛玉的風流別致,探春不顧寶玉的反對,說:“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第三十八回寫菊花詩,李紈判黛玉奪魁,探春又表揚寶釵:“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卻不見夸黛玉一句。
第五十六回,探春管家,實行改革,開發大觀園的經濟價值,其宗旨借李紈之口說出“專司其職……使之以權,動之以利”,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有點現代管理的味道了。因蘅蕪苑和怡紅院兩處院子多鮮花香料,平兒推薦寶釵的丫鬟鶯兒的母親管理,寶釵為避嫌推薦了寶玉的小廝茗煙的母親,說兩家親厚,茗煙的娘可隨時向擅長此事的鶯兒娘討教,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還認了茗煙之母葉媽做干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的好得很呢。”你猜平兒是有意還是無意?探春聽了,方罷了。兩家親厚,自是少些爭名爭利之事,但探春作罷還因為茗煙是寶玉的小廝,鶯兒是寶釵的丫鬟,親連著親的不好說話。同時她也看到了寶釵的心機,統戰工作如此到位,不是她一個庶出女兒能惹的,得罪寶釵的成本太高,探春付不起。她可以駁趙姨娘,親娘可以惹,辱罵就辱罵了,再氣惱也是生母,不是叫一句“姨娘”就能抹去的,終歸會原諒自己,但寶釵還是算了吧,自己雖叫王夫人母親,但人家的貼心小棉襖是寶釵,況且自己與王夫人之間隔著趙姨娘,還真當自己是人家女兒?得罪黛玉無非惹賈母不悅,但賈母畢竟是祖母,老人家還能記恨孫女不成?算起來寶釵對自己在賈府生存狀況的影響大于黛玉,不能惹。
第二十七回探春對寶玉說“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姐妹中,她與寶釵并無血緣關系,與黛玉是姑表姐妹,與迎春是堂姐妹,與惜春已是第五代血親,這句話實實在在為自己近寶釵而遠黛玉開脫。但她與黛玉的關系還算親密,第七十六回中秋節,王熙鳳生病不在,寶釵出了大觀園,寶玉心情不佳活躍度不高,但大家聚在一起人并不少,可“賈母猶嘆人少,不似當年熱鬧 ”,黛玉不覺感懷垂淚,況“探春又因近日家事著惱,無暇游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黛玉與迎春、惜春不合,那合的當然是探春了。但探春在公開場合不親近黛玉,甚至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疏遠。第六十二回,探春細數眾人生日,有元春、太祖太爺,到寶釵時是這樣說的:“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初九日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么沒人?就只不是咱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個記性是怎么了!”她們娘倆遇得巧,多親密的說法,只不知道賈母是否樂意?到了二月直接說沒人,連太祖太爺和賈璉的生日都沒忘,居然不記得天天相見的黛玉生在哪天,我能說你當眾故意如此嗎?她知道王夫人對黛玉的厭惡。
探春不能慰藉王夫人的孤獨,也無從排解她的委屈,但可以化解她的尷尬。第四十六回,賈赦討鴛鴦,鴛鴦不從,在眾人面前剪發明志,因王夫人在旁,賈母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敬,暗地里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要,剩了這么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 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 探春有心的人,知道別人都不適合出面說話,賠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嬸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話說的字字點在穴位,讓人駁無可駁,所以猶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姨太太別笑話,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一句話解了王夫人之困,也給賈母搭了臺階,否則二人都不好收場。這件事不光彩,也不簡單,祖母、伯母、嫡母都卷入伯父的納妾之事,自然是能躲就躲,李紈帶著姐妹們撤退是明智之舉,十三四歲的探春能停下來觀察事態走向,有勇氣出來調解,還一句話就平息了賈母的憤怒,這個女孩兒不簡單。
探春提議起了海棠詩社,很重要的理由是:棲泉石之間,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當宴集詩人。知道自己的詩才“難與薛林爭”,探春搭了一個讓別人展示才華的平臺,是有大格局之人。詩詞是她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第五十回“蘆雪庵爭聯即景詩”,黛玉、湘云、寶琴 三個人搶答,用湘云的話說“不是作詩,竟是搶命呢”。第七十六回中秋夜,賈母隔水聞笛,黛玉、湘云臨水聯詩,于清寂中給出絕美畫面。這是生活的自然過程,也是生活的組成部分。但有了詩社,寫詩就有了儀式感,在詩與人、詩與生活之間織了一層紗,透過詩看人、看品、看性格,看生活,甚至看未來。把寫詩變成游戲,把孤寂演成熱鬧,讓賈府這個墮落之地有了清雅純凈,讓禮教壓抑著的生活勃發著青春,探春有能力改變周圍人的生活。
詩社中才華突出的是寶釵和黛玉,探春做了幕后英雄,而協助李紈管家,則因高超的管理水平由配角變成了主角。
開始沒人看好庶出的探春,只三四日后,幾件事過手,眾人便“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興兒說:“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無人不愛的,只是刺戳手。”鳳姐說探春:“心里嘴里都也來的。”平兒對管家婆子媳婦們說:“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頭,也就只單畏他五分。”這些言論都是對她能力的肯定。她表面風平浪靜,心中自有丘壑,沒有管家經驗,但明了管家之道。當那些刁奴想欺幼主時,她只用規則、舊例,便一招制敵。當趙姨娘當眾發難,說:“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就忘了根本, 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時,她以禮教規范駁得趙姨娘啞口無言。
探春以公心處理事務,不欺己、不欺人、不欺天。
探春清楚地知道賈府的財務危機,也看到癥結所在,于是開啟了經濟體制改革之路,她做能做的事情。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免要觸動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她智慧地選擇府中最有體面的寶玉、鳳姐開例作筏子,不能殺雞,拔幾根雞毛還是可以的,讓猴收斂起張狂,按規則辦事吧。女孩子的胭脂水粉、男孩子的學費都是幾處支出,太浪費了,停發;園子很大,管理成本很高,好辦,收益歸勞動者,別拿工資了,花草香料,水果蔬菜,誰擅長什么就去做什么,園子里的收成都歸你,我只要一個花繁葉茂。幾項措施下來,財務亂局有了一些改觀,雖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賈府的衰落也阻止不了,只求慢一點,再慢一點。探春以她的方式告訴我們,衰落是天災,也是人禍,人不墮落,還可減緩頹勢,但看府中人,救無可救。
當人人走入迷局,便有匪夷所思之事。抄檢大觀園是邢夫人推波,王善寶家的助瀾,王夫人入局做了發起人,王熙鳳無可奈何只能隨其行動。
探春的反應是震驚、憤怒,賈家混亂至此,需要抄家來證明人的清白,小事被外化成天大的事。探春對抄家人的態度是:搜我可以,搜丫鬟不行,她護的不是丫鬟,而是賈府的尊嚴。王善寶家的挨打,是因為她亂了秩序。第五十五回,趙姨娘弟弟趙國基去世,趙姨娘說:“如今你舅舅死了……”探春說:“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檢點,那里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習按理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么說,環兒出去為什么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來?”她以家庭倫理秩序駁斥了趙姨娘,而王善寶家的違背了主尊奴卑的封建倫理。賈府長者為尊,即使長輩的奴婢也高看三分,尤其是年老的媽媽們,邢夫人是榮府長媳,地位很是尊貴,但陪房就是陪房,越不過主子,她有些膽大,且妄為了,敢掀探春的衣角,探春的滿腔怒火正好發泄在她身上。那一掌,是對長輩亂為的憤怒,是對秩序混亂的焦慮,是對倫理失范的無奈,無從發泄下正好遞了靶子過來,不打你打誰?
探春怒斥著:“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一個個不象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這番話直擊要害,賈府表皮光鮮內囊已爛,而眾人還在內囊中撕扯。只是由探春說出令人震撼,府中長輩焦慮中的非理性行為越發令人焦慮,她們的解決之法是加劇內斗的,可能認為把別人整倒,問題就解決了,或許不為解決問題,只要整倒別人就有天大的樂趣。府中男性似乎成了旁觀者,內宅的事內宅人解決,男性是管大事的,些許小事別來煩我。
第七十回,大家放風箏,一個喜字帶走了兩個鳳凰,預示了探春的遠嫁。第七十七回“有官媒婆來求說探春”,探春這只風箏真的要起飛了,只是不知道那根線是否還在賈家手中?遠嫁的探春還能回來嗎?脂批說:“使此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致流散也。”只可惜,賈府沒能留住探春,她空負智慧,眼睜睜看娘家敗落,兄弟流散。
她,救不了賈家。
惜春——唯愿青燈伴古佛
惜春的身份有點尷尬,她是寧國府賈敬的女兒,賈珍的妹妹,母親早逝,與迎春、探春隨賈母生活,后來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處擠著不方便,只留下寶玉、黛玉解悶,讓迎、探、惜三春跟王夫人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迎春和探春是賈母的親孫女,而惜春與賈母沒有血緣關系,雖然賈母從來說的是三個親孫女,聽起來暖心,待遇也無差別,但心理上的疏離感恐怕難以克服,比較起來,黛玉無論是血緣還是心理上都親近得多,黛玉都自認為寄人籬下,惜春呢?
惜春第一次出場是黛玉進賈府時,她“身量未足,形容尚小”。當時黛玉六七歲,惜春應該不超過五歲,還是幼兒呢。她母親早逝,父親在道觀中燒丹煉汞,平時無人看顧,目睹賈母如此寵愛比她大不了幾歲的黛玉,可有羨慕之情?
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宮花給三姐妹,看到迎春和探春下棋,惜春跟“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處頑笑”,她的玩伴似乎只有智能兒。而智能兒能進賈府幾次呢?大多時候惜春只能獨處,沒有長輩的關愛,沒有同齡人的陪伴。她隨著姐姐們給長輩請安、吃飯、參加活動,看起來色色不少、樣樣不落,不過慣例罷了。第五十四回,正月十五元宵節,賈府放煙火花炮,黛玉稟氣柔弱,不禁畢駁之聲,賈母把她摟在懷中,王夫人摟著寶玉,湘云最是大膽不怕的,寶釵等說“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還怕這個呢”,卻有薛姨媽摟著,最小的惜春連同她的兩個姐姐卻是無人呵護。
第三十九回,李紈夸鴛鴦時,“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她在意周圍人的態度,更在意賈母的贊美,可惜賈母的贊美沒有給她。
賈母也是個孤獨者,雖平日有人奉承,大多含蓄婉轉,來個情商極高的鄉下同齡人劉姥姥,奉承得坦蕩直白,把老人家哄得有點失了方向,炫了園子又開始炫孩子,這一炫就炫出了惜春的高光時刻。當劉姥姥說:“誰知我今兒進這園里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立刻接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
作畫讓惜春成為大觀園的中心,有了一次因她而起的聚會,雖然被寶釵、黛玉搶了話語權,但畢竟因她而起。此后,“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里幫忙。 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多往那里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于會面”。惜春的蓼風軒被一張畫驅走了孤寂。人還是要有一技傍身,會有無限可能等你呢。香菱曾指著畫上的美人說:“這一個是我們姑娘,那一個是林姑娘。”告訴我們惜春真的會畫,畫得形象逼真,賈母的炫以事實為依據,惜春以才華成全了賈母的炫耀。
“原應嘆息”四姐妹中,元春堪稱四角俱全之人,她父母雙全,有弟弟、有妹妹,其余三姐妹可沒有這樣的幸運,迎春的母親過世,父親賈赦形同虛設;探春是庶出,屢受趙姨娘連累,日子過得不清凈;惜春近同孤兒,且寧府名聲不佳,她自覺面上無光。如此環境成長的孩子怎能爛漫?同時三姐妹也各有各的智慧,惜春的聰慧敏感不在寶釵、黛玉之下,只是隱于文字之間,不易被發現。
第七回周瑞家的替薛姨媽送宮花,看到智能兒在,問她:“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曾得了沒有?”智能兒說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著?”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著。”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第七十四回抄檢大觀園時,從她的丫鬟入畫那里抄出私藏財物,入畫說是賈珍賞她哥哥的,鳳姐說:“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后門上的張媽。他常肯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幼小的惜春竟能把人物的行為表現作為線索,推斷出事情的前因后果發展態勢,邏輯思維一流,這點恐怕黛玉也有不及。
惜春的存在感甚至比沉默的迎春還少。姐妹中她最小,又不是榮府之人,關注她的人少,憐愛她的人更少,她靜默以觀,看成人世界的風霜雨雪花開花落,看多了,也就看懂了,看懂了只能更沉默。
與智能兒的頑笑應該是她少有的愉悅時刻,由此產生了對佛門的向往,第二十二回惜春所做謎語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
賈政認為惜春所作海燈是“清凈孤獨”,但惜春卻認為是“大光明”,在她短短的人生體驗中,佛中人比家中人更能給她愉悅、讓她安寧,她小小心靈已經有了逃避賈府的意識,所以當周瑞家的給她送宮花時,她說:“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里呢?”這時她未必知道此話的意義,只是純粹的心理認知,出家作姑子可以擺脫眼前的人和事,可以感受另外一種生活。不過自己懵懂,家人不知,只有賈政感受到四個女孩兒的凄苦哀傷,覺察到家族命運的晦暗無常。
賈府是大家族,人多、事多、矛盾多,但平時一團和氣,尤其是成人世界,往往用談笑風生掩飾住刀光劍影,大觀園兒女較少卷入到矛盾中,即使牽涉其中也多由大人出面解決。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王熙鳳效戲彩斑衣”,賈母、王熙鳳的唇槍舌劍本由黛玉引起,但她成了旁觀者。孩子之間的沖突多表現為吵鬧游戲,夾雜著玩笑,吵完就過,過后還是好姐妹。但抄檢大觀園是賈府矛盾的集中爆發,觸發的原因很多,有母親對青春期兒女的焦慮,有主子對奴仆失控的危機,有因沖動而輕信的昏庸,有家族衰落過程的恐懼等等等等。這次沖突對賈府的副作用自不必言,少男少女生活中的安定感更是被沖擊得七零八落。
年少的惜春看到抄家之人進來,因“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么事”。當從她的丫鬟入畫處抄出銀子等財物時,她害怕,對王熙鳳說:“我竟不知道。 這還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她惶恐,知道免不了處罰,但是,別讓她看見,不能看入畫被打或者不能看任何人被打,總之人不能在她面前打。當入畫求饒時,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次方可。這里人多,若不拿一個人作法,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樣呢。嫂子若饒他,我也不依。”說得絕情,卻是理性之言,入畫的行為雖合乎情理,終究違規,惜春要罰,理由充分有力,入畫不罰別人會有樣學樣,小錯不罰就會犯大錯,所以惜春房里不會出現欺主之事。
惜春要尤氏將入畫帶走時說:“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惜春是敏感細膩之人,看重別人的評價。入畫所犯之事很小,小到鳳姐、尤氏都不追究,但她認為實在是打臉,甚至說“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話說得絕情、惡毒。焦大公開罵出了寧府的骯臟,身在榮府的惜春對各種傳聞辯不得又聽不得,也許最好的做法是:我住在榮府,寧府之事與我無關。卻不想入畫與兄長之間的財物傳遞讓她陡然面對現實,終究還是寧府中人,千絲萬縷的聯系逃無可逃避無可避,或許杜絕寧國府能免受牽連,于是“他只以為丟了他的體面”,斷不肯留下入畫,并說:“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我每每風聞得有人背地里議論什么多少不堪的閑話,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上了。”明明白白告訴尤氏,再不斷交恐怕本小姐也沒什么好名聲了。
尤氏心虛,道: “誰議論什么?又有什么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著他才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著我倒好。 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么人了!還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惱,好歹自有公論,又何必去問人。古人說得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夠了,不管你們。從此以后,你們有事別累我。”尤氏道:“可知你是個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惜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么教你們帶累壞了我!”
這番話著實觸動了尤氏心事。賈珍、賈蓉父子與秦可卿之間,賈珍、賈璉兄弟與尤二姐、尤三姐之間的故事瞞得了誰?焦大之罵應是人盡皆知,惜春怎能沒有耳聞,這樣的丑聞讓她無地自容。入畫出事對她來說是人生污點,如同被寧府的污水濺了一身,只有跳出污濁之地才能保持純凈,于是她要舍了入畫,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與寧府斷決,才能保住自身清白。這不是無情,是舍如何,不舍又如何的無奈,是舍亦是不舍,不舍亦是舍的了悟,所以她說:“我不了悟,我也舍不得入畫了。”
了悟的惜春最終選擇了佛門,也許是現實的丑惡與凄涼,也許是幼時記憶中的安寧與愉悅,也許是姐姐們的命運令她陷入無望,總之“三春去后諸芳盡”,她“將那三春看破”,世間的“桃紅柳綠待如何”?不如去找那“ 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果”。
(責任編輯:馬倩)

素 言 經濟學教授,先后求學和訪問于西北大學、北京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現就職于長安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出版有詩歌、散文、攝影集《素言》《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