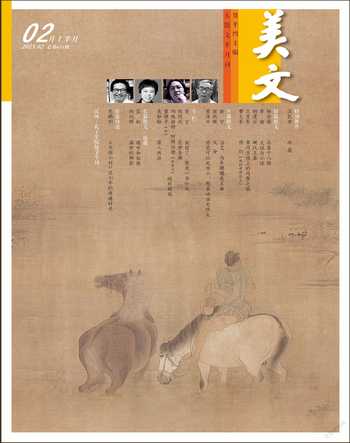分裂光芒的棱鏡
[加拿大]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董繼平[譯]
頁? 面
這一頁等待,假裝空白。難道那就是它的呼吁,它的空白?這光滑而潔白的,這清白得令人恐怖的,是其他什么呢?一場降雪,一條冰川?它是一片沙漠,完全干旱,沒有生命。但人們會冒險進入這樣的地方。為什么呢?為了看看自己的忍耐力究竟能有多大,有多少干枯的光芒?
我說過這頁面是潔白的,而它:潔白得就像婚紗,珍稀的鯨魚、海鷗、天使,冰與死。有些人說它像陽光一樣飽含所有的色彩,其他人則說它因為灼熱而潔白,它將燒盡你的視覺神經,還說那些盯著這頁面太久的人會失明。
這頁面本身沒有范圍,也沒有方向。沒有上和下,除了你自己所給予的標注,沒有厚度和重量,只有你放在那里的,北方和南方并不存在,除非你對它們確信無疑。這頁面沒有遠景,也沒有聲音,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因為這一點,你可以在其中永遠迷失。在那些設法從這頁面歸來者的臉上,你從未見過感激的外貌,歡樂的外貌?盡管他們衰弱,盡管他們失血,他們也跪下來,還把雙手插進泥土,還摟住自己所愛之人的軀體,或者在緊要關頭,懷著從未體驗過的緊迫感——進入這頁面之旅的十足的恐懼的人所不知的緊迫感,摟住他們所能摟住的任何軀體。
如果你決定要進入這頁面,就拿著一把刀和一些火柴,還有某種會飄浮的東西。拿著你可以抓住的東西,還有一只分裂光芒的棱鏡,一個發揮作用的護身符,用鏈條把它掛在你的脖子上:那是為了回來。無論穿哪種鞋都不要緊,但應該露出你的手。你決不要戴著手套走進這頁面。無需說,這樣的決定可不是輕率做出的。
當然,有些人沒有做決定,沒有事先打算就進入這頁面。其中一些人過著著迷的生活,沒有困難,但大多數人則會根本看不清。對于他們,這頁面顯得就像是水井,就像是可愛的水潭,他們一下子就在其中看到一張臉——他們自己的臉,但更好。這些不幸的人并沒跳起來:相反他們倒下,這頁面在他們頭上合攏,沒有一絲聲響,沒有一條縫隙,而且立即就一如既往地完整、空寂、玻璃一般、令人著迷。
關于這頁面的問題就是:它的下面是什么?它似乎只有二維,你可以把它拾起來,把它翻過去,背面與前面相同。你說,沒有什么讓人失望。
然而你在錯誤的地方觀看,你在背面觀看,而不是在下面觀看。在這頁面之下是另一個故事。在這頁面之下是一個故事。這頁面之下是發生過的一切,其中的多半事情,你寧可沒有聽說。
這頁面不是一個水潭而是一種皮膚,一種要在那里忍住的皮膚,它能感到你在觸摸它。難道你真的認為它會僅僅躺在那里一事不干?
觸摸這頁面,后果自負:那空白和清白的是你,不是這頁面。不過,你想去了解,什么也不會阻止你。你觸摸這頁面,仿佛用刀一劃而過,現在這頁面受傷了,一條彎彎曲曲的傷口張開,一個細細的切口。黑暗穿過它噴涌而出。
對第三只眼睛的指導
眼睛是一種視覺器官,第三只眼睛也不例外。把它睜開,它就看見,把它閉上,它就看不見。
大多數人都有第三只眼睛,但他們并不相信。F并不真的站在角落,把雙手插在大衣衣兜里面,等著光芒變化:F在兩個月之前就死了。他們說,這是我的眼睛對我們玩弄的把戲。光芒的把戲。
視覺和視覺之間有什么差異呢?前者聯系著它假設你看見了的東西,而后者則聯系著你沒有看見的東西。語言也并不總是那么可靠。
如果你想使用第三只眼睛,那么你就必須閉上另外兩只眼睛,然后均勻地呼吸,然后等待。這種方式有時候會起作用。另一方面,有時候你僅僅去睡覺。有時那樣也會起作用。
當你進行了足夠的實踐,你就不必因為這些預先的步驟而感到困擾。你也發現你看見的東西部分依賴于你想看著的東西,也依賴于你看著的方式。正如我所說,第三只眼睛只是一只眼睛。
有些人厭惡第三只眼睛。如果可能的話,他們就會將其清除掉。他們感到它就像是寄生蟲,蹲伏在額頭中心,以大腦為食。對于他們,第三只眼睛只會顯現出最糟糕的景象:洞口被毒氣殺死的燒焦的尸體,內臟被掏空的嬰兒,將軍們留下的足跡,而且,更靠近家,因為妒忌和貪婪而患上腺鼠疫的心臟,完全穿過任何人的背心和毛衣而閃爍發光。他們說折磨,也看見折磨。第三只眼睛可以是殘忍無情的,尤其是在受傷的時候。
但有人不得不看見這些東西。它們存在。別嘗試去抵抗第三只眼睛:它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別去管它,它就會對你顯現出這個真相并不是唯一的真相。有朝一日,你會醒來,萬物——車行道邊的石頭,磚石房子,每一塊磚,每一棵樹上的每一片葉子,你自己的身體,統統都將被照亮,從里面發光,明亮得讓你幾乎無法觀看。你將朝任何方向伸出手去,觸摸光芒。
那之后,因為沒有更多的選擇,就沒有更多的指導了。你看見。你看見。

蠟? 菊
我把手伸下去,抽起來的時候拿著什么呢?某種早熟的東西,一朵干枯的小白花,人們稱之為“蠟菊”。它在小路邊、公路邊被人采摘,靠近那露出石英的巖面,升起的太陽照耀到巖面上,照亮那塊巖石,就像照亮玻璃一般,就像通向光芒的入口。就在那時,世界成了你無法穿行、無法進入的東西。
那時,就在路邊任何寬敞的地方,你可以搭起帳篷宿營。帳篷是沉甸甸的帆布,發出瀝青味。其他人熄滅了篝火。幾乎沒有汽車,這是因為戰爭的緣故,戰爭在某處發生。紅色與橙色的毒菌鬼王筆,在那里一片片生長,紫苕子,氣味濃烈的雛菊,細小的黑螞蟻在花瓣上爬行。還有一條溪流,溪水呈淺褐色,清澈。
沒有什么事情可做,時間全在那里,無需將其充滿。我赤裸著雙膝,跪在潮濕的地面上,把手伸進時間的空缺之中,抽起來的時候拿著一把梗莖,光芒從溪流中反射著梗莖末梢,那些干枯的白花,早已永恒。
戰? 前
在戰前的舊日子,事情有所不同。在任何一天,你都可以在大約五點出去,走到碼頭的盡頭,幾番拋出魚鉤,就會釣到做晚餐或早餐的大眼魚,將其徹夜掛在樹枝上,那樣熊就不會夠得著。那時的熊還較多,會在伐木場周圍閑逛,你可以在傍晚走到垃圾堆去射殺它們。我知道一個人使用弓箭射擊,要是一擊未中,情況就不那么好了,盡管更像真正的狩獵,他也會追蹤血跡進入樹林。現在他們沒有伐木場了,也不會用曾經的方式來行事——曾幾何時,他們在冬天用馬把樹木拖到冰上,然后到了春天,他們就隆隆作響地拖著那些樹木迅速沿河而下,到達鋸木廠。那時使用的是弓鋸和雙刃斧,你再也沒法得到好工具了,一旦他們忘記怎樣制作那些工具,你就會花上好幾年來教會別人,沒有那樣的需求了。現在他們駕駛卡車和推土機開進去,將那個地方夷平,現場一片狼藉,到處都是樹樁和枯枝,留下的魚就不值一提了,總之,現在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乘坐飛機飛走了。印第安人也發生過什么,他們曾經從來不會在灌木叢中飲酒,在灌木叢中飲酒的始終是白人,印第安人在鎮子里飲酒,灌木叢對于他們太重要了,因此不會冒險在其中喝醉,當你喝得酩酊大醉,就會縱火。在那些日子,如果你在場滅火,那么每個人都會到場滅火。在風中,烈火會躍過樹冠,甚至會越過島嶼。為了阻止那場烈火,你會不休不眠地工作,你會揮汗多日。
現在他們為了獲得工作而故意縱火。沒有人在乎,這只是你在周末用快艇劃破水面之處。在戰前的舊日子,他們自己建造的木船,船上有一臺功率為五匹馬力的馬達。
太陽一如既往西沉,桃色的云,有一絲顫栗。這感覺就像是等待,但又不是。除了風沒有一絲聲音,細微的波浪在碼頭下柔和地緩緩移動。這里沒有人。離開小路一步,這里從不曾有過人,即便是現在,你也許還誤認為這一切依然可以得救。這是舊日子。這是戰前。
制作毒藥
五歲時,我就和哥哥制作毒藥。那時我們生活在城里,但不管怎樣,我們幾乎肯定會制作毒藥。我們將毒藥保存在別人房子下的一只顏料罐里,把我們所能想到的所有毒物統統都放在里面:毒蕈、死老鼠、也許無毒但看起來有毒的花楸果,還有我們存起來便于添加到顏料罐里面的小便。等到顏料罐裝滿的時候,里面的一切都有劇毒。
問題是,一旦制作好了毒藥,我們就不能把它留在那里了。我們得用它來干點什么。我們不想把它投進任何人的食物,但我們需要一個目標,一次實現。我們還沒有恨之入骨的人,這就成了困難。
我想不起最后我們用毒藥來干了些什么。難道我們把它遺留在那座棕黃色的木房子的角落下面了?難道我們把它扔向某個人,某個毫無惡意的孩子了?我們不敢把它扔向成年人。這是我腦海中真實的形象:一張流著淚水和紅色漿果的小臉,最后突然意識到那毒藥真正有毒了?要不,我們放棄了它,我記得那些紅色漿果順著排水溝漂走,流進涵洞,我清白無罪嗎?
首先,我們為什么要制作毒藥?我能回想起我們攪拌、增添所謂毒物的那種快樂,那種魔幻感和成就感。制作毒藥的樂趣幾乎就跟制作蛋糕一樣。人們喜歡制作毒藥。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你就不明白一切。
黑暗中的謀殺案
這是一種我只玩過兩次的游戲。
第一次是我五年級的時候在一間地下室玩的,一個叫做露易絲的女孩的父母擁有一座大房子,那間地下室就在那座房子下面。地下室里面,擺著一張有六個落袋的臺球桌,但我們大家都對玩臺球一無所知。那里還有一臺自動鋼琴。玩了一會兒,我們就厭倦了把打孔紙卷穿過自動鋼琴讓其演奏,觀看琴鍵自動上下跳動,就像你在看見死人之前的午夜電影中的某種東西。我愛著一個叫做比爾的男孩,那個男孩又愛著露易絲,另一個男孩,我記不起名字了,又愛著我。沒有人知道露易絲愛著誰。
于是我們關掉地下室的燈,玩起“黑暗中的謀殺案”,這就讓男孩們很快樂,因為他們可以用手摟住女孩的脖子,讓女孩們快樂地尖叫。這樣的刺激讓我們幾乎無法忍受,但幸好露易絲的父母回家了,他們問我們認為自己能勝任什么。
第二次,我跟成人玩這種游戲。盡管它在智力上更復雜,但同樣也沒有樂趣。
我聽說,曾經有六個正常人和一位詩人在一座夏季別墅玩這種游戲,那位詩人真的試圖殺死某個人。僅僅是一只無法辨別幻想與現實的狗介入,才妨礙了他行兇。關于這種游戲的事情,就是你必須知道在何時停下來。
這就是你玩的方式。
你把一些紙片折疊起來,放進一頂帽子、一只碗或桌子中心。每個人都抽取其中的一張。拿到寫有“X”那張的人是偵探,拿到畫有黑點那張的人是殺手。偵探離開房間,關掉燈。每個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直到那位謀殺者挑選出受害者。他既可以低語說“你死了”,也可以偷偷用手摟住一個人的喉嚨,進行好玩但又果斷地擠壓。受害人尖叫,倒下。現在,每個人都必須停止到處移動,謀殺者除外,他當然不想在尸體附近被人發現。偵探數到十就開燈,進入房間。現在他可以詢問除受害人之外的任何人,不準許受害人回答,因為他已經死了。除了謀殺者之外,每個人必須如實回答,而謀殺者必須撒謊。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玩一玩這種游戲。你可以說:謀殺者是作者,偵探是讀者,受害人是書。或許,謀殺者是作者,偵探是批評家,受害人是讀者。那樣的話,書就完全會成為場景調度,包括那實際上翻倒并打碎的燈。但是,玩這種游戲更有趣。
無論怎樣,在黑暗中的都是我。我對你心懷叵測,我正在密謀險惡的罪行,我正伸出手去抓住你的脖子,或許誤抓住了你的大腿。你聽得見我的腳步臨近,我穿著靴子,拿著刀子,或許是拿著一把手柄上嵌有珍珠的左輪手槍,無論怎樣,我都穿著鞋底很軟的靴子,即使我不抽煙,你也看得見我的香煙的那種電影似的微光,在房間、街道的霧靄中明明滅滅。當尖叫聲最終結束,你打開了燈,記住這一點吧:根據游戲規則,我必須總是撒謊。
現在:你還相信我嗎?
啞? 巴
無論是否說話:當你又說了太多那個再次出現的問題。又抓住一些名詞、一把名詞:看看他們怎樣將其挑選出來,那些詞語的顧客,到處都捏一下,看看它們是否被擦傷了。動詞的情況也不好,他們將其上緊發條,放開,在桌子上面亂扒,重新把發條上得太緊,彈簧斷了。沒有上緊發條的原因,沒有那里面發綠、不屬于你、被擦傷的詞語,沒有螞蟻爬滿它上面,沒有這種螞蟻的侵擾,你就無法獲得另一首彈簧的詩。這是一個市場,斑斑點點。你怎樣清洗一種語言呢?難聞的氣味開始散發出來,你能聽見低吼聲,有什么東西再一次被吃掉。你的嘴巴摸起來腐爛了。
為什么要把自己牽扯進去?你還不如坐在一邊,坐在雨篷下面的人行道上,用雙手捂住嘴巴、耳朵和眼睛,把一個杯子放在前面,人們將會或者不會把幾個小錢扔進去。他們認為你不能說話,但他們為你感到惋惜。然而,你等著那個詞語,那個最終正確的詞語。一個復合詞,生活的一代人,泥淖和光芒。
(責任編輯:龐潔)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 加拿大著名小說家、詩人,生于渥太華,曾在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畢業后當過市場調查員、出納員,后來在一些大學任教。她從1956年開始文學創作,迄今已出版了詩集《圓圈游戲》《那個國家的動物》《蘇珊娜·穆迪的日記》《強權政治》《你是快樂的》《兩頭的詩》《真實的故事》《無月期》《焚毀的房子中的早晨》《門》等多部;長篇小說有十余部,此外她還寫過不少短篇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她擔任過加拿大作家協會主席,多次獲得國際國內文學獎,還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董繼平 重慶人。兩屆諾貝爾文學獎、四屆普利策獎得主作品譯者。少年時代開始文學創作,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轉向文學翻譯,在國內多家文學期刊上主持譯介外國詩歌。獲得過“國際加拿大研究獎”;參加過美國艾奧瓦大學國際作家班,獲“艾奧瓦大學榮譽作家”;擔任過美國《國際季刊》編委。譯著有外國詩集三十余種,自然文學及散文集二十余種,包括梭羅的《瓦爾登湖》《秋色》,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鳥的故事》,繆爾的《夏日走過山間》《山野考察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