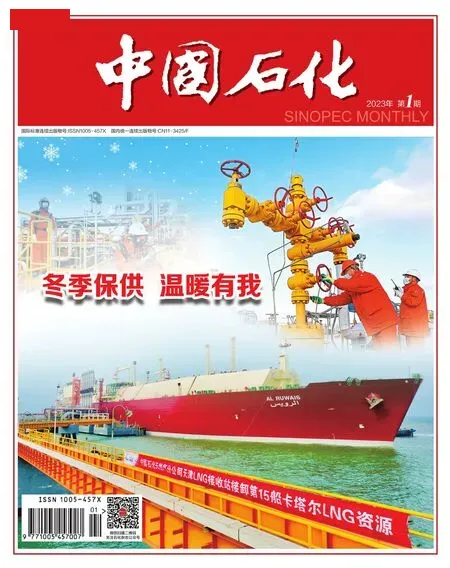河口會戰的激情歲月
□王守華

1972年12月27日,河口埕17井井廠被洪水包圍,器材運不進來,為早日把井固上保住油井,鉆井二部3211隊職工在冰水里人拖肩扛運套管。網絡供圖

1973年,河口埕東油田1807隊職工在井場新井立井架。網絡供圖
我看過數不清的電影,卻有一部電影《奠基者》使我難以忘懷,這是因為它帶我回到了那激動人心的河口油田大會戰的激情歲月。
1969年12月參加工作的我,有幸與地調225隊的工友們一起參加了河口油田石油會戰。那是1970年初秋,幾萬名勝利石油人唱著《石油工人之歌》,在黃河入海口的埕口地區打響了河口石油會戰的炮聲。勘探隊的炮聲、鉆機的隆隆聲、汽車的喇叭聲伴著《石油工人之歌》的歌聲,猶如萬人齊唱的戰歌,在黃河三角洲的大地、上空激蕩。戰歌喚醒了沉睡的海灘,海灘沸騰了,黃河三角洲沸騰了,整個黃河入海口人歡車鳴,勝利人“寧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壯語響徹云霄。這邊是鉆井隊在泥水中搬遷,晝夜鉆進,那邊海溝邊的放炮車是勘探隊在測點上放炮勘探,到處是轟轟烈烈的會戰場景,使我至今難以忘懷。
埕口“三寶”熱烈“歡迎”
山東省東營市河口區的埕子口(現在的東營市河口區最北端的海灘)地處黃河入海口,主干線與黃河入海口分線二河地段,茂密的蘆葦、紅柳、怪柳如原始森林,海溝縱橫如江南湖泊,秋天的黃須菜猶如紅紅的地毯鋪滿海灘,好一片富饒美麗的原始濕地!
我們地調225隊的駐地緊鄰二河,住的是用雜木桿扎架,用葦箔圍起當墻,外面糊上泥巴的簡易房;喝的是二河里經過沉淀的黃河水。傍晚,當工友們興致勃勃地欣賞遠處海平面上美麗的晚霞時,被人們戲稱為埕口“三寶”的蚊子、牛虻、小咬也嗡嗡地歡叫著加入到欣賞的人群中,好像在熱烈地歡迎初到的“客人”,可它們特殊的歡迎方式,卻讓人生畏。成群的“三寶”用尖嘴鉆透人們厚厚的帆布工服,貪婪地吸允著工友們的血,讓人防不勝防,防蚊藥也無濟于事。工友們只好退避三舍,鉆入蚊帳,商量起明天的施工安排。
少將指揮親臨前線“參戰”
會戰中,勝利油田(那時叫923廠)各級領導親臨會戰前線,與職工同吃同住同勞動,率先垂范,帶頭大干,親身參與指揮著石油勘探會戰,就連當時的油田“一把手”、少將指揮(在部隊時是少將軍銜)劉佩榮也親臨前線“參戰”。有一天,劉佩榮來到地調225隊看望參加會戰的將士,到現場后他便挽起褲腿投入到放線班的放線工作中。在毒辣辣的太陽下,在海灘的草叢、泥潭、溝壑中,劉佩榮深一腳淺一腳地與職工們一同放線收線,泥水濺滿一身,他也全然不顧。
領導率先大干是無聲的沖鋒號,職工們的戰斗精神更加高漲,超額完成了當天的生產任務。在晚間的大會上,劉指揮高度贊揚了職工們不怕苦、不怕累、無私奉獻的勝利精神和“寧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鐵人”精神。
測量組首創海灘“作戰”計劃
如果說地調隊是石油行業的先鋒的話,那么測量組便是先鋒的尖兵。作為尖兵的測量組要走在勘探生產的前邊,這就面臨著未知的風險,尤其是在生疏的海灘施工,更是如此。為此,測量組在“出征”之前集思廣益制定了施工“作戰”計劃和海灘施工各種險情應急預案,這在地調隊海灘施工中是首創。
面對潮起潮落、溝壑交錯,蘆葦、紅柳、怪柳如原始森林的復雜壞境,周密的測量施工計劃和符合實際的海灘施工險情應急預案,使測量組能躲過潮漲時間段進行施工,化解了一次次危險,安全優質地完成了勘探測線任務。
新員工“柳樁陣”掛彩不下“火線”
在地調225隊的隊伍中有幾個剛從石油大學畢業的新員工,他們懷著為祖國獻石油的激情與夢想,風塵仆仆地投身會戰大軍中,從此便開始了他們與艱苦環境為伍、與野外勘探為伴的石油勘探生涯。
我們測量組的袁寶鼎便是新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中的一員。他高高的個子,白凈的臉,總是笑呵呵的,與工友們一塊兒鏖戰在海灘上,為埕口石油會戰忙碌著。每次出工他都認真仔細地做好準備工作,到達工地跑前跑后忙個不停,無論是站前尺、后尺,還是觀測、記錄,他都一絲不茍,嘴上還總是唱著歌兒,尤其是那首《我為祖國獻石油》的歌曲,是他每天的保留曲目。袁寶鼎總是歡快地唱著歌兒,沿著測線在溝壑、蘆葦、紅柳、怪柳中穿梭,惹得海鷗、白鷺等鳥兒們圍著他鳴唱,與他合奏著勘探會戰的美妙“樂章”。
有一天,施工的測線穿過一片怪柳林,到處是茂密的怪柳,還有腐朽的怪柳茬。穿著雨鞋的袁寶鼎在測線路上走著,突然一腳踩在了怪柳茬上,尖尖的怪柳茬刺穿了他的雨鞋,扎進了腳心,鮮血染紅了雨鞋。同事見狀立即幫他拔出怪柳茬進行包扎,還勸他回去休息。可袁寶鼎輕傷不下火線,他穿著帶血的雨鞋繼續沿著測線走去。在陽光照耀下,他一瘸一拐的身影,顯得笨拙卻高大。
人機組合大戰淤泥灘
由于是在海灘施工,勘探隊施工車輛大都配的是前后加力的越野性能強的車,以防車輛陷進淤泥。但在渤海海灘潮起潮落,海溝時而有水,時而無水,灘涂看似平緩,實際是淤泥,所以,時不時有車輛陷入泥潭。
一次,我們的一輛水罐車陷進了海溝的泥潭中,我們采取了汽車加力、人工鋪草、拖拉機拖等措施,不但沒有奏效,反而使車越陷越深。最后只好調來了大吊車。但吊車自重很重,陷入泥潭的水罐車周圍盡是淤泥,吊車無法靠近。怎么辦?大家集思廣益,想出了鋪一條草板路的辦法,即用葦草、雜木桿襯底,上面再鋪上木板,就像在泥潭上架起一座“浮橋”,讓吊車靠近水罐車實施起吊。
說干就干,領導從會戰指揮部調運來雜木桿、木板,葦草就地割取,大家挽起褲腿衣袖,有的用鐵鍬、用手挖車輪底下的淤泥,往里面墊草、雜木桿,有的人用木板鋪從吊車通向水罐車的路。
沒有怨言,只有默契的配合和有序的搶修,泥水和汗水和成稀泥濺滿了地調隊干部職工的身上,他們一個個都成了“泥猴”;滿臉的泥水,讓他們用力時露出的兩排牙齒顯得格外白。一瞬間我仿佛看見一群戰天斗地的英雄雕塑。
經過大家一個多小時的努力,通往水罐車的“浮橋”路修好,當大吊車吊起水罐車的時候,人們跳著發出的歡呼聲響徹黃河入海口的天空,像是向大自然發出挑戰:海灘、泥潭你們聽著,再大的困難也嚇不倒我們這些為祖國石油而戰的石油英雄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