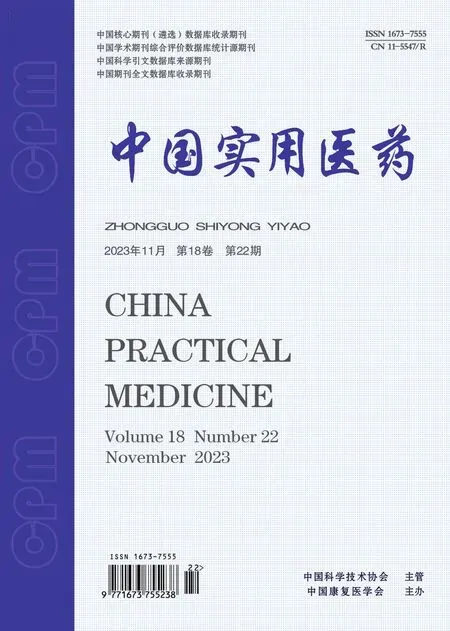中藥治療惡性腫瘤原理再探討
魏龍艷
1 中藥物種基因與治療疾病的關系
1.1 基因是人體生長發育的本原物種 基因是細胞核染色體具有遺傳效應的DNA 片段, 是調控生命形態性能的基本遺傳單位, 儲存著種族、血型、孕育、細胞生長、凋亡等生命信息, 是細胞分裂、復制和蛋白質合成, 決定人的生長、發育、衰老、疾病與死亡等一切生命活動現象的生理過程, 決定著人的健康生死內在因素, 有著自我復制保持生物特征的性能。基因突變、變性、缺乏、免疫、調控能力下降, 是導致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因此, 基因是一切生物遺傳生命本原的活種物質。中藥也是從古老物種基因遺傳下來的物質, 具有強大生命力, 完美的保留了調控人類生長發育的基因。中藥治病遵循“藥食同源”的原則,彌補了人類遺傳基因退化缺乏與免疫力下降的不足。中醫通過包括“四氣”、“五味”、“歸經”、“升降浮沉”等作用方式的內涵規律和經驗的總結, 適應于人體所需基因的補充、激活、糾偏、修正作用, 從物種基因的根本上解釋了中草藥治病原理。上海沈朝斌教授就是從中藥煎煮液中找到了黃芪補氣的微小核糖核酸(miRNA)基因, 解釋了黃芪補氣培土益肺的原理[1]。沈氏指出:“miRNA 是生物進化過程中最早產生的, 比脫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都要早, 所以miRNA 在生命起源時是植物與動物共有的。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基因受多重影響而發生突變或病變, 而導致疾病的發生, 這就需要補充原始的基因修飾自身不好的基因, 從而恢復到原來的健康狀態”[2]。“如果人體疾病靶基因上的信息能夠被吃下去的某些基因片段改寫, 使疾病基因的表達被抑制或直接被降解, 自然會‘藥到病除’, 就是基因調控作用”。沈氏從基因分子實驗的說明是解釋中藥作用原理的最好例證。
1.2 基因學說與腎藏精理論探源 中醫理論關于“腎藏精, 主生殖與發育, 主骨, 生髓......”, 無不道明了基因與腎系藏象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關系。中醫“腎”的概念, 涵括了現代分子醫學基因遺傳, 儲存人類種族、繁衍的全部信息, 構造人體合成蛋白質、調控細胞分裂復制, 催生個體生命的形成, 疾病與死亡等一切生命活動現象過程, 是人體生長發育的先天原始基因和后天遺傳基因的物質, 即中醫理論的陰陽水火交蒸,能量氣化源泉之所在[3]。因此, “腎藏精”與基因調控生長、發育、衰老、病死規律密切相關。如惡性腫瘤就屬于基因失去有效調控, 不能控制細胞分裂、復制過程才出現細胞組織“突變”的疾病。從發病學年齡看,腫瘤多起病于40 歲左右男女, 根據《內經》對人體腎氣發育關于“男子五八腎氣衰, 發墜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 面焦, 發鬢頒白;女子五七陽明脈衰, 面始焦, 發始墮;六七三陽脈衰于上, 面皆焦, 發始白”生長發育衰老規律的論述, 說明人一般在35~40 歲開始陽氣逐漸下降、腎氣虛衰的生理性衰退現象, 此時基因免疫系統容易出現變化或崩潰, 不能有效地調控細胞的生長, 容易出現組織突變, 發生惡性腫瘤[4]。
1.3 中藥治病原理, 即是基因補充修復的作用過程中藥治病原理是“藥食同源”地利用天然物種基因補充、激活、糾偏、修復的作用過程。①人類起源是從海洋生命到陸地, 從樹上到地下, 從狩獵到農耕, 從猿人到智人, 直到現代人, 是個基因遺傳進化的過程;②人類生長形成的個體, 通過攝取動植物補充機體所需能量,不斷進行基因補充, 從低級到高級逐漸完善其進化質變的過程。起初的生活習性和飲食結構多為食草、果蔬、少肉、五谷雜糧, 遠遠不同于現代人生活飲食結構, 處于“營養過剩與營養不足”并存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其“營養不足”, 即是指人體正常發育的基因的缺乏、退化之不足;③大量研究資料表明, 現代人已不能適應現代飲食結構, 現代人之所以多病, 根本原因是基因失去對人正常生長發育的調控和免疫抗病能力[5]。如現代人體體溫從平均37.0℃下降到36.6℃(免疫抗病能力下降30%), 是因為人的勞作運動減少, 肌肉產熱能量不足;自然生態遭到破壞失衡, 人體需要的營養基因攝取不足, 導致原本的基因退化、缺乏、免疫力下降的結果;④中藥是生長在地球上有著古老強大生命力遺傳基因保留下來的物種, 有著完整的遺傳基因片段和各種適宜生長的微量元素, 雖然中醫藥理論上有著“寒熱溫涼”、“四氣五味”藥性之說[6], 但毫無例外的真正治病原理, 就是天然中藥中原始物種基因在人體不斷得到補充、激活、糾偏、修正、修復、自愈能力的結果。
1.4 惡性腫瘤辨治的標與本 中醫理論體系以人的“整體觀念”為本, 以疾病的證候性質進行“辨證論治”為標, 即人的整體是本, 疾病是標, 整體是本, 局部是標, 人的整體性是固定之本, 靈活地辨證論治是不定的標。現代醫學對“細胞癌變是基因突變或基因功能失調結果”的論述, 可以說任何疾病的發生, 都是人體基因免疫調控、修復能力失衡變態的結果。腫瘤的定義是人體在內外有害因素作用下, 使細胞組織器官遺傳基因DNA 損害, 喪失了生長調控機制和功能, 產生“以細胞過度增殖為主要特點的新生物”[7]。其病理機制是人體在內外有害致癌因素作用下造成DNA 修復調節功能損害, 從而激活原癌基因、滅活抑癌基因和凋亡調節基因的表達異常, 使調控細胞組織生長機制和功能喪失, 發生異常轉化或過度增殖突變而形成惡性腫瘤, 可見惡性腫瘤發生的本質是基因性疾病。西方醫學對惡性腫瘤的治療, 主要從生物細胞分子學局部點位入手, 著眼于微觀細胞的“物”質上, 在思維方式和行為認知方面, 并不認為細胞是構成人體生命的整體性, 不是從人的整體屬性的細胞基因本質原因上著眼,將“人”和“細胞”分離, 只是講究一味局部的毒殺腫瘤細胞, 就避免不了“腫瘤細胞殺完了人也就去了”的結局。思維邏輯認知觀念的迷失, 必然導致錯誤方法的錯誤結果。
2 腎虛為本, 是惡性腫瘤論治的基本原則
惡性腫瘤本質上屬于細胞突變基因性疾病, 是病理機制的本質現象之本, 所謂痰濁毒瘀寒熱氣血諸邪夾雜為標, 都是自由基代謝產物和使DNA 基因受到損害的結果。因此, 從“腎虛為本”的觀點入手, 是中醫藥治療惡性腫瘤論治的綱領性法則。在實施治療的選方用藥上, 圍繞以“腎”屬系統功能的生理病理及其相互關系為中心, 注重藥物的歸經、性味和升降浮沉的作用方式, 以及臟腑經絡表里、五行母子生克、虛實補瀉關系。如腎與膀胱是相為表里的功能關系, 腎在臟屬水, 藏精, 為生命源泉之性能, 主生殖與生長發育, 其臟腑經絡功能部位受納自然界陰陽物質精華, 外行背部受太陽膀胱經諸脈之陽氣溫煦, 內斂行于腹部受諸臟經脈之陰精滋養, 通過水火交蒸(水濕精津與人體溫度發生生化反應, 即包括現代微觀醫學細胞質、核和染色體、DNA 基因調控細胞分裂、復制、紡錘體形成等生長發育系統生理功能)氣化變物, 催生細胞組織器官形成人體, 是生命新陳代謝的核心樞紐。中醫理論上適于咸味歸腎藥物, 分辨虛實以行補瀉之法;腎水以肺金生我者主水, 尊肺主氣, 四布朝百脈和衛氣屏障, 上下內外宣發肅降溝通、調節水道功能為母, 適于味辛歸肺藥物, 虛則補之;以我水生木之肝, 化精涵木使之藏血, 且主疏泄, 克我脾土運化而化生萬物, 遇實則瀉之等。
3 重視利用藥材物種基因意識
動植物藥材之所以能夠經過長時期的四季寒暑、風吹雨打留存下來, 是因為中藥有著完整的遺傳基因和各種適宜生長的微量元素。如紅豆杉就是史前植物基因遺傳物種, 其抗癌是經科學實驗研究證明, 具有天然植物藥材性質, 屬于“細胞毒”類化合物“紫杉醇”藥物, 是繼阿霉素等抗癌藥之后, 至今發現的唯一能夠調控癌細胞生長, 可作為廣譜、高效、治療多種晚期惡性腫瘤的天然植物藥。治癌原理可能就是紅豆杉基因能與微量蛋白質結合, 靶向性的作用于細胞分裂復制的G2期和M 期, 阻止細胞有絲分裂及紡錘體生成,抑制癌細胞分裂增殖、轉移與擴散, 而不影響腫瘤細胞DNA 及RNA 合成而治療腫瘤, 可能正是因為紅豆杉具有天然植物基因性質而很少有治療惡性腫瘤副作用的優勢, 被譽為“治療惡性腫瘤的最后一道防線”。
4 論治組方應注重藥材基因特點
惡性腫瘤公認的病理機制是“細胞基因突變與功能失調”。中醫理論認為其病位主要在腎, 相關肺、肝母子關系等整體相互聯系的次要臟屬, 因此在治法配方上, 一是以“補氣扶正, 益腎增免”為主, 配伍具有鮮明動植物基因特色藥材, 如歸經肝腎的脊椎動物龜甲類、無脊椎特殊環節生物的地龍、沙漠植物寄生生長的肉蓯蓉、真菌繁殖的靈芝等一組具有強大物種基因的特色藥材, 與經科學證實的抗癌專屬藥材組成配方起主要作用的為組方主藥(如紅豆杉);二是根據寒熱痰濁毒瘀氣血夾雜辨證性質, 分別選用清熱、溫化、活血、利濕、解毒諸藥。在諸邪之中, 以“寒凝氣血”性質為多, 因為腎陽命火本虛(基因功能下降), 不能溫行氣化使物以常形, 所致氣血寒凝而贅生腫瘤, 符合惡性腫瘤“寒凝血瘀”的病機特點, 其病程中伴發的陰虛火旺的“發熱”, 也是“真寒假熱”現象。因此選用具有溫性扶陽之藥是配方中不可缺少的藥物(如肉蓯蓉配伍砂仁, 性平味咸入腎溫里, 肉桂峻熱傷陰, 只宜少量作引使用);三是“補氣、益腎、解毒”三者是基本固定的用藥模式(簡稱2+1)法則。“補氣益腎”是不變病機之本, “解毒”是夾雜病邪性質靈活辨證過程之標[8]。鑒于癌變細胞組織是諸邪所化之毒最終損害機體的結果, 因而“解毒”是貫徹始終的治療法則, 可根據病邪證候性質, 分別選用清熱、溫陽、化痰、利濕、活血、解毒等性質的中藥靈活辨證組方論治。
5 中醫藥抗癌保健需注意適于患者
源于古老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是“天人相應”,運用宇宙觀的整體觀念與個體化證候的辨證論治診療疾病, 與西醫思維認知有著根本的不同。中醫對惡性腫瘤的認知, 從本質上并不單看作是一種病, 而看作是某種病的一個癥狀, 或一種病的結果, 而不是惡性腫瘤發病起源的病因, 治療上不只是要設法消除疾病, 而是注重消除疾病的病因, 針對疾病所反映的客觀證候信息進行辨證論治, 真正消除疾病的關鍵在于人的“正氣”(基因)的調控、修復、自愈抗病能力。從中醫整體理論而言, 就不能、也沒法、局限地存在治療“惡性腫瘤”一說。因此, 癌癥在古中醫疾病學上屬于“積聚”、“癥瘕”等范疇, 屬于中醫診療的慢性疾病。后受西醫影響, 出現了以肺、胃、肝、腸等組織器官命名的各種“癌癥”診療名詞。現代中醫藥學家雖然也建立起了“中醫腫瘤學”, 還出版了不少的書籍[9], 基本上是西醫學者做中醫的文章, 沒有脫離西醫的思維模式、體例, 不過是“結合”了一些中醫的論述而已,都還是強調以“細胞病理學為依據”。目前中醫藥進入保健抗癌行業還是處于舉步維艱的狀態[10]。為避免醫患糾紛和言行違規, 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為此建議:臨床接診以“知情自愿”為原則, 可以“保健抗癌防病”進行中醫藥服務的口徑接待患者;行為方面把握“同情而不宜過度熱情, 做到患者為客, 肅敬禮貌,醫患關系分明”, 營造情同家人的人文氛圍, 以示尊重患者隱私, 減輕患者心理壓力;要把“心理疏導與科普培訓”做到有專業專人日常健康教育內容, 作為臨床工作重要組成部分, 貫穿于保健康復治療過程的始終;注意患者心理情緒穩定開朗, 必要時首先進行心理治療與疏導, 鼓勵樹立戰勝病魔的意志, 共同制訂康復方案。在不影響治療順利的原則情況下, 不排除、不評價患者與其他方面建立的治療康復關系;建立醫患信任合作關系, 簽訂有家庭監護人約定諒解保障備忘錄, 遇到心理阻抗、不信任或經過一定時間治療感到用藥無效時, 即行終止治療活動, 必要時就此通過公證以取得有效的法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