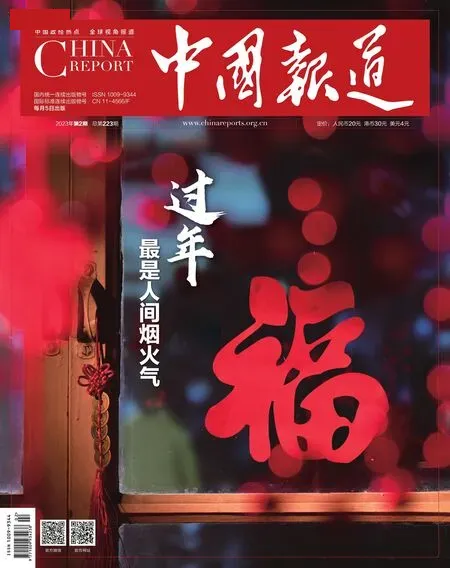中國工作隊“拯救”吳哥窟
文|郭熙賢

1861年,法國生物學家亨利·穆奧在柬埔寨暹粒的密林中尋找熱帶動物時,無意中闖入了一片神秘恢宏的古建筑群,揭開了消失的吳哥城的秘密。
吳哥古跡與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萬里長城和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并稱為“東方四大奇跡”。吳哥城被柬埔寨人民視為象征民族精神的文化符號,自1953年獨立以來,柬埔寨的每一屆政權都在國旗上使用吳哥形象。
1992年,吳哥古跡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超過20個國家加入了柬埔寨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發起的“吳哥古跡保護國際行動”,中國也在其中。2010年,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組建的“吳哥古跡保護中國工作隊”完成了周薩神廟的10年保護修復項目,并正式展開了對吳哥遺址中最雄偉且具有典型特征的廟山建筑之一——茶膠寺的保護修復工作。
困難重重的修復之旅
柬埔寨吳哥古跡是高棉帝國留下來的9—14世紀的寺廟、城市、水利工程、道路、橋梁等遺跡以及大量的考古遺址,后來因為歷史的原因被遺棄,森林逐漸將它覆蓋。今天我們只能通過壯觀的石塔、精美的石雕想象千年前高棉王國的盛世景象。
從大吳哥城勝利門向東走大約一公里,會看到一座以印度教須彌山為意象的建筑,這就是茶膠寺。茶膠寺又名達高寺,意為“祖先的水晶塔”。茶膠寺處于高棉建筑形制的轉型時期,新舊建筑元素同時出現,具有“承上啟下”的特殊地位,對于研究高棉文明有重要作用。
當第一次進入茶膠寺現場的時候,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文物保護工程師金昭宇就被這里雄偉的氣勢所震撼,卻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破敗不堪的廟宇,滿地的碎石,這對于從未接觸過廟山建筑的中國考古專家來說無疑是個挑戰。
擺在面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器械的使用。茶膠寺是吳哥建筑中第一座全部由砂巖建成的寺廟,長期的高溫濕熱和病蟲害,讓很多構件都出現了松動坍塌,基臺難以承受大型機器的重量。
整體建筑是逐層收進的方形須彌壇,共有三層平臺,頂臺上是像骰子的五點一樣排列的石塔。從基臺外側地面至最高處高度為43.3米,上須彌壇的一層層石階幾近90度垂直,工作隊想要上到石塔需要手腳并用。施工場地狹小,高空作業風險高、難度大,在工程開展之前,工人們不得不在建筑外圍手工搭建腳手架,量身定制每一個鋼結構支護,最大程度保護建筑本體。
初到這里的游客可能會有些困惑,這處建筑為什么只有石塊堆疊,沒有精致的裝修和雕刻。這也正是茶膠寺在吳哥古跡中最獨特的價值。它始建于公元975年,是阇耶跋摩五世時期開始建造的國寺,但是未能完工。
由于當初建造的時候,工匠是將大小不一的石頭堆疊后,再切割打磨成想要的外形,因此石構件都是不規則的形狀。石塊之間無灰漿或其他黏合劑,僅靠石塊之間的結構和重量彼此結合在一起,墻壁的表面還沒來得及雕刻佛像和花紋。在吳哥古跡眾多繁復的浮雕中,獨特地呈現出粗獷樸素的原始美,但這也對修復工作造成了障礙。
茶膠寺的原石有一萬多塊,有的深埋地下,有的碎裂磨損,大的重達4噸,小的僅有5厘米長,工作隊需要找到所有的碎石,并照原址用電腦畫出圖紙,將石塊重新排列組合,一一填充。
“每一塊石頭都是獨一無二的,有一塊的位置不對,都會導致堆疊起來的縫隙越來越大,最終無法復原。”金昭宇向記者解釋。他們需要先測量、標記,再進行尋配、歸安。有時為了避免歸位后出現問題,他們需要先在地面上反復進行拼裝實驗。“這就好比是復雜的拼圖,卻并不是游戲那么簡單。”金昭宇感慨。
“傳統”與“創新”的碰撞
大量石刻裝飾和施工痕跡被保留,茶膠寺具有獨特的建筑風格。想要復原這種缺失的美就需要在“傳統”與“創新”之間找到平衡。
金昭宇表示,茶膠寺的建筑格局與建造工藝,在了解吳哥建筑方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對于客觀、科學、全面地研究吳哥歷史有重大意義。中國工作隊被寄予了厚望。

中國援柬吳哥古跡保護工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先后修復了周薩神廟和茶膠寺。圖為中國修復的周薩神廟。 攝影/滕妍妍
由于年代久遠,有些石塊難以找到或已經碎成粉末,需要用和茶膠寺原材料相匹配的新料進行填補。為了盡可能展現原始的模樣,工作隊找遍了周邊的石料廠。找到石材樣本后,他們還需要在項目附近進行一定周期的極端天氣實驗,記錄比較石材的微小變化,選擇最適合的進行補配。
在不影響建筑整體復原的情況下,專家們選擇最大程度保留現有殘缺,將整個修復工程中新增配的石材比例控制在15%以內。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館員袁濛茜說:“文物修復并不是要把未完成的做完,而是要展現真實的歷史,保留建筑的靈魂。”
山花是寺廟塔門上的石構件,通常由幾塊石頭拼接而成,并且刻有精美圖案。之前的修復案例往往通過打錨桿的方式,在石頭上鉆孔,達到串聯構件的目的。但暹粒極端濕熱的氣候會加速錨桿膨脹和老化,還會對建筑本體造成傷害。為此,中國工作隊反復研究,想出了在石頭外側設置拉桿進行加固的方法,雖然對美觀有一定影響,但能夠達到對建筑的最小干預。這項創新的工藝也得到了保護和開發吳哥遺址國際協調委員會(ICC-Angkor)專家組的認可。
工作隊還在鋼結構和石材接觸的表面加入橡膠以防止對文物產生損壞。這些可逆的防護措施,既保證了文物修復的質量,也為后人更先進的技術應用留有余地。金昭宇說:“文物是有生命的,我們的責任就是延續和保護它們的生命。”
2022年11月10日,李克強總理參觀了中柬文化遺產交流合作30年成果展,并出席了茶膠寺修復項目的實體移交儀式。中國工作隊經過夜以繼日的努力,終于讓古跡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文化交流的平臺
文物有國界,但文化沒有。在“文物醫生”的眼中,這些沉寂許久的文化瑰寶在通過他們的手,向世人講述著千年前的故事。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研究員劉漢興表示,每接觸一個項目,最先做的準備就是學習。學習文物建筑背后的歷史、宗教和文化內涵,學習傳統的工藝工法,還要學習當地的語言與民俗。
剛到暹粒的時候,工作隊只能和柬方的工作人員用英語簡單溝通,但后來隨著交流的深入,他們和當地居民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工作閑暇時,他們會討論李小龍、甄子丹,還會學習地道的柬語表達。有工人的家中舉行婚禮或老人壽辰時,還會邀請中國專家去參加。
中國與柬埔寨的交往源遠流長,元代時的周達觀作為文明的使者出使吳哥,并撰寫《真臘風土記》,為后人研究吳哥歷史提供重要資料,今天中國工作隊再一次成為文明溝通的橋梁。金昭宇表示,與當地人交流的過程就是體會歷史文化的過程,“我們將被打斷的文明脈絡重新連接起來”。
中國在吳哥考古公園設立了茶膠寺管理與展示中心,向游客展現中國隊的工作成果與保護理念,深化中柬雙方的文化交流。同時設立中國柬埔寨吳哥古跡研究中心,開展長期的古跡調查與研究工作。這成為中國開展國際文物保護研究和國際合作培訓的重要平臺。
在修復茶膠寺的過程中,中國工作隊也幫助柬方培養了一支文物保護工程技術團隊,提高了當地工匠的就業能力,創造了就業機會。同時推動當地旅游業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和環境整體治理。
“我們不只要修復文物,更要發揮文化遺產的潛力,走一條‘研究+保護修復+展示利用’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不僅考慮到文化遺產的保護,還要充分利用并兼顧當地社區協調發展,讓當地人民真正從項目中受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向東表示。
2019年,柬埔寨政府將遺產核心區域的王宮遺址交給了中國。項目不僅要對文物建筑進行修復,還要建造實驗室和展示中心,幫助柬埔寨在王宮遺址保護、旅游需求和社會發展等多方面實現可持續發展。

2018年7月9日,中國—柬埔寨政府吳哥古跡保護工作隊成員正在進行茶膠寺保護修復項目的結項收尾工作。
李向東表示,中國在文物保護與研究領域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加深,從最早的參與者之一到如今形成吳哥保護的“中國模式”,中國隊終于站在了舞臺中央。
中國在吳哥古跡保護領域取得成就的背后是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力量的發展。近30年來,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中國在柬埔寨、烏茲別克斯坦、尼泊爾、蒙古等6國先后開展11項文化遺產保護修復合作項目,促進了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推動了人類對文明的探索與思考。
中國文物保護工作者在柬埔寨的文物修復之旅還在繼續,挑戰也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