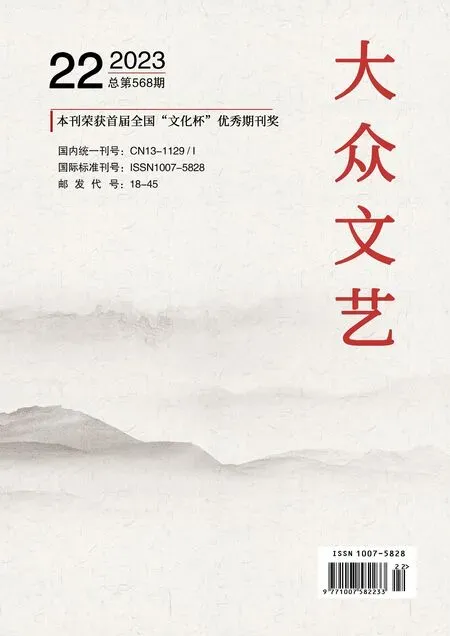山西民間信仰區域特點初探
馬雪純
(太原師范學院,山西晉中 030619)
人類從誕生之初就要受自然條件的制約,生存環境對生存者有著天然的、絕大的制約作用。民間信仰的起源往往出于人類最樸素的需求,而在漫長的人類發展史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始終是最重要的議題。由于地理環境的制約,一定區域內人類無法解決的自然問題,往往假托于神,促成了各種民間信仰的誕生。不同的地域發展而來的形色各異的民間信仰成為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人類學都極為關注的話題,社會史視角中大量運用施堅雅、杜贊奇、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論對民間信仰進行研究,對于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的解讀也紛紛出現。美國地理學家詹姆斯認為,“全部歷史都必須用地理觀點來研究”①[1],民間信仰與地理學息息相關,它的地理學視角當然也不可或缺,張偉然、藍勇、張曉虹等人已經開始從歷史文化地理角度進行研究,日、美學者對此也有深入探討。民間信仰的變遷和地理分布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一定區域內氣候、地形、物種、植被及地方文化等地理要素,有助于了解歷史時期該分布區域內的人地關系。通過對民間信仰的追本溯源,可以反推出歷史時期人類曾經面對過的、無法解決的自然問題,從而對歷史時期的自然環境有更全面更具體的認識。
山西向來被稱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存在著大量、多種類的民間信仰,明清山西地方志中所載祠廟結合留存現狀及發展歷程,反映出山西民間信仰所呈現的獨特區域特征,其表里山河的地貌特征與干旱少雨的氣候條件對山西地區民間信仰的形成與傳播都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一、古圣先王信仰長期留存
山西作為最早的文明發祥地之一,古都林立,作為早期中國的中心地帶,山西留存了許多古老的帝王崇拜,或因封地、墓地,或因事跡流傳。《漢書·地理志》對河東民風的描述“其民有先王遺教”②。[2]厚重的文化積累之下,先民們形成了對造福百姓的君王、士大夫、地方官吏以及杰出人物的敬畏和信仰,封閉的地理單元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為傳統信仰的保存提供了條件,此類信仰也只有在山西才有條件產生和存在,對古圣先王的人物崇拜在山西占比極大,成了山西區域性的文化特征。
上黨地區地處高處“居太行山之巔,與天為黨也”③[3],是古史傳說記載的集中地,其密度之集中、內容之詳備遍及上黨各山各村落。例如《澤州府志》載,“炎帝嘗百草至羊頭山得秬黍”,《長治縣志》《山西通志》對羊頭山和炎帝也均有記載,在傳說區域也相應地出現了伏羲、女媧、炎黃等的信仰崇拜,炎帝信仰在晉東南地區廣為流傳,當地的神農城、神農井、五谷廟等遺跡與眾多傳說一同構成了龐大的炎帝傳說信仰圈。神農和黃帝除了是古帝王之外,還有其對于醫藥的貢獻也是受到后人崇拜的原因。
相傳“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平陽、蒲阪、安邑的具體位置學界仍有探討,但都位于山西已基本沒有爭議,是以堯、舜、禹在山西皆有祠廟且數量較多。其后較為多見的還有湯王廟,“商湯祈雨桑林”的傳說,陽城作為傳說中的祈雨之地,也成了湯王信仰的中心,并在晉東南一代廣泛流傳,留下了眾多的廟宇和碑刻。而作為晉國故地,晉文公廟也多處存在。后代君王,常以山西為龍興之地,漢文帝、唐太宗,在太原、霍州等地存有祠祀,北魏孝文帝也在晉中區域多地建有祠廟。
除賢明君王外,忠義臣子列為祠祀的數量也相當之多,從比干、箕子到伯夷、叔齊,賢良忠臣多有所祀。在山西,春秋時期的晉國所祀忠臣有二十位左右之多,有輔佐晉文公的狐氏父子、介子推、先軫,有藏山護孤的趙盾、程嬰、公孫杵臼,還有俠士靈輒、提彌明、豫讓,大夫尹鐸、荀息、竇鳴犢等等。此后歷代名臣如漢張良、樊噲、曹參、霍光,唐狄仁杰、魏征、尉遲敬德,還有一些與民有功的當代地方官。這些賢臣良將后代多有加封,一直列于國家正祀之中,地方官員也多有維護。相對而言此類信仰在一定區域內出現,與人物本身有一定關系,傳播相對困難。
古圣先王信仰的長期留存也和山西一直處于京畿之地有關,離統治中心較近,民間信仰受官方意識影響較大,④[4]教化民眾的功能比較突出,通過對此類信仰的宣傳與維護,宣揚忠、孝、仁、義等儒家思想,規范民眾行為。儒家精神看似并未大肆在民間傳播立祠,但對于古圣先王的祖先崇拜和忠義倡導卻深深根植在民間信仰的血脈中。
二、民間信仰區域化
山西的地理位置優越,是游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文明的交界帶,地形復雜,山地居多,東有太行山為天然屏障,西、南以黃河為界,《左傳》講山西的地形是“表里山河”表有大河,里有高山,山河天險,賦予了山西深山藏古剎的優越條件。這種自然環境必然對地方的民間信仰產生諸多影響。除土地廟、城隍廟、文廟、關帝廟、龍王廟、八蠟廟、娘娘廟等全國普遍性存在的信仰外,山西境內還長期保留了大量區域性極強的民間信仰,其形成與發展與當地的環境、歷史、都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地方社會的發展和演變中起著重要作用。山西的高山河流劃分出了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地域,山西的晉北、晉中、晉南地區形成了不同的風俗與方言,反應在民間信仰上就是不同的區域信奉不同的主神,雖然隨著交通逐漸發展、商業往來愈發頻繁以及國家權力的推行,一些地域性的信仰會逐漸向外傳播,影響力日漸擴大,但其發源地依然是主要的信仰區域。如紀念介子推的介廟最早只在山西有,后來逐漸發展至全國,甚至于海外都有其蹤跡。
晉南地區普遍存在崔府君信仰,尤其是晉東南的澤潞地區。關于崔府君的身份說法頗多,廣為流傳的是兩宋時期“泥馬渡康王”⑤的故事[5],因其護佑國家的功績還屢次得到了官府賜額冊封。一直到明清時期,崔府君形象逐漸豐滿,其出身及親屬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故事流傳。明初以后,崔府君信仰的地位越發重要,開始與地方社會相結合,成為地方保護神,以國家正祀的身份存在。崔府君信仰的分布范圍以澤潞地區為中心,逐漸向周圍地區擴散,清代以來很多地區都開始出現崔府君的祠廟。加之澤潞地區商業活動的繁榮,走南闖北的澤潞商人把崔府君信仰帶到了山西各地,擴大了崔府君信仰的影響力。
晉中地區存在較多的區域性信仰應該是狐突信仰。狐突是春秋時期晉國大夫,其子狐偃、狐毛在晉文公門下,父子三人以忠義著稱,在晉文公執政之路上立下極大功勞,歷代統治者及民眾感其忠義,因而立祀。據傳狐突死后葬于馬鞍山,當地人稱狐突為狐爺、狐神,從忠義代表一步步變為水神,最后成為當地百姓無所不能的保護神,并逐漸以馬鞍山為中心形成了狐突信仰圈,相關的廟會、傳說、祭祀儀式也越來越豐富。
晉北地區佛教氛圍厚重,民間信仰相對單一,較為特殊的是一類武將信仰。晉北地區在中國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是邊疆地帶,甚至為外族所占,“其民鄙樸,少禮文,好射獵”⑥[1],到了明代推行衛所制度,移民屯兵、修城筑堡,使得晉北地區一直以來尚武之風較為濃厚,。歷代以來更是不乏驍勇善戰的守將與地方官,隨之而生的就是為紀念這些武將而產生的祠祀。如鄂國公信仰,祀的是唐代將軍尉遲敬德,分布在朔州、馬邑、保德等北部邊鎮,還有蘇武廟、趙武靈王廟、李將軍廟等等。此類信仰的產生與分布應該與晉北邊區位置和戰爭頻發有極大關系。
除大的區域范圍外,還有一系列與自然地理條件相關的區域所產生的民間信仰,比如汾河流域,石樓、靜樂、寧武、陽曲、太原、臨汾、曲沃等地的汾水神信仰,即臺駘信仰。還有長治地區的三嵕廟,因其山勢挺拔、祈雨靈驗,在當地香火不衰,被百姓信任崇拜。由此可見,受地理環境與區域限制,民間信仰的地域性鮮明,各地出現了類型不同、各式各樣的信仰。
三、神靈職能趨同化
縱然山西各地信仰各具特色,但身處同一大區域之中,各地的民間信仰又有非常多相似之處,尤其體現在信仰的職能上,有著逐漸趨同化的特點。由于山西干旱少雨的氣候條件,使得民眾的求雨需求長期存在,除常見的龍王廟外,許多有過求雨經歷的古帝王和原本以忠孝仁義立祀的人物都逐漸轉換為祈雨的雨神,再變為地方保護神。這種功能上的轉變與地理環境、時代發展都息息相關。
地理環境包括了許多因素,如氣候、地形、植被、土壤等等,在傳統農業社會中,氣候對民眾生產、生活影響最大。山西屬于典型的大陸性氣候。南北部的氣候與晝夜溫差差異較大,晉北相對寒冷,晉南相對炎熱。全省年降水量僅400~650毫米,降水受地形和季節的影響頗大,冬季干旱,夏季多雨;其中又山區較多,盆地較少,盆地是人群聚居的密集地帶,少且不穩定的降水量給人民進行農業生產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于是祈雨就變為當地百姓與地方官的一項重要活動。水資源也成了社會權力分配的一項重要指標,山西有關“分水”的民間傳說及史料記載也數量極多,祠廟也常作為“分水”的場所或見證者出現在碑記中。農業生產的需要和干旱少雨的現實導致山西各地遍布專司祈雨的龍神廟和各式各樣的司雨神,山西地區的龍神廟數量相當龐大,另一方面反映出山西的祈雨需求也是相當之多的。
竇大夫祠是紀念春秋時期晉國大夫竇犨的祠堂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區上蘭村,《山西通志》載“竇大夫祠在府城西北四十里烈士峪口祀趙簡子臣竇犨元至元三年建國朝洪武三年改稱晉大夫竇鳴犢之神有司歲以四月五日祭”。⑦[6]據說此地古稱狼孟,竇犨的封地在此,后來也成了百姓及地方官祈雨的場所。關于祠廟的存在,最早的記載出自唐代李頻的一首游烈石詩,但詩中只是講“竇犨遺像在林巒”,并不能顯示出其水神職能。《陽曲縣志》記載“廟臨汾流而靠諸泉,宋元豐八年六月,汾水漲溢,遂易今廟,有金縣令史純碑記。”⑧[7]說明了其所處位置與汾水臨近。金大定年間縣令史純的《英濟侯禱雨感應碑記》說,“汾水之濱,有祠曰英濟,俗呼為烈石神。考之圖籍,乃春秋時趙簡子臣竇犨,……英靈能興云雨,里人立祠祀焉,舊無碑記可考”。⑨[7]由上可以看出至少從北宋開始,竇犨的職能就已成為水神。趙世瑜⑩[8]對于竇大夫從賢臣到水神的功能轉換做了完整的論述,然而這種情況在山西乃至全國都并不罕見。山西地區的湯王廟、狐突廟、鄂國公廟、臺駘廟、竇大夫祠、三嵕廟等等祠廟,無論最初供奉的是君王、大夫、還是山神、水神,但都在歷史過程中開始承擔祈雨職能,凡呈現出求雨靈驗的“神通”,其余各種愿望和需求也會接踵而來,直至成為神通廣大的地方神,所在祠廟最后都成了祈雨的場所。“民間信仰成三教合一的特色,那么反應在神祇功能上,各路神就成了一專多能的多面手,各種神祇的神通就不再為他身前的職業所限,而成了能夠應付各個社會階層,各種類型的信仰者及各式各樣愿望和要求。(11)”[9]
四、與宗教文化的融合
佛道文化逐漸傳入山西后,就與本土的民間信仰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許多祠廟開始供奉多種或多教的神祇,這些廟宇的日常維護者也變成了僧人或道士,宗教文化對民間信仰進行了神靈和祭祀儀式的改造,以及對廟宇空間及資源的再分配,使得民間信仰呈現出新的格局和面貌。在宗教文化與民間信仰的融合過程中,也許開始是為了使當地百姓更容易接受新傳入的宗教文化,但后來隨著佛道二教的興盛反而是祠廟中宗教的存在使得民間信仰得以長期留存。
佛道二教文化的傳入,對山西的信仰空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達到空前繁榮,當時戰爭頻發,社會環境動蕩,政權頻繁交替,而山西在這一時期作為政府的政治重地和戰略要地,處于胡漢交界之地,既是政治經濟中心,也是文化交流中心,對于佛教在山西有了充足的發展條件。據載“魏都平城時期,為亞洲盛國,西域諸國,相繼來朝,從事朝貢貿易,僧徒亦樂東來弘法”。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僧人都曾在這一時期在山西進行活動,《山西通志》中記載過佛圖澄曾駐錫于中條白石寺。《晉書》中也記載了佛圖澄與后趙石勒的相識,在佛圖澄的影響下,石勒大興佛教并遍修寺塔,后趙當時的范圍就包括今天的山西地區。還有佛圖澄的徒弟釋道安“在并州聽大陽竺法濟、支曇《陰持入經》”“后于太行、恒山創立寺塔”,公元351年,釋道安隱居雁門封龍山,建寺傳教。云岡石窟的修建,五臺山道場的初步形成都發生在這一階段,由此可見這個時期山西的佛教已經十分興盛,也為后來三武一宗滅佛埋下了伏筆。但佛教在山西的發展卻未曾禁斷,北魏孝文帝,隋朝煬帝、清朝康雍乾三地都曾駕幸五臺山,歷朝帝后下詔、遣使朝拜、修廟建宇從未間斷。元代山西處于腹里之地,其境內山河廣布,適合隱居修行,歷來是方外圣地,全真道興起之初就將山西芮城人呂洞賓尊為五祖之一,甚至認為“全真之教蓋發源于此”,山西境內的呂祖祠、純陽宮等建筑頗多,在晉中、晉南、晉北均有全真教派建筑,且常處于市中心的文教區域,與府城相近,例如太原和大同的純陽宮都是這種情況,充分說明了全真教在山西的發展繁榮,官方的支持度也相當高,為全真教及整個道教向山西境內發展提供了信仰基礎。同時,道教利用統治者的力量,影響力迅速擴大,其教義又適應民眾祈福避災的信仰需求,信眾人數和道觀數量大為增加,在山西還開鑿了多處道教石窟,使山西成為北方道教的中心區域之一。
宋元時期山西宗教呈現南佛北道的格局,佛道二教與當地民間信仰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尤其是道教對民間神祇的吸納和融合相當普遍。以晉東南的二仙信仰為例,興起時間在唐末左右,二仙所供奉的是晉代樂氏二姐妹。相傳樂氏姐妹的生母早故,遭受繼母虐待仰天痛哭,其哭聲傳至天神,降下黃龍,兩姐妹乘龍升天,遂成仙女。二人在成仙后關心民間疾苦,有求必應,晉東南一帶極為崇信,遂建廟祀之。至宋元時期,二仙與道教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宋徽宗曾封二仙為真人,真宗時期二仙再度被推崇并賦予道教形象,二仙的身份在官府認證為道教女仙。二仙通過其道教身份,獲得正祀地位,道教又通過吸納二仙獲得更廣大的信眾。盡管道教對二仙信仰的改造始終不徹底,道士以及道教信徒還是通過重塑二仙形象、賜封道教名號、推行道教儀式等手段影響著二仙信仰。(12)[10]
也有許多民間信仰經歷千年,本來已經香火寥落,廟宇殘破,由于與宗教的融合才得以繼續留存。上文提到的竇大夫祠在晚明時已十分破敗,據明萬歷年間的《保寧寺養贍地畝碑記》說,一般寺廟都是“廢者莫舉,舉者易圮,若烈石古廟是已,然特高僧世鮮故至此”,由此可知此時的英濟侯廟破敗不堪。這時有個叫邢海靜的僧人募捐,“于烈石左建一寺,為古廟翼”。晉王府的宗人朱慎錭不僅給寺命名,而且用15兩8錢銀買了16畝地,“施為烈石廟保寧寺焚修之資”,意在以佛寺養竇大夫祠。(13)[8]在竇大夫祠原址的基礎上又修建了保寧寺,保寧寺住持也就是竇大夫祠的管理者。竇大夫祠因保寧寺的建立而得以留存興盛,也說明了佛教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間信仰的留存。
此種現象也并非個例,陽高縣羅文皂鎮許家園村的青云寺,當地又叫作胡老爺廟,廟內主殿供奉的是春秋時期晉國大夫狐突,據當地百姓所言,原來是一座純粹的道觀,現今已成為一座佛寺,寺內有住持及僧人,同時供奉有佛、道及狐突三類神靈。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在發展過程中共生共存,相互吸納融合,在當地鄉村社會中共同扮演了神圣的角色。
從現存的寺廟景觀的狀況來看,山西許多建筑都呈現出不同朝代的建筑和不同的信仰疊加在同一空間內的情況,通過對寺廟進行時空剖面分析,可以看出民間信仰與宗教文化融合的過程,也是不同信仰與地方社會互動角力的過程。
五、結語
三晉文化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多種多樣的信仰,信仰的發展又孕育了這塊黃土地上的人們對自然和祖先的敬畏之情、敬仰之意,以及對道德、良知的尊重和推崇。山西民間信仰的出現時間極早,留存時間極長,經歷朝代更迭以及民國以來近代化的沖擊,總體變化一直相對較小。民間信仰所體現出的強烈的地域特征是地方社會與民風民俗的代表,也是地理環境影響下百姓訴求的體現。《漢書·地理志》講到“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14)[1]所謂“水土之風氣”,正是自然地理環境帶來的具有區域性質的民風特點,而“隨君上之情欲”,《漢書·地理志》中將一地風俗的形成歸咎于古帝王德行與治民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探究山西大量古帝王祠祀留存與其地風俗的重要因素。我國民間信仰的顯著特點就是極具功利性,但凡所求靈應、能庇佑一方的神祇,民眾都會通過建廟立祠、修筑金身等方式進行回饋,而地方官員為更好地管理民政也會對地方神祇進行祭拜、組織修繕,國家也會對這些信仰人物進行封賜。除了社會方面外,信仰的地理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環節,山西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封閉在各個區域的信仰留存,獨特的歷史地位又產生了獨屬山西的民間信仰,其干旱少雨的氣候,又造成了神靈職能的轉換。在多個層級與地理環境的共同作用下,許多古老信仰得以留存至今,并形成區域性的特征差異,對于我們研究古代社會及山西區域文化提供了極好的資料。
注釋:
①李洪峰.歷史學讀書筆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05):287.
②班固.漢書·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卷二十八下,一六四八頁.
③李會智.山西元以前木構建筑分布及區域特征[J].自然與文化遺產研究,2021(01):1.
④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M].北京:三聯書店,2002:56.
⑤郜俊斌.宋以降崔府君信仰的塑造、傳播與本土化:以山西為中心[D].廣西師范大學,2012:8.
⑥班固.漢書·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卷二十八下,一六五六頁.
⑦康熙《山西通志》卷9,“祠祀”,第7頁上.
⑧道光《陽曲縣志》卷8.“禮書”,第29頁上.
⑨史純:《英濟侯禱雨感應碑記》,載道光《陽曲縣志》卷15,“文征上”,第41頁下-42頁上.
⑩趙世瑜.從賢人到水神:晉南與太原的區域演變與長程歷史[J].社會科學,2011(2):3.
(11)喬潤令.山西民俗與山西人[M].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198.
(12)易素梅.道教與民間宗教的角力與融合:宋元時期晉東南地區二仙信仰之研究[J].學術研究,2011(7):3.
(13)趙世瑜.從賢人到水神:晉南與太原的區域演變與長程歷史[J].社會科學,2011(2).
(14)班固.漢書·地理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卷二十八下,一六四〇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