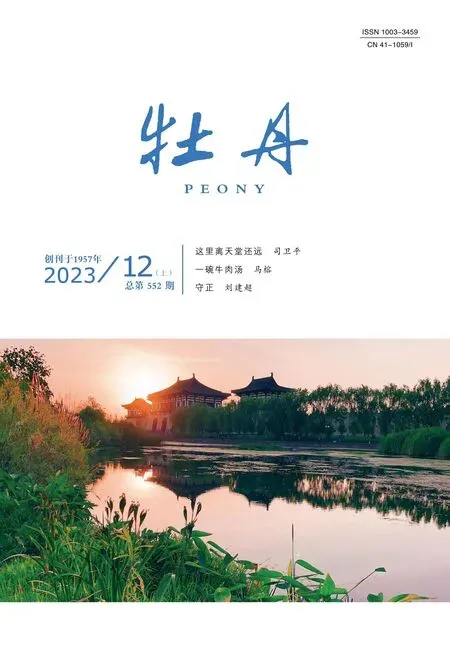蝶戀花
梁樹欣
一
她年輕時是鎮(zhèn)上出了名的漂亮姑娘,走到哪里都會被人夸贊長得俊俏,大眼睛,雙眼皮,鼻梁不高,但顯小巧,眉毛濃淡相宜,像是顏真卿最擅用的長橫。
每當過年走親戚,她扎起辮子,搭在兩肩,紅繩綁在辮尾,一手挎著籃子,一手夾緊新做好的紅棉襖,辮子隨著腳步,在肩膀上蹦蹦跳跳。一路上,聚在瓦屋門前的長輩會不時傳來一陣低語,說,這是老街東頭家的閨女,你看長得多喜歡人。每當聲音躍到耳畔,她會側著頭,小跑似的離開,紅撲撲的臉頰,不知是害羞的顏色還是街口風太寒的緣故。
上學時,奶奶會給她扎起馬尾。她最喜歡奶奶給她梳頭。爺爺眼睛不好,是個高度近視的老知識分子,讀書都要拿著放大鏡趴在紙頁上,手上的老繭也厚,梳頭常常拿捏不好輕重,而奶奶不僅手暖和,而且會邊梳頭邊夸她,夸她頭發(fā)又黑又多,扎起后捧在手上,粗粗的,沉沉的,飽飽的,最后,奶奶把從縣里帶回來的蝴蝶結卡在她頭上。她覺得自己是比露水還要新鮮的一朵鮮花。這是童年的她對幸福一詞諳熟于心的理解。
她背著奶奶縫的挎包去了鎮(zhèn)中心的學校。
她是班里人緣最好的,老師們絲毫不掩飾對這個寫字一筆一畫、上課坐姿端正的女孩的喜歡。但人緣好不代表身邊一定比別人熱鬧,男生們往往羞于在人前談論她,抬頭瞧她都要鼓些勇氣,當她出現(xiàn)的時候,那些本就熱鬧的男生會變得更熱鬧,但他們不會設法把這種喧鬧牽扯到她身上,只是不時有余光蜻蜓點水似的落在她身上,男生在看她是否因此抬頭。女生看到她頭上的新蝴蝶結,喜歡圍著她詢問來處,在黑綠藍盛行的年月里,只有她身上常常會點綴那么幾處斑斕,像是黃土世界里一抹新鮮的亮色。每周的升旗儀式,女生除了注目升起的國旗,余光總要落在她的蝴蝶結上,看看這次又換了什么顏色。當歌聲漸隱,國旗飄駐于桿頂,女生便心安理得地觀察起她的發(fā)卡,像是在端詳一只隨時會飛走的蝴蝶。他們與她一同成長,可她常是漂亮而又新鮮的,衣服并不嶄新,但洗得干凈,像山林里的蝴蝶,生于此長于此,看著大方且得體,美得獨特且祥和。
那時,人們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她以及他們的父輩都在為在土地上蓋起新房而耕作,人們剛剛知道去外地打工能掙大錢,但真正有這樣高瞻遠矚的人在一個鎮(zhèn)上都屈指可數(shù)。不知不覺間,人們對土地逐漸埋下了一絲倦悶,人們喜歡用罵誰“土”來表達自己除了農(nóng)耕外為數(shù)不多的攻擊性。但男生不會說她土,除了她從不與人置氣外的性格外,也和她家的住處有關,鎮(zhèn)西的老街是每逢露水集時最繁榮的地段,而她家就在那條老街東側。
在她上學的日子里,當然受過委屈,但校里校外從未與人置過氣,有一次,奶奶擦著她頭發(fā)上已經(jīng)干硬的泥漿,拍著她臟兮兮的衣裳,問,阿珍,你這都不會生氣嗎?她一邊用手背擦著眼淚,一邊哭著搖了搖頭。
第二天黎明,天邊的霞光初露頭角,她跨上昨日黃昏便已收拾好的書包,辮子一跳一跳的,一如往日,干干凈凈地去了學校。早上的霞光并不刺眼,但升起得很快,黑夜尚未散盡,像彼時的黃昏一樣欲拒還迎,她的大眼睛像是一面鏡子,迎接陽光的同時也會折射陽光,她總會把自己收到的溫暖倒映給旁人。不論這陽光似夏日那般盈余,還是如冬日那般稀少,她像大自然對待萬物一樣收放自得,容納黑夜的同時會給黃昏留有余地,看到嫩芽后依舊會對枯葉一視同仁,她把自己的眼淚當作人生中的風雨。她此后的人生中沒有經(jīng)歷什么大的風浪,但她贈給別人的彩虹早已不計其數(shù)。
她的氣質(zhì)與這個小鎮(zhèn)大體相像,但總不盡相同,不像祖輩那樣斤斤計較,也不似同齡人那般好大喜功,她的性格有著不言自明的顏色,不像土地一樣緊繃,也不似井水那般松軟,而是像雪花一樣綿延跌宕,與湛藍色的天空相得益彰。
高中畢業(yè)后,她沒考上大學,在鄉(xiāng)鎮(zhèn)小學當了老師,在教書的第三年,經(jīng)媒婆介紹,被一個穿著破衣服、推著破自行車后面還馱著個破柴鍋的年輕人娶回了村里。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相親,也是最后一次。男生大她四歲,中專畢業(yè),頭發(fā)有些自來卷,但由于長時間疏于打理,亂蓬蓬的像是個雞窩。兩個人一起去了鎮(zhèn)北的油菜田,去了縣南的城湖。幾個月后,他們搭了一輛長途客車去了洛陽城,從黎明顛簸到傍晚,當她踩著發(fā)軟的腳步下車時,看到了客車兩側濺滿的泥漿。在龍門石窟,她第一次見到了大山。
最后,他們回家去看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媒人。他們結婚時沒有彩禮,沒有嫁妝,也沒有大操大辦的酒席,男生買了新自行車把她馱回了五公里外的村莊。多年之后,村頭那個蒼老的媒人還常念叨這對順風順水的新人。結婚之后她依舊在鎮(zhèn)上教書,男人去了外地掙錢,天南海北地跑過麥種,晝夜不停地跑過大車,既在城市的霓虹里賣過水果,也在一無所知中誤入過傳銷,最后,從工程測繪員開始,一心一意地搞起了水利。
夏天的蟬一茬又一茬,冬天的雪一陣又一陣,立春前村口的寒風依舊刺骨,驚蟄后墻根的嫩芽準時破土。小滿已過,夏日又長,林葉悠悠,秋后落黃。
在她出嫁的第三年,奶奶死了,剛剛在她鋤地的時候,臉頰上似乎還含蘊著奶奶手掌的余溫。她放下手頭的活兒,草草盤起頭發(fā),在回娘家的路上已然淚如雨下,奶奶早已不能坐起給她梳妝,她月初回鎮(zhèn)上時,還將奶奶的手心貼到自己的臉頰上,說下次趕集再來看你。她雖然早有預感,可以往那虛妄的預兆卻墜破了如今真實的生活,那雙松松垮垮的手再也無法像小時候那樣攥緊,到了娘家,尚未娶親的弟弟站在屋外正擦著眼淚,她進了屋,看見奶奶的身體還躺在床上,本來靜悄悄流淌的淚水,眨眼間泣不成聲,淚眼蒙眬間,她看到,奶奶像蝴蝶一樣飛遠了。原來死亡就是永別的意思。喪事過后,她騎著婚時的自行車,回到了五公里外的村莊。
風吹麥田,麥子高低起伏,像正泛起波浪的大海,雖然她從未見過海。
二
自從她嫁到這兒,村里的人都夸這家老三娶了個俏媳婦,又漂亮又孝順,還是鎮(zhèn)上的。那年鄉(xiāng)鎮(zhèn)小學改革,學校把非師范的老師聚在一起,說交一萬塊錢就可以轉正,她放棄了,覺得自己學歷低,也不是科班出身,才不配位。
離開學校后,她便安心留在村莊里,陪著不識字的婆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婆婆總在人前人后夸她能干,說她除草耕田,養(yǎng)牛養(yǎng)雞,洗衣做飯,干得比誰家媳婦都好。
第四年的深冬,墻頭的老樹剛剛抖落枝頭第一捧雪花,她懷孕了。
妊娠前,男人從工地回來,她到縣醫(yī)院,生下了她一生中唯一的孩子,這個八斤重的嬰兒,衡量著她此前每一個朝暮重疊起來的重量,她的腳步從此不再指向自己的未來,而是踏在另一個生命前進的路上,她用此后那個寸步不離的身影來告別那個喜歡蝴蝶結、喜歡奶奶給她扎頭的少女。
孩子出生后,男人的工作逐漸穩(wěn)定,隨著公司的遷移,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落了戶,單位分了房,湊足了首付,稍作裝修便趕忙讓她搬來。第三年,她第一次坐上火車,帶著兩歲大的兒子搬到了百公里外的這個家屬院,住進了屬于自己的樓房。
家屬院往北一公里是市中心,往東三百米就是京廣鐵路線,火車聲在她的耳畔日夜不息。她開始以全職主婦的新身份來與這個城市互動,與自己的生命互動,與生命中的另一個小生命互動。很快,她能駕輕就熟地穿梭在菜市場和紅綠燈之間,賣魚的、賣肉的、賣雞蛋的、她把各家小販的價格了然于心,誰的質(zhì)量好,誰的價格貴,幾點的時候菜最新鮮,幾點的時候菜農(nóng)會把賣不盡的低價處理,她認識到,母親的身份比教師的職業(yè)更需要深入細致地學習,城市與鄉(xiāng)鎮(zhèn)比起來,在這兒的每一處生活都需要肉眼可見的開支,她開始記錄一天的每一筆支出,百元的稀有,千元的罕見,本子上大多是一塊四一把的生菜、三塊五一包的十三香、八毛錢的綠豆芽,超市小票里的幾分錢也不落下。除了兒子穿小的衣服和穿不上的鞋子,床頭的幾本日記就是她與生活朝夕相處的全部記錄。這個習慣她保持了八年,八年后,六層高的家屬院在拔地而起的建筑群的映襯下已經(jīng)不算是高樓,兒子變成了初中生,她從全職主婦變成了小面館的老板娘。
六個月后,兒子到了上學的年齡,去了距家兩個路口遠的幼兒園,她開始擁有少許可供自己支配的時間,她買了輛自行車,到路南的烹飪學校學習做飯,從素菜開始,再到蒸煮燜燉,她都記在了筆記本上,不過,廚師教煎炸的時候她刻意回避了去,不是與接送兒子的時間相沖突,是她覺得油炸的東西不好。
華北平原上的四季,各地相去不多,只是那些在異鄉(xiāng)和家鄉(xiāng)兩個概念的中折返的人,情緒不免此消彼長。夏季的悶熱和冬天的刺骨逐漸被襯托得有所不同,相比于農(nóng)村的淡煙流水,在城市里尋陰納涼都成問題,相比于城市的見多識廣,農(nóng)村的不成體系也難值一提。她喜歡玫紅和橘黃,先后買過一條紅色的長裙和一件黃色的棉襖,她開始戴起發(fā)箍,她最喜歡那個兩指寬窄、淡粉底色的布制發(fā)箍,上面有一圈透明小鉆,小鉆在太陽下躍起的陣陣光點,是她三十歲的見證。
晝短夜長,晝長夜短,從柳樹綴出新芽,再到銀杏面掩鵝黃,日落而息的生活已從她生活中淡去,她逐漸習慣了這座城市的日夜,不遠處傳來的火車聲也不似最初那般刁鉆刺耳。她送兒子上幼兒園時的動作不再那么緊張和僵硬,兒子松開她手掌的瞬間也逐漸變得穩(wěn)健且果斷。
日子像火車一樣過了去。兒子上了小學,學校在離家三個路口處,她與這座城市的節(jié)奏逐漸變得如榫卯一樣契合,廚藝也小有所成。她讓兒子中午放學時和同學一路回家,要求兒子不能吃垃圾食品,但兒子時常會在到家之前把辣條或者冰糕吃完,有時一進門她便會聞到一股辣條味。她想了一個辦法,聞不到味時就抓起兒子的小手嗅一嗅,兒子常會心虛,慘叫著把手縮回去,跑到衛(wèi)生間洗手,接著耀武揚威似地把手重新伸回她面前。
周末她會帶著兒子去半截河玩,初春時最為頻繁,一早便騎著自行車,車簍里放著昨夜準備好的風箏和吊床,坐在后座的兒子唱起音樂課里學的歌,但他規(guī)矩地唱一會兒便覺得無聊,轉而背起男生間口口相傳的順口溜。
到了半截河,自行車扎在一旁,她尋兩棵間距合適的樹把吊床系上,小男孩玩累了,在包里找出口琴,笨拙地吹起《兩只老虎》。斷斷續(xù)續(xù)的樂聲并不讓她煩躁,她和兒子一同俯下身子,觀察枯枝上透出的綠芽,半截河沿岸全是柳樹,遠看時,隱約間蒙著一層綠色,但到了近處,卻發(fā)覺柳枝與入冬時模樣并無二樣。這似有似無的綠似乎是氤氳在樹皮之下,像是即將長大的小孩,鉚著一股勁兒在生機肆意的春天里博得自己的領先。一周一周的,漸漸地,兒子脫掉一層層的衣服,也看到了正綻放生機的萬物,感受到春天來臨時那靜悄悄的步伐。夏天時,兒子在林中的小路上奔跑,對著那座有著南水北調(diào)標識的高橋吶喊,刺耳的蟬鳴給他和著節(jié)拍,兒子在河邊打水漂,像她小時候一樣。有一天,兒子把頭枕在這座橋的欄桿上,兩岸的柳樹倒映著微風的模樣,他挺直了腰,說,媽媽的頭發(fā)像春天的柳樹。
又過了幾年,兒子到了小學高年級。有一天,她發(fā)現(xiàn)兒子在偷拿衣柜里的錢,想到自己先前不時會在家里找到一些玩具,她開始注意兒子背著她在學校門口買玩具接著偷渡到家的行為。那一天,早晨細雨朦朧,清早如傍晚一般昏沉,雨落得又急又密,像行人匆匆的腳步。兒子穿著五色雨衣,和她在入校的拐角處揮手告別,這條路名叫育才路,小朋友們會沿著這條路徑直入校,她往往和其他家長一樣在此止步,而這次她想看到兒子走進校門的那一刻。她猜的沒錯,兒子不時回頭,拐個身子進了路對面的小賣鋪,她匆匆合上雨傘,三步并作兩步,在兒子從雨衣兜里拿出被水微微打濕的一張五十元時,擰住兒子的耳朵,她搶過紙幣,攥在手里,兒子嚇傻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她說,你站著干啥,現(xiàn)在給我上學去,回家再跟你算賬。兒子走出小賣部,再一次匯入戴著紅領巾的孩群中,兒子走得緩慢,背影像是要奔赴刑場。她注視著兒子越過保安身前,踏入校園,而后雨已將她的劉海盡數(shù)打濕,她撐開傘時,發(fā)覺紙鈔已被她攥成再難展開的一團。
她的白頭發(fā)似乎是從那一年開始長的。
后來,她又發(fā)現(xiàn)兒子偷拿她錢包——一個泛著黃斑和黑漬、皺巴巴的塑料袋子——里的錢,那晚,她把兒子在床底、被褥下藏的玩具悉數(shù)擺在客廳,各式各樣的模型,有逼真的袖珍摩托,有蘭博基尼和布加迪,問兒子買這些東西的錢是哪來的,兒子眼神躲閃,沉默不答,每當她音調(diào)升高,兒子胸膛總會一抖。她當著兒子的面,舉著實木板凳,把一地玩具砸得四散而飛,兒子終是不忍心看著玩具一夜盡毀,說,媽,我再也不偷偷拿錢了,我錯了,你別砸了。她看著兒子,把板凳扔到一邊,在墻角處碰出噔嗵一聲,跟瘋了似的,把所有本該向兒子發(fā)的火一股腦地撒在自己身上,她好傷心,說,都怪我,沒教好你,把你教成了個小偷、教成了個賊。說著一個巴掌扇到自己臉上,接著又是一巴掌,她打著哭著,兒子崩潰了,大哭著撲過去,撐住她扇向自己的手掌,大喊,媽媽你打我吧,你別打自己,你別打自己。兒子雙手握住她的手腕,想讓耳光落在自己臉上,可根本拗不過母親懲罰自己的力氣。兒子哭著跪下求她,她停下,將臉別過一旁,情緒上的抽噎依舊繼續(xù),胸口起起伏伏滿有皺紋的眼眶已是通紅,大眼睛里血絲連片,像是紅色的蜘蛛網(wǎng),兒子哭得喘不過氣。她紅色絨襖在腋窩處露出棉花絲,是她第一次去洛陽時買的,如今也染上了為人母的憔悴。
自那次起,她開始爽朗地給兒子零花錢,兒子對于錢的舉止也逐漸落落大方。
三
兒子六年級時,剛剛在外地干完南水北調(diào)支線工程的男人回了家,本處事業(yè)上升期的他剛得幾日清閑,工程驗收時卻出了問題,坍塌事故造成民工傷亡,上到分公司老總下到男人這種職員,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懲罰,幾個主事的領導有的貪污受賄被抓進了監(jiān)獄,有的因挪用公款而傾家蕩產(chǎn),有的因知情不報而受到牽連。男人算是幸運,也算不幸,被吊銷了到手沒幾年的建造師證書,原本事業(yè)蒸蒸日上的他一下成了無業(yè)游民。
等到兒子小學畢業(yè),男人和她商量,托關系把男孩送到市區(qū)邊緣的一個寄宿制初中,一周回家一次,男人把這些年掙到的錢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用來買了一輛五菱面包車,一部分拿來租了個四十平方米的店鋪,加盟了家熱干面館,算是開了個夫妻店。她的身份也從全職太太轉換到了個體經(jīng)營戶,自她成了老板娘起,她頭上只留下了兩樣裝飾,一是黑色皮筋,二是白頭發(fā)。
前兩年,生意不可謂不紅火,中午和晚上兩個飯點,小店里擠滿了顧客,她在外面記賬收拾碗筷,男人在里屋煮面配底料,兩人前腳趕后腳,忙得不可開交,常常是夜里十一點還有生意,待到收拾好一天的碗筷,凌晨時能回家已是少有。每夜她都會把當天一口袋零錢癱在客廳,數(shù)出一日的營業(yè)總額,再減去早晨的本錢,一天的收入便出來了。
那段日子,晚上男人總說起他的獨到的眼光和明智的決定,飯店的生意來錢真快,沒等男人說完,她便已沉沉睡去,男人也累,連夜里打呼嚕的余力都沒了。
小飯店能掙快錢,可快錢不意味著可以穩(wěn)定增收,錢來得快去得也快。小飯店所依托的有兩類客源,一是對面中學的學生潮,二是附近百貨批發(fā)市場的路人潮,然而中學在那一年改為食堂集體就餐。與此同時,電商出現(xiàn),網(wǎng)購興起,批發(fā)市場的客流再不似先前那般人滿為患。
小面館第二年生意便不如第一年,當男人看到面館盈利的上限時,他對體面的在意逐漸從金錢的短暫奪目中閃出身來,一過飯點便回了家去,再不復最初的熱情。晚上收攤時免不了抱怨這日薄西山的生意,身邊的朋友聽聞科班出身的男人正在以賣面條為生,話里話外都是說他屈才。男人的焦慮占據(jù)了飯點忙碌之外的所有細節(jié)。逐漸,小面館里收錢和煮面都成了她一個人的事。
半年后,男人經(jīng)朋友介紹跳槽到一家國企,進入事業(yè)的第二春,相比于男人上一份工作的坎坷,這次春天來得更舒展些。
這時,她七十歲的母親去世了,聽聞噩耗,她和住校的兒子打過招呼便趕回了家。
母親患上腦出血已有七年,第一次腦出血之后便不能說話了,像一塊喑啞的玻璃,后來情況惡化,頭上數(shù)次開刀,左腦一側有著明顯的凹陷,看起來像是大雨過后被碾過的泥坑,摸起來像是一個蒜臼。隨著病情的反復,玻璃上的裂紋已如蜘蛛網(wǎng)一樣密集,母親的死亡似乎是板上釘釘?shù)氖拢缃瘢赣H呼出的最后一口氣隨著鏡子碎裂的齏粉一同向遠空蕩去。她看著火化后的母親被裝在棺材里,用釘子釘固四周,埋入土里,成了華北平原上千萬的千萬墳頭之一。墳西種了棵松樹,墳東種了棵柏樹,那棵萬年松是她親手所種,那棵柏樹是她弟弟栽上又培的土,曾經(jīng)母親膝下的一子一女,如今的鬢角都已猝不及防地添上了白發(fā)。
她在家住了十天,直到喪事忙完,收拾好情緒,黎明一如既往地鋪在眼前。
到了城市,她正式開始一個人經(jīng)營小面館。早上起來騎著自行車去面條鋪買熱干面,后面馱著硬紙箱,去菜市場買蔥蒜,到店里,先虛掩卷簾門,把紙箱子卸下,在門口擺出禁止泊車的路障,再拖地擦桌子,配足能應付晌午客流的料碗,最后將卷簾門徹底抬起,打開門,迎接第一位客人。當她起身目送最后一位客人離開,收攤時,常常已是凌晨。因為店里只有她一個人,客人再少也顯得手忙腳亂。
熱干面館來到了第三個年頭,智能手機普及,掃碼支付開始流行,彼時她還用著按鍵手機,思來想去終究沒有下定買新手機的決心,只是將男人的收款碼放在店里。她對這種新事物的興起并不信任,可她口袋里能數(shù)出的收入越來越少,不知從哪一天起,她晚上不再細數(shù)當天的收入。
兒子擦著分數(shù)線考到市里的重點高中,這是她開面館的第四年。
這時,電商開始崛起,人們嘗到了網(wǎng)購的甜頭,周邊飯店賴以生存的百貨市場主顧們一個個另尋出路,市場里關門的店鋪越來越多,自己的商鋪尚且難以為繼,租房做生意的小商小販更是如坐針氈,她看著恒定且冷寂的房租,總覺得自己的身體似乎大不如前了。
小飯館的命運就是,越紅火時越紅火,越冷清時越冷清,剛開店時一早便會擺出去的折疊木桌,已蕩上無心擦拭的灰塵,酒架最高層的那幾瓶牛欄山依舊是那幾瓶,空調(diào)的溫度也沒有先前那么精準,夏天不夠涼,冬天不夠暖,當?shù)昀餂]人時,她一人也不愿再開上空調(diào),當人來時打開,空調(diào)的風尚未吹滿屋子,客人便吃罷離開。
她是最不會做生意的生意人,當她為門可羅雀的飯店而憂心忡忡時,疫情來了。
她在家里陪著即將高考的兒子,近半年足不出戶,小飯館的生意徹底停滯,每個月的房租卻是一分不少。半年后,兒子成年,考上了大學。她把飯店重新開張,然而人們習慣外賣與網(wǎng)購,稀少的客源讓她度日如年。
最后,在男人的催促下,她把面館里的電器和餐柜一并變賣,當鑰匙交回到房東手上時,房東說,你要是繼續(xù)租的話,咱們房租可以降一降,她心里突然顫了顫,似乎有一肚子話想要急促地傾訴出來,可她不知從何說起,就像一根粗大的毛線找不到那處微小的針鼻,她匆匆換了話題,窘迫地與房東告別。
那晚,她從面館里最后一次走出來,把卷簾門放下,沒有上鎖,扶好白天被風吹倒的自行車,踢起腳蹬,拿繩子把買菜的紙箱子拴在車座后,箱子里放的是她收拾出的最后一批雜物。
她朝著相鄰的幾家店鋪頓了幾下,一同做生意的街坊如今已經(jīng)換了幾茬,還留在那里的只有一家夫妻打印店和一家開了二十多年的饸饹面店。她最初的鄰居是一家大臉雞排,開店的是個胖乎乎的女孩,沒生意的時候總會跑來笑嘻嘻地喊她姐,長得又可愛嘴巴又甜,她只能那么喜歡這個雞排女孩了。
雞排女孩和她相處久了,逐漸感受到了這個中年婦女的一塵不染,女孩嘴邊最常掛著的話就是,姐,你咋那么好啊,我沒見過比你還好的人。女孩常常跟她吐槽家里人又怎么數(shù)落她,一會兒說她沒出息,一會兒說她嫁不出去。這幾年,她幫雞排女孩介紹過兩個對象,不過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前年的一個中午,雞排女孩給她掂了兩份雞排,說門面轉讓了,不干了以后,準備回家考縣里的公務員,找個穩(wěn)定些的工作。
她回過神來,眼睛有些干澀,打了個哈欠后,方才察覺風中已稍稍摻了些涼意,她告訴自己,以后再不開飯店,累死個人,就算有的那點好也都過去了。
想了一會,她似有似無地把剛剛的自己否定,心想,好什么好。
那晚的路燈把她映得忽明忽暗,影子起起伏伏,她推著車,高高扎起的馬尾辮在后背一起一伏,馬尾蓬起時,能看到后背上被汗沁透出了不規(guī)則的一塊,在燈光下變了顏色。在腳步的一路探照下,她打開家屬院早已緊閉的鐵門,吱嘎一聲,在深夜像火車一樣悠遠,像是有一滴水落在了她的眼睛里,眼神輕輕漾出幾尾波紋,如月光一樣空明。
到家后,打開燈,她意識到,小面館和她老板娘的角色一樣,再也不會亮起,她要告別這段人生,她在社會上唯一的身份湮滅在這一片黑色里。
干生意的那些年,她對經(jīng)過耳邊的火車早已不再有情緒上的起伏,火車早已像紅綠燈一樣平等地存在于她的生命中。兒子上大學,逐漸明白事理,時隔三年才給父親道了歉。父子和好,是她拋開小面館之外所獲得的唯一圓滿。兒子在外地上大學,常常是幾個月不回家,隨著成年,他的骨架已經(jīng)長開,后背和肩膀逐漸寬大了起來。男人四十而立,事業(yè)比之先前已經(jīng)是有所為,單位從省會遷到天子腳下,她屬兔的,想來也到了不惑之年,可這不惑之年卻給她帶來無止境的困惑。
飯店不干后,她賦閑在家,再次感到火車經(jīng)過時床板和沙發(fā)的微微震顫,每每如此,她常會感到自己心里的不安,像鐵軌一樣,雖然堅固,但卻顫顫巍巍。她不知如何向自己解釋這一無是處的生活,這憂心實在是無稽之談,只是隱隱覺得,她的不安似乎來得有理有據(jù),像在腸道里不時滲出苦水,讓她心神不寧。
她守著空家,其間找過零零星星的散工,工作并不繁重,但她一日下來總是身心俱疲。
這樣的日子捱過了一年,她的頭發(fā)愈來愈白,頭發(fā)掉得越來越多,稀疏的劉海根部已經(jīng)露出明顯的灘涂,魚尾紋和黑眼圈愈發(fā)沉重,沉重得每晚都把她拉入夢中,拉著兒子的小手,站在小面館門前,向絡繹不絕的客人一遍遍地解釋今天飯店關門,歇業(yè)一天。
她早已告別年輕,或者說,現(xiàn)在就是她最年輕的時候。如今她依舊是美的,是不出彩的漂亮,是不顯眼的整齊,是一種疏松的美,如她這半生一樣,既沒有燈光舞臺所渲染的華麗身姿,也沒有濃妝艷抹所鋪陳的精致五官,大眼睛里雖然有了些雜質(zhì)但并不渾濁。她能看到自己,是孫女,是女兒,是妻子,也是母親,是一個經(jīng)過半生的自己。
四
入秋時男人回了家,趁著中秋節(jié),開車帶她和兒子回到鎮(zhèn)上的娘家,昨夜到,明天走。
黃昏時她去到母親的墳前,買了三刀黃草紙,拿百元鈔在紙上比著壓了壓,拿指甲在黃紙表層理了理,引燃后,往火焰上三張三張地添,她不停地說,媽,我回來了,媽,我回來了,媽,你妮兒回來看你了。
焰心一時旺一時垂,火苗一時高一時低,火舌像在吞吐著什么,不時傳來枯葉燃燒的噼啪聲。有的灰燼留在地上,有的灰燼漫在空中,像是一個女人飄蕩著的凌亂白發(fā),單從頭發(fā)看,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一樣憔悴。
姐弟倆在墳頭兩側各自種下的松樹和柏樹在夕陽的掩映下微微搖動,一同搖動的還有她現(xiàn)已稀疏的劉海,噴過啫喱水的劉海一綹一綹地曲在前額,看著畏手畏腳,像是在害怕著什么。
弟弟種的那棵柏樹已經(jīng)長得能供一人納涼,而這萬年松早已不是她最初種下的那棵,這些年里,萬年松種上又枯死,枯死再種上,就是種不活,這棵萬年松弟弟剛剛幫她種上一年,尚未見枯萎的跡象。
兩棵同時種上的樹如今卻大相徑庭,種不活的松樹像是母親對自己的懲罰,她望向四周的百畝良田。一馬平川的田埂一眼可以看到天際,赤紅的晚霞將視野盡頭的座座墳包染成鐵銹的顏色。看著別家老人墳前寬大的樹蔭,一派生機勃勃,像是秋收萬顆籽的景觀,她不由得悲從中來。想到媽媽生前吃了一輩子苦,死了也沒有享福的命,她大哭道,媽,你不讓這樹活是不是怨我嘞,說都這么長時間了,這阿珍咋還不來?咋還不來哎?咋還不來哎?媽,你別生氣了,我來看你了,你讓它活吧……此時她像是一個請求母親原諒的女孩,腳尖朝內(nèi),雙手垂前,因為犯了錯誤而委屈地抹著眼淚,眼眶通紅,眼球里的血絲像是在晚霞里浸了浸,眼袋像是裝上了露水的重量,顯得沉甸甸的。在她哭泣的時候,風把面前的松樹吹得搖了搖頭。
紙錢燒盡了,遠處的殘陽吐出最后一抹余霞,穿過樹枝,越過田埂,在她頭上織成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最后,余暉散盡,墳前的最后一粒火星在黯淡的空間中隱去。
天空步入了夜晚,平原上處處困閑,人們一邊相聚一邊永別,目送著一道道血脈承轉塵間,在與某種存在分離的同時,迎來某種心灰意冷的希冀。
晚上她睡在母親曾長久臥病的床上,枕頭里塞的是碎麥秸,一翻身就會有淺淺的聲響。在夢里,她夢見頭痛的母親在深夜里磨牙,看到自己小時候睡覺的模樣,身體里生長的骨骼正在悄悄作響,夜里總覺得發(fā)寒,似乎有露水下在她身上。剛入秋,夜變長了,但也沒有愿想中的那樣長。等天朧亮時,她終于把被窩暖熱了。
太陽起得很早,一點一點地驅(qū)散露珠余下的寒氣,母親說她不疼了,她的骨骼也停止了生長,街上傳來稀疏的鳴笛和輪胎的摩擦聲。她起身做飯,一米六二的身高,和大腿高的壓水井有著血脈相連的默契,幾間蒼老平房上跳躍著清晨的陽光,紅底黑墨的福字將門框襯得更低了些。她側著身子,提著晃蕩但不溢出的水桶進了廚房,陽光還沒投進屋里,暗涌的朦朧色正緩緩將她的背影隱去。
晌午要離開時,她匆匆忙忙地檢查行李,檢查有什么東西忘了帶,有什么話忘了說。男人邊與岳父寒暄邊打開車門,突然從副座飛出一只橘黃色的蝴蝶,拍打著羽翼,應是昨夜不小心飛進來的,在車里懵懵懂懂地徘徊了一夜。這蝴蝶飛過熙攘的一家人,忽快忽慢,像是心中七上八下,最后似要停駐在她的頭上。男人見狀,伸手趕了去。兒子注視著這只略顯突兀的蝴蝶,似乎在哪里見過,卻又從未見過。她看著蝴蝶一點點飛遠,看著它跌跌撞撞地飛來,又舉棋不定地飛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