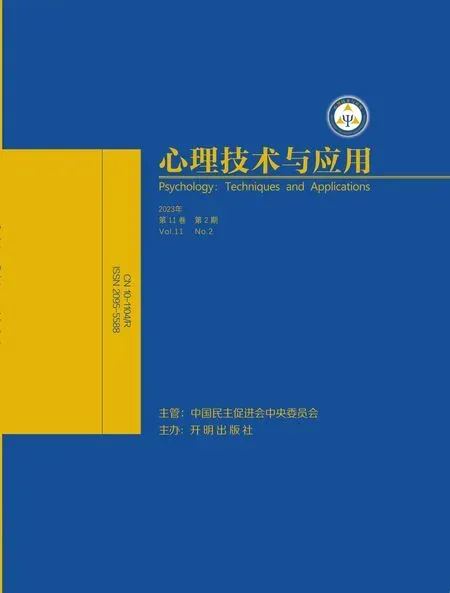仁慈領導對員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
蔣 鎖 竇 凱
(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系,廣州 510006)
1 引言
仁慈領導是儒家思想與現代管理理念相融而生的一種領導方式,其核心是給予下屬生活上的教導關懷和工作上的支持照顧(樊景立, 鄭伯塤, 2000)。仁慈領導不僅能減少職場中的人際偏差行為(Erkutlu, 2018),還有助于改善組織中的道德氛圍(Gumusluoglu et al., 2020),抑制員工的不道德行為(Jiang & Lin, 2020)。然而,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仁慈領導對員工出于自利動機產生的不道德行為的影響,卻忽略了仁慈領導是否影響員工為組織受益而產生的不道德行為,即親組織不道德行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UPB),如為了組織利益而欺騙顧客、偽造財務報表等(Umphress & Bingham, 2011)。此類行為不僅損害顧客利益,從長遠看也有損公司聲譽,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仁慈領導如何影響員工以及在該影響下員工何時產生親組織不道德行為。
仁慈領導以信任和關懷的方式對待員工,會形成高質量的交換關系,從而使得員工產生積極的認知、態度和行為(Chan & Mak, 2012)。然而為了保持互惠,下屬可能做出超越特定規范的行為,如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具體而言,當道德標準與組織利益發生沖突時,下屬會更關注行為的親組織性而非道德性,進而產生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仁慈領導對出于自利動機及親組織動機的不道德行為產生不同影響,可能的解釋是存在不同的心理機制。
因此,本研究基于社會交換理論,從員工工作態度出發理解仁慈領導如何提升員工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具體而言,根據社會交換理論觀點,互惠是社會交換的核心原則(Nohe & Hertel, 2017),這種互惠關系通常由領導發起,當員工感知到支持時會產生情感反應進而產生回報行為。領導的仁慈會讓員工產生積極的工作滿意度(Hiller et al., 2019),員工出于回饋、感激動機,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回報仁慈領導的關懷。但員工在這一社會交換過程也會受到員工對工作家庭支持需求的影響。例如,Wang等(2013)研究發現,相較于低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高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更能夠感知到家庭支持型領導的情感支持,工作家庭矛盾可得以妥善解決,因此對工作更加滿意。據此,本研究基于社會交換理論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從工作滿意度的角度探究仁慈領導影響員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中介機制以及工作家庭沖突的調節機制。
2 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2.1 仁慈領導與親組織不道德行為
親組織不道德行為是指員工為維護組織整體或部分成員利益而不惜違反社會核心價值、法律法規或道德標準的行為(Umphress & Bingham, 2011)。員工從事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出發點雖是維護組織利益,但其本質上是不道德的,從長遠看會給組織發展帶來潛在風險。以往研究發現,領導風格是影響員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Mishra et al., 2021)。
仁慈領導關懷員工及其家屬,維護員工面子,從交換的視角看,這會促使下屬將關系定義為積極的社會交換關系(Lin et al., 2018)。Bryant和Merritt(2021)發現與領導建立積極社會交換關系的員工會努力報答領導的恩惠以減輕人情壓力,甚至不惜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展現對領導和組織的忠誠。此外,仁慈領導對下屬工作中的失誤寬容以待,避免公開責備下屬等,為員工營造出了安全的心理氛圍(Li et al., 2021),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化解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顧慮。Lu等(2021)也證實領導的寬恕會使得員工產生感恩之情,進而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回報領導與組織。據此,仁慈領導可能會導致員工從事更多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H1)。
2.2 工作滿意度的中介作用
工作滿意度是“員工對其工作或工作經歷評估的一種積極的情緒狀態”(Weiss et al., 1967)。仁慈領導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密切相關。仁慈領導如慈父般關懷員工的工作與個人福祉,允許犯錯,不僅會塑造員工的積極工作態度(Erkutlu & Chafra, 2016),而且會建立持續的交換關系。根據社會交換理論,互動雙方遵循互惠規范,接受者以相似的態度回報對方(Blau, 1964)。因此,當仁慈領導努力改善員工福祉,創造積極的工作環境時,員工會感知到領導的關懷與支持。此時,員工不僅愿意為組織奉獻,而且對自身工作感到更滿意。而且,感知到領導的善意關心,員工會產生服從、信任和忠誠的感覺,這有益于提升工作滿意度(Islam et al., 2022)。現有研究已證實仁慈領導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之間存在正相關(Bedi, 2019; Shi et al., 2020)。
當感到工作滿意時,員工可能以“愚忠”的方式回報組織(Dou et al., 2019; Zhang, 2020)。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的互惠原則(Blau, 1964),高工作滿意度的員工會從組織中獲得更多資源,更有意愿回報組織以維持與組織的積極聯系(Lu et al., 2019)。因此,對工作感到滿意的員工在決策時可能更關注行為帶給組織的利益,將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作為與組織建立積極社會交換關系的一種方式,而忽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道德屬性(Zhang, 2020)。換言之,高工作滿意度的員工可能會為組織利益最大化而犧牲道德標準和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實施親組織不道德行為。
社會交換理論研究表明,工作滿意度在各種前因變量和工作場所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Crede et al., 2007)。然而,仁慈領導是否會通過工作滿意度誘發員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尚缺乏實證探討。本研究認為仁慈領導對員工個別照顧,維護員工面子,員工可能體驗到高水平的工作滿意度。作為回應,對工作滿意的員工有強烈回饋組織的動機(Hiller et al., 2019),導致其采取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以展示對領導和組織的忠心。據此推測:工作滿意度在仁慈領導與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間發揮中介作用(H2)。
2.3 工作家庭沖突的調節作用
工作家庭沖突是指工作和家庭兩個領域的角色壓力不相容造成的角色內沖突,包括工作干涉家庭和家庭干涉工作兩個維度(Greenhaus & Beutell, 1985)。不同程度工作家庭沖突下的員工對領導提供的工作家庭支持的需求與感知不同(Hammer et al., 2011),因此,我們認為仁慈領導的有效性會受到工作與家庭沖突水平的調控。
社會交換理論認為,在交換過程中個體會進行成本與收益分析,以確保所獲得的社會效益與所回報的價值具有可比性(Wang et al., 2013)。首先,與低工作干涉家庭的員工相比,高工作干涉家庭的員工難以解決工作中的困難,更傾向于尋求領導支持(Yang et al., 2019)。當仁慈領導者在工作上允許員工犯錯,并給予適當的教育與輔導時,高工作干涉家庭的員工認為領導的關懷支持更具有價值,更受益,這將加強仁慈領導的積極效應。此外,對于家庭干涉工作較高的員工而言,仁慈領導在生活層面照顧員工及其家人,關懷員工私人生活起居,可使得員工更易調整工作結構以解決家庭問題(Wu et al., 2020)。因此,與低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相比,高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在仁慈領導下,更可能獲得所需資源,這將加強仁慈領導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的積極影響(H3)。我們推測:相較于低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高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更受益于仁慈領導,從而對工作更滿意,會實施更多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H4)。
綜上,本研究擬構建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如圖1),探究工作滿意度在仁慈領導與員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間的中介效應以及工作家庭沖突的調節效應。

圖1 假設模型
3 方法
3.1 被試與施測過程
采用方便取樣法,以華南三個不同省份22家公司的員工為研究對象,調查主試由經過培訓的公司人事專員擔任。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采用多時間點方式采集數據,415名員工在時間點1填寫仁慈領導問卷和人口學信息,完成后放入帶有身份信息標識的信封(方便匹配);間隔2周后, 員工填寫工作家庭沖突、工作滿意度和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問卷。剔除36名因出差未能填寫或未答題超過30%的員工數據,共獲得379份有效數據(回收率91.33%)。其中, 男性占47.76%, 已婚占比45.12%, 平均年齡為36.05歲(SD=9.58), 在公司的平均年限為13.73年(SD=9.23)。
3.2 研究工具
仁慈領導。選自家長式領導量表(樊景立, 鄭伯塤, 2000)。該量表包括四個項目,5點計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樣題如“領導關懷我私人的生活與起居”。仁慈領導具有人治色彩,按照差序格局區別對待員工,將這種因人而異的領導風格作為個體變量更具有理論對應性(沈伊默等, 2017),因此,我們將仁慈領導作為個體變量來處理。該量表α系數為0.86,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單因子模型對數據擬合良好(χ2/df=1.41, CFI=1, SRMR=0.01, RMSEA=0.03)。
工作家庭沖突。采用Gutek等(1991)開發的工作家庭沖突量表。該量表包含工作干涉家庭和家庭干涉工作兩個維度,共八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樣題如“我自己的事占據了原本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本研究中該量表α系數為0.85,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兩因子模型對數據擬合良好(χ2/df=3.49, CFI=0.97, SRMR=0.04, RMSEA=0.08)。
工作滿意度。采用Weiss等(1967)編制的明尼蘇達滿意度問卷。該量表包含內在和外在工作滿意度兩個維度,共二十個項目,5點計分(從“非常不滿意”到“非常同意”),樣題如“職位晉升的機會”。本研究中該量表α系數為0.95,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兩因子模型對數據擬合良好(χ2/df=3.68, CFI=0.92, SRMR=0.05, RMSEA=0.08)。
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采用Umphress等(2010)開發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問卷。該量表包括七個項目,5點計分(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樣題如“為了幫助公司,我愿意做任何事”。本研究中該量表α系數為0.89,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單因子模型對數據擬合良好(χ2/df=3.47, CFI=0.99, SRMR=0.03, RMSEA=0.08)。
根據陳默和梁建(2017)的研究,本研究選取員工的性別、年齡、工作年限和婚姻狀況等人口學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其中性別采用二分類變量(女性為0,男性為1),其余變量為多類別變量。
3.3 統計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6.0進行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并采用Mplus8.3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和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在Mplus中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設置重復抽取5000次,若其95%置信區間不含零,則表示有統計顯著性。采用層次回歸進行調節效應檢驗,為便于理解,先對仁慈領導和工作家庭沖突進行中心化并計算乘積項,并進行簡單斜率分析。采用中介效應差異分析法進行Bootstrap(設置5000次迭代)前半路徑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若其95%置信區間不含零,則表示有統計顯著性。
4 結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和區分效度
采用“Harman 單因子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顯示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為33.69%,未到解釋量的一半,表明沒有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為檢驗區分效度,進行了驗證性因素分析。單因素模型沒有達到統計要求,四因素模型擬合較佳(χ2/df=5.60, CFI=0.92, RMSEA=0.06, SRMR=0.07),且顯著優于其他備擇模型,說明各變量之間具有良好的區分性。
4.2 相關分析
如表1所示,仁慈型領導與工作滿意度(r=0.45,p<0.001)和親組織不道德行為(r=0.23,p<0.001)呈正相關,但與工作家庭沖突呈負相關(r=-0.20,p<0.001);工作滿意度與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呈正相關(r=0.28,p<0.001),但與工作家庭沖突呈負相關(r=-0.37,p<0.001)。

表1 各變量描述統計和相關矩陣(N=379)
4.3 中介效應檢驗
首先檢驗仁慈領導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直接效應,加入控制變量后,仁慈領導直接影響親組織不道德行為(β=0.23,p<0.001)。因此,H1得到支持。將工作滿意度作為中介變量納入模型后,模型各項擬合良好(χ2/df=1.15, CFI=0.99, SRMR=0.03, RMSEA=0.02)。如圖2所示,仁慈領導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0.45,p<0.001);工作滿意度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0.23,p<0.001);仁慈領導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仍有顯著正向影響(β=0.14,p=0.018),說明工作滿意度在仁慈領導和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偏差校正的Bootstrap結果顯示,工作滿意度的間接效應量為0.10, 95%CI=[0.035,0.141]未包含0,表明中介作用顯著,H2得到支持。

圖2 工作滿意度的中介效應
4.4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控制員工的性別、年齡、工作年限和婚姻狀況后,模型擬合情況良好(χ2/df=3.10, CFI=0.93, SRMR=0.04, RMSEA=0.07)。圖3呈現的含乘積項的結構方程路徑分析結果顯示,仁慈領導與工作家庭沖突的乘積項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度(β=0.09,p=0.044),支持H3。簡單斜率檢驗結果顯示(圖4),相較于低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Bsimple=0.19,p<0.001),仁慈領導對工作滿意度的正向影響在高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中得到顯著增強(Bsimple=0.31,p<0.001)。

圖3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圖4 工作家庭沖突的調節效應
有調節的中介檢驗結果顯示(見表2),當工作家庭沖突較低時(取均值減一個標準差),仁慈領導通過工作滿意度影響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間接效應顯著(indirecteffect=0.07, 95%CI=[0.031, 0.125]);當工作家庭沖突較高時(取均值加一個標準差),該間接效應顯著(indirecteffect=0.09, 95%CI=[0.045, 0.154]),但兩種條件下,間接效應差異值顯著(indirecteffectdifference=0.03, 95%CI=[0.003, 0.060])。該結果表明工作家庭沖突顯著調節工作滿意度在仁慈領導與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間的中介作用。具體而言,當員工的工作家庭沖突越強烈,仁慈領導通過工作滿意度影響親組織不道德的間接效應越強,H4得到支持。

表2 不同工作家庭沖突水平下的中介效應(N=379)
5 討論
基于社會交換理論,本研究考察了仁慈領導影響員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中介與調節機制。結果發現,仁慈領導不僅會直接增強員工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還會間接通過提升工作滿意度發揮作用;更重要的是,工作家庭沖突顯著調節仁慈領導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即相比于低工作家庭沖突,仁慈領導顯著增強了高工作家庭沖突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此外,工作滿意度在仁慈領導與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間發揮的中介效應在高工作家庭沖突條件下顯著更強。
5.1 結果分析
本研究在中國情景下開展問卷調查發現仁慈領導正向影響員工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具體而言,仁慈領導在強調員工要為組織創造實質性的利益與產出的同時,也注重激發員工的感激、忠誠與服從。員工出于回報心理和人情壓力,將“忠”置于首位,可能會以不道德的方式來維護組織利益,進而做出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以上結果與以往研究基本一致(Shaw & Liao, 2021; Shaw et al., 2020)。例如,Shaw & Liao(2021)以山東多家企業員工為樣本,支持了仁慈領導與員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正向關系。然而,張永軍等(2017)研究結果發現仁慈領導與員工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不相關,可見仁慈領導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影響具有情景依賴性,發揮作用可能需要一定的邊界條件。
本研究發現仁慈領導不僅會直接增強員工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還會間接通過工作滿意度以發揮作用。這可能因為仁慈領導提供的資源可滿足員工的情感需求,從而使員工形成較高的工作滿意度(劉洋等, 2018)。而工作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員工的角色外行為,工作滿意度高的個體因感激領導和組織更容易利用角色外行為方式來維護組織利益,進而產生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事實上,以往一些研究也支持領導行為通過態度影響員工角色外行為。例如,Wang等(2013)發現家庭支持型領導通過提升員工工作滿意度,從而提高組織公民行為。本研究與上述研究具有一致的邏輯,說明領導與員工直接建立良好的社會交換關系易誘發員工更多的角色外行為。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工作家庭沖突顯著調節仁慈領導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即相比于低工作家庭沖突,仁慈領導顯著增強了高工作家庭沖突員工的工作滿意度,且工作滿意度在仁慈領導與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間發揮的中介效應在高工作家庭沖突條件下顯著增強。這可能是因為在仁慈領導的支持下,高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可化解工作中的壓力,對工作更滿意,從而愿意以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回報組織(Wang et al., 2013);相比之下,工作家庭沖突較低的員工可能未感知到仁慈領導支持的益處,從而不會影響他們對工作的情感反應。
5.2 理論意義
第一,聚焦于仁慈領導的黑暗面,為理解仁慈領導的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視角。以往研究側重于仁慈領導對員工態度與行為的正面影響(Bedi, 2019; Hiller et al., 2019),忽視了仁慈領導的負面作用(王震等, 2019)。本研究揭示了仁慈領導在影響員工道德行為方面的消極效應,提供了一個探究領導有效性的獨特視角,有助于領導理論的豐富和深化。
第二,豐富了社會交換理論的應用情境。以往研究已從社會認同角度出發,證實仁慈領導能夠提高員工對領導的認同,進而產生親組織不道德行為(Shaw & Liao, 2021)。本研究則從社會交換理論視角進行了探索,發現仁慈領導會通過工作滿意度發揮作用,為深入理解仁慈領導對員工不道德行為產生的作用機制提供了有益參考。
第三,通過揭示外部環境在仁慈領導影響機制中的邊界作用,推動學界認清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形成機理。以往研究多關注道德環境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調節(程墾, 林英暉, 2019),而忽略家庭環境的影響。本研究通過揭示家庭環境與組織中領導方式兩大線索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的聯合作用形式,豐富了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誘發機理的認識。
5.3 實踐啟示
由于仁慈領導與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存在正相關,采用仁慈領導方式的領導者需注意可能會帶來的隱患。仁慈領導者在對員工提供支持與關懷的同時,應鼓勵形成崇尚道德的文化氛圍,及時關注并調控組織中的不道德行為,從而更有效地管理組織。此外,組織在招聘和培訓時,也要重視道德和倫理建設。
本研究結果顯示仁慈領導可以通過工作滿意度正向影響員工的親組織不道德行為,這對管理實踐也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領導不僅要重視員工的工作體驗,也要關注員工行為的道德性。管理者應認識到評估與獎勵系統的重要性,將道德行為準則納入獎懲制度,如員工出現不道德行為,將負面影響其薪酬。此外,組織應建立保護機制,鼓勵員工在面臨道德困境時做正確的事,而不必擔心受到譴責。例如,組織可以指定道德倫理審查專員來阻斷員工從事親組織不道德行為。
本研究發現工作家庭沖突顯著調節仁慈領導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這啟示管理者在體恤照顧員工時,需要注意員工的個體差異。針對高工作家庭沖突的員工,管理者需要對其采取更多的道德教育,從而抑制不道德行為的發生。
5.4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與不足。第一,采用被試自我報告的方式收集數據,數據屬于橫截面性質,在未來研究中,可采取多階段的縱向追蹤設計以更好地反映因果關系。第二,未控制其他領導風格與被試道德相關變量,對模型的可靠性具有一定影響。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控制其他的領導風格(如,家長式領導的道德領導和權威領導)及道德相關變量(如道德推脫)以確定特定領導風格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影響的獨特差異。
6 結論
(1)工作滿意度在仁慈領導和親組織不道德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
(2)高工作家庭沖突增強了仁慈領導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的促進效應;
(3)工作滿意度中介仁慈領導對親組織不道德行為的影響在高工作家庭沖突員工中更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