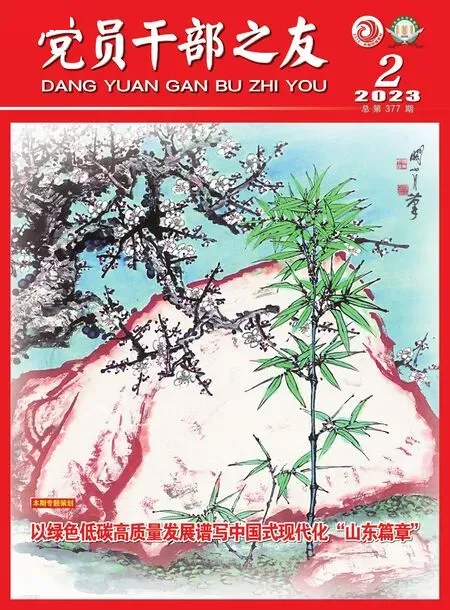『陽』后讀書記
□逄春階

黎青/圖
壬寅年冬,我們都有共同的記憶:不用天天做核酸,心理上特別放松。可是微信上關于“陽”的信息鋪天蓋地發來,又覺得處處有風險,有著小小的焦慮,于是干脆選擇足不出戶,宅在家里。
2022 年12 月14 日中午,幾個老鄉約我小酌,我怕被感染,先是婉拒,但終是禁不住誘惑,半推半就地聚在了一起。臨別,我們彼此祈愿別“陽”了,注意防護。次日早晨5 點醒來,我趕寫一篇文章,感覺渾身發冷,倒無大礙。思路很清晰,我一直寫到中午11 點,四千字的初稿寫完,這時與一位朋友通話,突然感覺嗓子不得勁兒,放下電話,嗓子還是火辣辣的,一量體溫超過37 度。我趕緊用抗原試劑盒自己檢測,兩道杠,陽了。打電話給一起小酌的老鄉,有兩個發燒的。我趕緊吃藥,內弟還讓我把高度白酒溫熱搓腳心。
中招了,我在心理上稍微有點兒小緊張,但不太恐懼。為防止家人被感染,我把自己隔離在書房里。從第二天開始,我流鼻涕,咳嗽,嗓子難受,憋氣,喝姜湯蓋著被子冒汗,枕頭都濕了,還是不行。我生自己的氣,索性從書架上取出李澤厚的哲學著作《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翻閱,一邊咳嗽,一邊看,那佶屈聱牙的表述,平時都無法忍受,這次專門“與痛苦搗亂”。看不下去,我就抄。比如:“康德否認能認識‘物自體’的存在,但認為可以思維它存在,假定它存在。從而,這種存在就根本不同于提供感性來源的第一層含義的存在,而且恰恰是第一層含義的對立面。它也不是第二層含義的認識界限,而恰恰是對這種界限的揚棄。于是,它不再是那個提供感性來源的唯物主義的‘物自體’(不依存于人的客觀物質存在),也不只是那個純粹作為感性——知性認識界限的消極的‘物自體’(它是否存在不可知),而是一個‘不能知之,只可思之’卻能積極存在的‘物自體’了。”抄一遍不行,還糊涂著,再抄一遍,一直折騰到凌晨三點,實在是困了,才上床睡了兩個小時,又憋起來,劇烈咳嗽。
清晨吃飯,我咽稀飯都如刀割,嗓子像冒火一樣。朋友也“陽”了,向我傳授經驗,可以點揉左手食指指甲旁商陽穴,能退燒。我揉了,不管用。按壓咽痛穴兩三分鐘,能緩解咽喉疼痛,我也按了,按得拇指皮都破了,也不管用。還有推薦刮痧的,沿著胳膊內側的尺澤穴開始往下刮,刮到魚際穴,我也刮了,好像管點用,但依舊咳嗽。朋友、親戚發來一些藥方,我也懶得去弄藥。沒辦法,還是看書,拿出趙鑫珊的《貝多芬之魂——德國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貝多芬音樂》讀,其中有引述康德《判斷力批判》中關于“崇高”的一段,我就把宗白華和鄧曉芒的兩個翻譯版本找出來比較,感覺還是宗白華翻譯得更有詩意,于是就抄了兩遍:“粗獷的、威脅著人的陡峭懸崖,那密布蒼穹、攜帶著閃電驚雷的烏云,帶有巨大毀滅力的火山,席卷一切、摧毀一切的狂飆,濤呼潮嘯,洶涌澎湃的無邊無際的汪洋,以及長江大河所投下來的巨瀑,還有其他諸如此類的景象。它們那巨大的威力使得我們抗拒的力量相形見絀,渺不足道,但是只要我們自己處在安全之境,那么它們的面目愈是猙獰可怕,就對我們愈是具有吸引力。我們欣然地稱呼這些對象為崇高。因為它們把我們的精神力量提升到了遠遠的、超出了庸俗平凡的高度,并讓我們在內心發現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抗衡力量,它使我們有勇氣去和大自然這種看來好像是全能的力量進行較量。”這是康德著作中比較好懂的詩意段落,兩個翻譯版本,差別不小,看來比較一下非常重要。我讀了兩個多小時,居然沒咳嗽。
山西的文友說,讀書費眼,可以躺在床上下載喜馬拉雅軟件聽書。這倒是個好主意。中午就躺下聽賈平凹的小說《秦腔》,一直聽到下午4 點半,有時從書櫥上拿出書來對照。《秦腔》剛出版時,我在西安采訪過賈平凹先生,后來就有了聯系。忍住咳嗽,我發短信給賈先生,賈先生說:“我周圍人也陽了五個,多多保重。”著名文學評論家宋遂良教授聽說我“陽”了,即興賦詩一首:“小逄呈陽日/南北盡‘沉淪’/英雄無所懼/一杯劍南春。”宋先生知道我愛喝酒,專門提到“劍南春”,可我現在已經無法喝酒,只給宋教授回了兩個苦澀表情。四天里,連聽帶讀,我把《秦腔》又復習了一遍,比第一次讀,有了更多感悟。
從第四天開始,我突然產生夜晚恐懼癥,害怕黑夜,因為無法入睡。我就起來看智利作家羅貝托·波拉尼奧的《2666》,這是我在10 年前在深圳文博會上買的,那是我在青島采訪翻譯家趙德明時,他推薦的。他翻譯這本書,下了大功夫。當時他囑咐我一定要讀這本書。可是我平時坐不下,就沒看完,放下了(很怪異,書只要放下了,很難再拾起來)。這次拿出來,我看了兩次,躺下,又憋起來,再看,一直看到凌晨三點半,才困意上來迷迷糊糊睡去。
《2666》這本書,869 頁,如果我不“陽”,也許永遠看不完,可這次我是讀進去了。我終于理解了翻譯家趙德明的話,他說:“如果說《百年孤獨》曾經是20 世紀拉丁美洲文學的標桿,可以了解拉丁美洲的‘孤獨情結’,是一部關于拉丁美洲的神話;那么《2666》就是對百年的超越,因為《百年孤獨》的認識和描寫天地還限于哥倫比亞,而《2666》作者的思想已經飛躍到了2666 年!地域范圍遠遠突破了拉丁美洲的天地,即:站在全人類的現實高度看人性惡的膨脹,更預見到未來。”
“陽”了,精力不行。最痛苦的時候,書也懶得翻閱,我就把一些狠話寫到日記本上,比如“反正病毒不讓我睡,我就與你耗到底!病毒病毒我恨你!我看不見你,但我不怕你的猙獰,我詛咒你!你打不敗我!”
第九天,終于一道杠,轉陰了,但是還是咳嗽得厲害。有時,我就坐著睡。一直到2023 年的1 月6 日,才算徹底好轉。回頭看,親戚、朋友之間的守望相助,每一個細節都值得回味。當然,我最感謝的,還是書房里的書。
病中讀書,跟平時讀書還真不一樣。平時就隨便翻,翻完也就忘記了,這次有點把書當“藥”的感覺。沒有特效藥,書,就是藥吧。我把康德、李澤厚哲學的書當藥,把羅貝托·波拉尼奧、賈平凹的小說當藥,把趙鑫珊的哲學隨筆當藥,把《周易》當藥。20 多天不出門,與病毒、與書相伴,我專找那些平時不看的書看,比如翻出已經落滿灰塵的《大自然的詩意哲學》《潘雨廷先生談話錄》《疆村叢書》等,還翻起了1987 年的《文匯月刊》,居然看得有滋有味。
平時讀書,我不愛做筆記,這次我一筆一畫地抄了不少,認真做了讀書筆記。比如看黃立宇的小說《馬廄島》,看到了一段英文,作者翻譯得特別好。那段英文是: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sun moon and you.sun for moring,moon for night,and you forever.我翻譯的話是:我愛三種東西,太陽、月亮和你。太陽屬于早晨,月亮屬于晚上,而你是全部。可是人家翻譯的是:“浮世萬千,吾愛有三,日、月與卿。日為朝,月為暮,卿為朝朝暮暮。”翻譯得文脈充盈,太絕了。如果不記下來,也許就隨看隨忘了。
因為感染,打亂了我原有的生活模式,好像換了個頻道。一整塊時間,忽然從地底下冒出來了一般,看問題也變換了角度。看書也是,是帶著痛感在看,是把書當成了“藥”,也就看得扎實,沒有了浮躁的心態。
隨著身體漸漸恢復,我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但我已經開始讀的幾本書,我會全部讀完。突然地,很珍惜感染的那些日子,很單純,很無奈,但也很充實。看手機的時候少了,看書的時候多了,忽然感覺,不看手機,日子也照樣過。
要是沒有了書,我豈不是白“陽”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