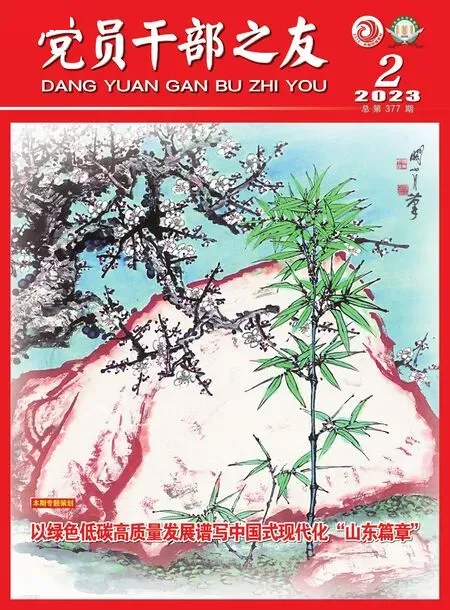一個(gè)下午的四分之一
□朱成玉

鹿毅/圖
午睡后,胸口有些悶,狀態(tài)十分不好,心情自然也差。拉開厚重的窗簾,陽(yáng)光一下子射進(jìn)來,猶如萬箭穿心。這些陽(yáng)光之箭,不傷人,反而是用來治愈的。為了讓更多的陽(yáng)光進(jìn)來,整個(gè)下午的四分之一,我都在擦洗一塊玻璃。
一群燕子,在湛藍(lán)的天空飛過,仿佛在那里潑下了幾滴水墨。春天像閃電一樣來臨,又像閃電一樣短暫。當(dāng)我發(fā)現(xiàn)第一只燕子從身邊掠過時(shí),郊外的草地已經(jīng)綠波蕩漾了。
麻雀?jìng)冊(cè)谠绯繗g歌,而午后便沉寂下來,相依著在密葉間小寐。偶爾竊竊私語(yǔ),輕描淡寫地聊一聊另一個(gè)樹枝上的鳥。
我看到了那朵云,像一扇巨大的翅膀,甚至翅膀里的骨骼都清晰可見,這大自然的神奇之處,令我詫異。
當(dāng)我把藍(lán)山和卡布奇諾混合到一起沖泡的時(shí)候,體會(huì)到了什么是美好。
盡管身體有一點(diǎn)不適,但這些白云,以及卡布奇諾與藍(lán)山交融的香氣,妥帖地?fù)嵛苛宋摇2灰粫?huì)兒,那片云終于散盡,我的心情也已隨之走出陰霾,我想,這片云好像就是為了我而來,也為了我而去的。
我復(fù)制這朵云到我的畫板上,只是,我只能復(fù)制它的形狀,卻無法復(fù)制它的魂魄,因?yàn)楫嫲迳系倪@朵云,沒辦法流下淚水。
所以,還是把它放進(jìn)心里去吧。一顆心,裝得進(jìn)多少白云,就流得出多少眼淚。
在剛剛的午睡里,死去的人,托夢(mèng)來,向我描述地獄。語(yǔ)調(diào)平緩,毫無驚悚的意味。他說地獄里并無酷刑,只有無盡蔓延的冷漠。
我知道這種冷漠,會(huì)讓三伏天的太陽(yáng)都結(jié)了霜。
一個(gè)下午的四分之一,風(fēng)用它溫柔的翅膀,把湛藍(lán)的天空擦得更藍(lán)了。風(fēng)吹動(dòng)萬物,其實(shí),那并非風(fēng)的本意,只是樹葉想動(dòng),云想走,草們一會(huì)兒想對(duì)你點(diǎn)頭致意,一會(huì)兒想趴下小憩。
風(fēng)在到處敲窗,告知我們春天的喜訊,它更為殷勤,也更為直接,不像喜鵲,銜著好消息,卻喜歡賣關(guān)子,總是先清清嗓子,理理羽毛,做足了鋪墊。
兩個(gè)放學(xué)的女孩,一邊走一邊打鬧,笑聲不曾停止。那笑聲,仿佛是青春的響鈴,循環(huán)播放著。一輛120 從她們身邊疾馳而過,救命的鳴笛聲淹沒了那笑聲。
很多花瓣在風(fēng)里飄,有一瓣落到我的窗欞上,那是風(fēng)在提醒,被我們浪費(fèi)掉的花香。
妻子在醫(yī)院護(hù)理岳母,空閑下來,與我視頻。我看到病房里,穿著病號(hào)服的病人來回走動(dòng),而陪護(hù)的健康人都倒去床上酣睡。自動(dòng)取片機(jī)前,那些排隊(duì)等著取化驗(yàn)結(jié)果的人,比山谷里的樹還沉默。但不一會(huì)兒,就有咳嗽聲響起,仿佛起到了帶頭作用,一大片咳嗽聲緊隨而來。
“醫(yī)院是一些咳嗽的房子。”米粒兒說。她的話總是帶給我驚喜。此刻,她跑出去,在窗外蕩著秋千,一只鳥正在替我們打掃庭院。它銜起地上的一片葉子飛走,不一會(huì)兒回來,又銜起一片葉子飛走了。
我安慰著妻子,讓她安心照顧母親。這讓我想起詩(shī)人阿信的代表作《在塵世》,詩(shī)中寫了他和妻子在去醫(yī)院的路上,遇見紅燈,他反復(fù)輕拍著妻子顫抖的肩,說,不急不急。通過這個(gè)典型而樸實(shí)的安慰動(dòng)作,表達(dá)出他們相濡以沫的情感,“身在塵世,像兩粒相互取暖的塵埃,靜靜地等著和忍著。”這種無奈與辛酸,是多少人的共同經(jīng)歷,也是萬千中年人的共同寫照。
遙遠(yuǎn)的寺廟里傳來鐘聲,敲擊人心,有的人癢,有的人疼。老年公寓的老人們,倚在墻根,打盹。一會(huì)兒誰都想不起,一會(huì)兒,誰都在心底。
人世悲欣交集,許多事猝不及防,趁著這個(gè)下午的明媚,我要撿拾回我的率性,想歌就歌,欲淚就淚,不聽奉承話,也不放彩虹屁,不用再為說錯(cuò)一句話而忐忑不安,也不必再為打了一個(gè)飽嗝而心跳加速。說出的話,寫下的字,無須粉飾和潤(rùn)色,只管一條道跑到黑,撞了南墻走北門……
我想守住一些秘密,像小時(shí)候捂住口袋里的牛皮豆,生怕它們不小心蹦出來,掉進(jìn)日光下的人群中。
一個(gè)下午的四分之一,這一生中微不足道的須臾,飽滿、充盈,令我舍不得半點(diǎn)游離。
- 黨員干部之友的其它文章
- 加強(qiáng)新時(shí)代廉潔文化建設(shè)
- 小卡片
- 抗疫路上急先鋒 杏林岐黃傳薪人
——記山東中醫(yī)藥大學(xué)附屬醫(yī)院(第一臨床醫(yī)學(xué)院)黨委委員、第一臨床醫(yī)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賈新華 - 堅(jiān)持實(shí)業(yè)報(bào)國(guó) 振興民族工業(yè)
——記山東魏橋創(chuàng)業(yè)集團(tuán)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總經(jīng)理,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zhǎng)張紅霞 - 堅(jiān)守初心使命 講好山東故事
——記山東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化研究所所長(zhǎng)張偉 - 不讓須眉的女書記
——記濟(jì)南市章丘區(qū)雙山街道三澗溪村黨委書記高淑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