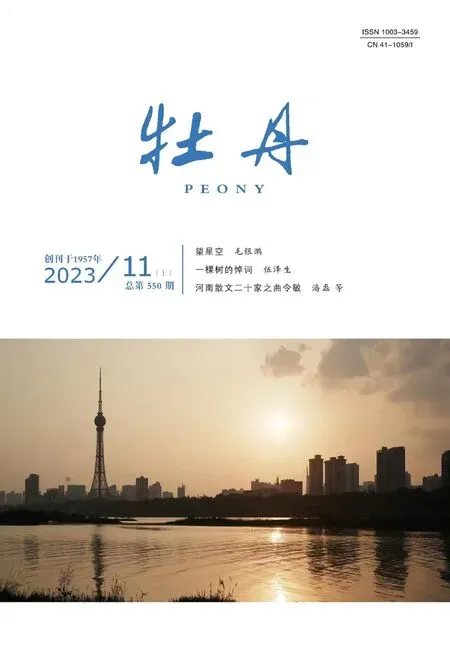冬戲
晉玉靖
嵩縣大章鄉閆溝村是一個普通的農村村莊。二十幾年前的很長一段時期,這個村莊與它四周的鄰村相比,另有一番好氣象,就是這個村里有一臺唱曲劇的民間戲班。每年春節期間,總要高搭戲臺熱熱鬧鬧地唱幾天。
多年來,這個村莊民風淳樸,人人懂禮義守規矩。違法亂紀的人沒有,不孝的兒孫沒有,不敬公婆的兒媳婦也沒有。老人們說,這些好處都與這臺戲的教化有很大關系。
冬天到了,農事閑了,這個業余的團體就開始組織排戲了。村民們也稱這個團體為“劇團”,但與專業劇團不同的是,他們演戲純屬娛樂,沒有報酬。我的父親就是這個團體中的重要成員。
我15 歲的那年冬天,父親病了,病在咽喉,只能喝湯,咽不下饅頭,也去醫院看了,吃了不少藥,卻不見好轉,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母親勸父親不要再去劇團了,父親說演戲是集體藝術,少他一個人就開不開戲,何況他病得苦悶,也想去散散心。
母親要管家,弟妹們又小,無奈之下母親就讓我休了學,天天跟著去陪護父親。
我陪護的任務有兩個,一是每餐照看父親吃飯,伙上的飯不合他的口味時,我需要另外再給他做;二是我的家在一個山嶺上,距離排戲的劇團大院還有五六里崎嶇的山路,每天晚上排完戲回轉時能給父親做伴。冬天夜寒,盤旋而上的林間小路在暗夜里靜得怕人,若遇風雪天,小路上結著薄冰,在山頂就能聽見從山底往上走路的人“咔嚓咔嚓”的腳步聲。我明白母親對病著的父親的擔心。
這兩件事做起來都很容易,何況父親到劇團以后心情大好,很少有讓我單獨給他做飯的時候。這樣,我的大部分時間就是看他們排戲了。
劇團共有三四十個人,樂隊文武場加在一起占十幾個,演員二十多個,兩個團長,一個管生活,一個管業務。生活團長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伯,聽說他大字不識一個,對戲劇的唱念做打一竅不通。他在這劇團主了一輩子事,沒有人聽見他哼過一句戲文。說也奇怪,他就是對村里唱戲這項事業有著特別的熱情。
每年冬天,他最先忙起來。他負責到村中各家各戶籌集錢糧。錢用于每年新的戲裝的添置,糧供應大家立伙吃飯。他還要領幾個人上山砍做飯和下雪天烤火用的燒柴,也管著伙食,哪一天吃什么飯由他來安排。他去誰家收糧食,沒有人不給。收錢,十元不嫌多,一元不嫌少,都用紅紙記上賬,回來貼到劇團大門外的正墻上。
業務團長負責排戲。這個春節要演幾場戲、演什么戲,冬天要復排幾場過去演過的看家戲、要另排幾場新戲、新戲去哪里找劇本、演員的角色怎樣分配,都由他說了算。還有戲文的曲調,樂隊的配器,也由他來定。他還要給演員講劇情。
這個人,就是我的父親。
從農歷十一月初開始人員集中到春節演出,只有兩個月的時間,排練任務很重。每個人都很努力,沒有閑人,也沒有閑的時間。上午,有三五個人聚在一起對戲詞的,有在大院中舞刀弄槍練身段的,有圍著琴師調弦子的,有幾個年輕小伙子在另一間大教室里練習打鼓的。下午和晚上全體樂隊坐場排戲。每一場戲,樂隊和演員沒有十遍八遍磨合是排不成功的。這樣,劇團大院內,整日吹拉彈唱,熱鬧非凡。
他們先排練好了幾部過去演過的戲,準備再用二十天時間排一部新戲。父親對每年要排的新戲特別上心,因為這一部新戲是全村群眾新年的最大期待。劇本已選好,是二十四孝圖中有記載的《安安送米》。劇情大意是:書生姜詩娶妻龐三娘,生性刁鉆的姜妹在母親面前挑撥是非,姜母偏聽偏信,逼姜詩休妻,將龐三娘趕出家門。三娘無顏回歸娘家,寄身于尼姑庵中,受盡饑寒。其子安安,年方七歲,在南學每日從自己的口糧中省下米糧,積攢數月后,冒著風雪到尼姑庵尋母,把米糧送給母親的故事。
演員已經定好,戲詞也背過,開始拉場了,這個演安安的演員,在情感上入不了戲。他的母親已被奶奶和姑母趕出家門了,他站在那里面無表情。送米一折有很悲傷的戲文,他也唱不出感情來。不行,又換了一個人,也不行,和上一個一樣,骨肉分離時不悲,全家團圓時不喜,任憑父親怎樣給他導戲,他也表演不出一個孩童該有的性情。找不到合適的安安,這部戲就排不成,眼見十幾天時間已耽誤過去,另選新劇要來不及了。父親很著急,恨不得天上能掉下一個“安安”來。
那天晚上,我不知從哪里來的勇氣,走上前去,對大伙說,讓我試一試吧!父親急忙攔住,說別添亂,快站一邊去!
這時,有幾個老演員為我幫腔,說就讓孩子試試吧,這么多天都過去了,也不差這一個晚上。父親說她曲調不會,戲詞也不會,又從小靦腆,沒有大聲說過話,不是上舞臺的料,別聽小孩子胡鬧。我趕忙說,我會,我會!我已經看會了!
我口中答著話時,就快步往中場一站,先喊一聲“爹”,再喊一聲“娘”,大大方方,不害羞,不怯場。蒼涼哀怨的曲胡旋律一響,那真是話未出唇淚先流,我唱的一字不差,聲情并茂。龐三娘被趕離家園時,小安安抱著母親的腿哭得呼天搶地,嬌滴滴的孩童嗓音叫得人肝腸寸斷。同場的演員都感染得哭了,那真是好好的一個家庭瞬間就要散了,父也哭,母也哭,孩子也哭,一家人生離死別,哭成了一團。在一旁看排戲的觀眾,人人都入了戲。全場靜悄悄的,個個淚流滿面。
安安送米那一折,小安安背著重重的一袋米糧,在風雪交加的背景和蒼涼的器樂聲中踉踉蹌蹌上場。米重,身小,天寒,路滑,還要趟過一條小河。唱詞唱腔悲傷悲痛,曲胡伴奏如泣如訴,幾個滾身翻得干凈流暢,數聲念白道得鬼神心傷。我完全化作了戲中人,將一個七歲孩童思母孝母的形象表演得淋漓盡致。
散場了,掌聲響起來,我站在那里不動,心緒還在戲中。幾個叔叔阿姨快步上前,大笑著把我抬了起來。
這時,生活團長袁老伯走了進來,他手中端著一碗熱湯,說今晚特意安排做了夜宵,叫大家熱乎乎吃點再回。他說著這話時,已笑瞇瞇地把他手中的碗筷雙手遞到我的手中。說:小安安,快吃吧,你救了這場戲了!劇團加餐做夜宵,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事。
我不敢先吃,忙放下碗筷去尋我的父親。那一刻,我怔住了,我看見父親一只手端著一碗湯,另一只手還拿著一個饅頭,要知道,我的父親因病已經連續幾個月沒有吃過饅頭了。我不敢驚動他,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看著他一口一口把這個熱乎乎的饅頭咽到了肚里去。那一晚上我沒有吃夜宵,兩行激動的熱淚順著我的面頰止不住地流淌。
唱罷這個春節,父親的病竟然痊愈了。我就返回了校園,課業緊張,再也沒有機會和父親一塊兒去看排戲。父親說,《安安送米》這部戲在閆溝村只演了那一年,因為,以后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合適的安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