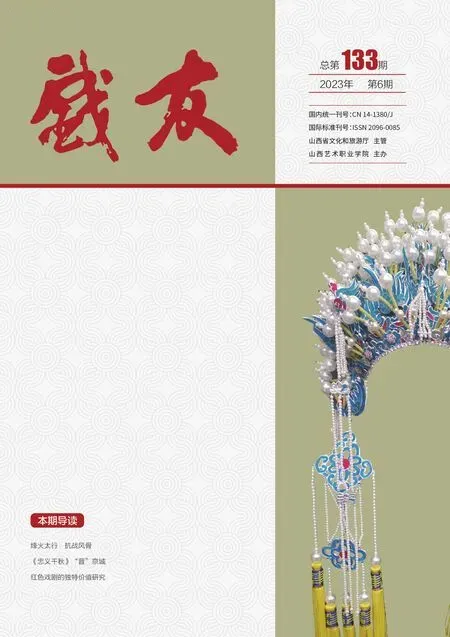試論明清河南山陜會館劇場形制與演劇活動
吳曉麗
山陜會館是山西、陜西籍商人在河南地區集資興建的館所,是同鄉同行業協商議事、維護權益、祭神拜祖之所。明清時期,河南因地處中原地帶,水路交通比較便利,因而成為重要的商業中心,也是山西、陜西商人活動的主要商業區域。正如《南陽賒旗山陜會館旗桿記》碑載:“(南陽)水陸之沖,商賈輻輳,而山陜之人為多。”①河南地區的山陜會館主要分布在豫中、豫西南地區。根據文獻資料記載,在豫的山陜會館多達80余座。這些山陜會館形制完備,功能齊全,是山陜商人在豫開展交流、祭祀等活動的重要場所,對研究民間鄉神崇拜、戲曲傳播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一、劇場形制
《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卷》“劇場”條目指出作為劇場所包含的要素:“觀眾觀賞演出的地方。此詞源自希臘文‘Theatron’,意為‘一個為了看的地方’。中國原有‘茶園’‘戲樓’或‘戲園’等名稱,現統稱劇場。古代或現代的劇場至少由兩個部分構成:一是進行演出的地方,即舞臺;二是觀看演出的地方,即觀眾席。”②可見傳統劇場的組成包括表演空間(戲臺)和觀眾席(看樓、看亭、看壩等)兩個部分。山陜會館既是民眾酬神演劇的重要場所,也是傳統劇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整體布局、戲樓裝飾和劇場選址上均具有特別的文化價值。
(一)廟館合一的建筑形制
梁思成先生指出:“以多座建筑合組而成之宮殿、官署、廟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齊之絕對整齊對稱之布局。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線之成立,一切組織均根據中線以發展,其部署秩序均為左右分立。”③河南地區山陜會館的建筑布局相同,均由山門、戲樓、正殿及兩廂組合成一進或二進四合院落,少者建有照壁、拜殿、后殿等建筑。如河南省老城區九都東路隋唐大運河博物館山陜會館,建筑整體坐北朝南,兩進四合院,中軸線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有琉璃照壁、山門、戲樓、拜殿、正殿,中軸線兩側分布有西門樓、東西儀門、東西廊坊、東西官廳、東西配殿等。河南省平頂山市郟縣山陜會館,整體建筑坐北朝南,中軸線上自南至北依次為照壁、山門、戲樓、正殿和后殿,呈二進院落布局。其中戲樓東西兩側對稱為鐘鼓樓,正殿和后殿兩側為東西配殿。河南省輝縣市文昌大道山西會館關帝廟,整座建筑坐北朝南,中軸線由南向北依次為山門、戲樓、拜殿、正殿,兩側有配殿、鐘樓、鼓樓,呈兩進四合院布局。所有建筑連接形成一個內向封閉空間,主要建筑均在南北軸線上,總體呈現“軸對稱式”布局,其中戲樓均為過路臺,朝向正殿,一面觀或三面觀,臺前空場或大或小,可容納觀眾看戲。這些形制布局與廟宇劇場有著較高的相似度,究其原因,是與山陜會館“酬神娛人”的功能密不可分。《創建晉冀會館碑記》有說明:“歷來服官者、貿易者、往來奔走者,不知凡幾,而會館之設,顧獨缺焉……雖向來積有公會,而祀神究無專祠,且朔望吉旦群聚類處,不可無以聯其情而洽其意也。議于布巷之東蔣家胡同,購得房院一所,悉毀而更新之,以為邑人會館。”④晉冀商人“祀神究無專祠”,且“無以聯其情而洽其意”的場所,從而建設會館。山陜會館同樣以山西籍人士為主要成員,他們有共同的地域和文化認同,因而山陜會館的功能之一,是為滿足山陜籍商人對于關公信仰的鄉神崇拜而建。更有甚者,直接在寺廟的基礎上改擴建而成,據《沁陽縣志》載:“八府寺,在西關祭祀關公,今改為山陜會館并祀關公。”由此可見,在八府寺的基礎上改建為山陜會館以祀關公。因此,在建筑形制上形成了“廟館合一”的形制特征。

河南省洛陽市老城區九都東路山陜會館
(二)精巧富麗的裝飾藝術
山陜會館在戲臺裝飾上極其精美,頗具耗資,無論是雕刻、彩繪的豐富性,抑或手法、取材的多樣性,都可窺見富麗堂皇的裝飾特色。如周口山陜會館從修建到完工,歷時150 余年,其間重修、擴建10 余次,動輒花費上萬兩白銀;洛陽關帝廟也是“狀貌巍峨,極翬飛鳥芽之奇觀,窮丹楹刻桷之偉望”;如河南省南陽市社旗縣賒店鎮永慶街5 號的山陜會館,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76),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至光緒十八年(1892)落成,全部工程歷時137 年。有“中國第一會館”美譽的社旗山陜會館坐北朝南,中軸線上自南向北依次為琉璃照壁、懸鑒樓(戲樓)、大拜殿和春秋樓,呈二進院落布局。社旗山陜會館于1998 年1 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戲樓名為“懸鑒樓”,又名“八卦樓”,始建于清嘉慶元年(1796),竣工于清道光元年(1821),歷時25 年,是全國保存最完整的三層戲樓。戲樓坐南向北,三重檐歇山式樓閣建筑,通高30 米,如翚斯飛,玲瓏雄偉。三面觀,過路臺,戲樓面闊三間12.36 米,其中明間面闊4.84 米,下層高2.19 米,角柱高3.25米,柱礎高0.67 米,臺口高3.65 米。通進深10.10 米,其中前臺進深4.45 米。戲樓規模宏大,結構精巧,是中國古代建筑的藝術精品。由于山陜會館作為山陜籍人士向關帝表示謝意和虔誠的固定場所,戲曲表演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娛樂神靈,而戲臺作為戲曲演出的場所,戲臺在建設和修葺過程中會被傾注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時間成本,最終呈現富麗堂皇的裝飾特色。
(三)通衢大道的選址偏好
山陜會館的選址,從宏觀角度來看,多位于交通或商路要道之上,具有集聚性。從微觀角度來看,山陜會館是籌資新建,亦有在家宅或廟宇基礎上修葺而建,具有隨機性。如開封的山陜會館,“聊攝為潛運通衢,南來客舶絡繹不絕,以吾鄉之商販者云集,而太汾兩府尤多。白國初康熙問來者肩相摩,踵相接,橋寓旅社幾不能容。議立公所,謀之于眾,捐厘醵金,購舊家宅一區,因其址而葺修之,號日‘太汾公所’。”⑤“太汾公所”為山陜會館的前身。由于“潛運通衢”的優越運輸條件,“吾鄉商販云集”以致“橋寓旅社幾不能容”,通過對家宅的修葺即可成為會館。而具有財富象征的山陜會館,對于選址家宅而建具有共識。之所以形成這樣的特色,原因在于商賈因利而往來,而優越的商路或水路等便捷的區位因素,意味著當地相對可觀的經濟市場,以及對于拓展和鞏固異域市場具有便捷途徑和較少成本。
由此可見,在相對優越的區位因素影響之下,使得商賈不斷積累財富,而為了滿足其酬神娛人的心理夙愿和精巧富麗的財富象征,便在商道上選址建有山陜會館。山陜會館的建制不僅遵從了軸對稱的形制特色,還以戲臺為會館酬神娛人的重心和核心。
二、演劇活動
山陜會館作為秦晉商人在異鄉的家園,自然少不了以鄉音解鄉愁。每逢節日活動,必然會請家鄉的演樂人員前來唱戲以表祝賀。“商路即戲路”,但凡有秦晉商人的地方,其演劇活動也異常豐富。成書于康熙至乾隆年間的小說《歧路燈》,曾多次描寫有關山陜會館演戲的場景,為我們了解這一時期山陜會館中的演劇提供了有力例證。如該書第四回記載:“俺曲米街東頭巫家,有個好閨女,他舅對我說,那遭山陜廟看戲,甬路西邊一大片婦女,只顯得這巫家閨女人材出眾。有十一二歲了……孝移見王氏說話毫無道理,正色道:‘你不胡說罷,山陜廟里,豈是閨女們看戲地方?’王氏說:‘他是個小孩子,有何妨?若十七八時,自然不去了。’”⑥其中也提到女性觀看戲曲時不能隨意出現在公眾場合。目前現存清代的廟宇、會館中,多有專門為女性觀眾觀看表演所設的看樓、看臺等。這也說明了當時戲曲演出活動的繁榮景象,女性觀劇的盛行。在豫的山陜會館其演劇活動主要集中于傳統祭祀演劇、罰戲演劇、商業演劇等方面。
(一)祭祀演劇
在山陜會館中,秦晉商人秉承著“忠”“義”“禮”“信”等經商理念,都希望平安、避兇、生意順利,關公作為晉秦等地的家鄉神,在豫的山陜商人也敬奉關公,而在歲時節令演劇便是其祭祀神靈的重要活動。如河南周口山陜會館光緒二十四年《山陜會館捐厘部署繼美盟心碑文》載:“日射歌臺,風回舞榭,人散一聲,經問僧舍……梨園送響,古妙英謳,疊曲霓裳,舞散離愁。”⑦會館的鄉親每逢歲時節令都會設筵演戲,祭祀關公以祈求經商順利。又有河南沁陽山陜會館《重修關帝廟碑記》中記載:“商賈抑去父母之邦,營利于千里之外,身與家相睽,財與命相關,祈災患之消除,惟仰賴神明之福祐,故竭力崇奉。”⑧遠在異鄉經商的鄉親,通過獻戲還愿以保佑來年身體健康、生意順利。同樣,開封地區的山陜甘會館也祭祀關羽。《開封民俗》記載:“在開封的山西會館,特定旅汴同鄉于五月十三日聚集,設三牲大祭關圣,并演戲一天,關岳廟有廟會,民國前巡撫盡享,所有武官及武舉、武秀才均得隨之跪拜,全市商業亦各自祭。這一天相傳為關公磨刀赴會之期,早晨必雨。開封地區卻傳為關公磨刀斬鬼之日,每年是日有雨,俗稱‘磨刀雨’,也稱‘雨節’。”⑨每年五月十三正值夏至前后時,白日較長,日照充足,氣溫較高。及時降雨可緩解干旱以確保農作物豐收。
(二)罰戲演劇
除祭祀演劇外,會館中還出現罰戲這一特殊的演劇活動。如社旗山陜會館中《同行商賈公議戥秤定規概》中記載會館組織山陜商人議定戥秤的事宜時,規定“公議之后,不得暗私戥之更換。犯此者,罰戲三臺。如不遵者,舉秤稟官究治。”⑩相比于報官秉公處理,罰戲是一種較為人性的懲罰方式。在樹立規矩懲罰同行的同時,以獻戲的方式獲取同行的諒解,也可以增強行業商人的凝聚力。《歧路燈》第八十四回亦載:“那老客商道:‘今日望日,關帝廟午刻上梁,社首網三爺嚴明,有一家字號不到,罰神戲三天。爭擾譚爺一杯酒,誤了上梁燒紙馬,要唱三天戲哩。’紹聞道:‘三天戲俱是敬得起的。’盛希僑道:‘賢弟大差,神圣大事,如何可誤?只得送列位赴廟獻神。’”?足見,會館內設置懲罰機制對于商戶的約束略有成效。除此之外,還有郟縣山陜會館每年在二月二十日會演戲一臺,用以聯誼同鄉。正如社旗山陜會館《重修山陜會館碑記》記載:“敘鄉誼、通商情、安故旅”。可見會館中的戲曲演出具有規范行業、共敘鄉誼、行業交流等功能。
(三)商業演劇
在豫的山陜會館都建于交通要道、商業較為發達的城市,如在開封、洛陽、周口、社旗等地均建有山陜會館。貿易的往來帶動著城市的繁榮,各大會館都建有戲樓用以組織演戲觀劇等活動。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祭祀演劇和罰戲外,在豫的山陜會館還具有商業演劇功能。上蔡縣民教館在1934 年7 月創辦戲劇訓練班,“經訓練所演新、舊劇八十余出,前日下午在城內山陜會館公演《馬關條約》,觀眾無不痛恨滿清及日本強暴。”?在20 世紀30 年代,河南地區在進行戲曲改革活動時,在開封地區也出現培養戲曲人才以宣傳戲曲改良活動。1920 年2 月18 日,《河聲日報》中記載:“近日菊部王某組織一反調新班,并邀集京、滬男女名角來汴協助,以與各戲園競爭,并定于二十日假山西會館開演會。”?這一則報道可以看出,在民國時期,會館內的演出已出現具有商業性的戲園競爭演劇活動。除此之外,為招攬商客,擴大貿易,一些廟會演劇、集會演劇等隨著廟會、集會等商業貿易活動應運而生,這些演劇的戲資多從集會收入中去支付,因而演劇已具有商業性的特點。
除了在山陜會館中進行商業演出外,部分山陜會館也承擔著私人“堂會”演出的功能。《中國戲曲志·河南卷》中收錄了《王宅堂會戲目表》?,該表反映了民國時期王家邀請劉奎官等名角前往會館演戲的活動情況。根據節目單可以看出因是“堂會戲”,所以其演出的劇目自然少不了《拜壽》《八仙慶壽》等吉祥戲,邀請演出人員也多為名角,如表中的劉奎官乃京劇名凈,曾因演紅生戲與周信芳、趙如泉等名震上海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職中國戲曲家協會云南分會副主席、云南省京劇院院長等。
明清時期,山陜會館中的演劇活動,是商人擴大社交區域的手段,是促進商業貿易的工具。其對戲曲文化的傳播起到了宣傳推廣作用。正如“館內好戲連臺,館外徐府街集市上人海如潮……真是會館因集市而興,集市因會館而旺。”?因此,會館與戲曲傳播之間相輔相成,起著同發展、共促進的作用。同時,晚清民國時期,單純的祭祀儀式逐漸增加了集貿功能,這一時期的演劇已經具備商業性特征。而到了民國時期,河南地區城市發展、戲劇改革活動對其戲曲演出活動也有所影響,其大都借助河南地區的山陜會館進行宣傳、商演等活動。
注釋:
①此碑現存東馬棚北,座已佚。碑高2.05米,寬70 厘米,厚18 厘米。參見山西省政協《晉商史料全覽》編輯委員會編《晉商史料全覽·會館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43 頁。
②曹禺、黃佐臨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203 頁。
③梁思成《中國建筑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 頁。
④⑦⑩分別摘自山西省政協《晉商史料全覽》編輯委員會編《晉商史料全覽·會館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48 頁、第193 頁和第140 頁。
⑤許檀《清代河南、山東等省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選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353 頁。
⑥?分別摘自(清)李綠園著《歧路燈》,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頁和第413頁。
⑧參見沁陽山陜會館《重修關帝廟碑記》。
⑨陳雨門、韓德三《汴梁瑣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11 頁。
??分別轉引自張召鵬《民國時期河南戲劇演出情況考察》,河南大學2010 屆碩士學位論文,第33 頁和第55 頁。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河南卷》,中國ISBN 中心出版社2000 年版,第561 頁。
?王瑞安《山陜甘會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9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