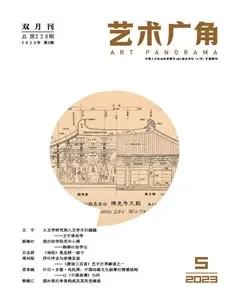致“盲”影像:邁克爾·哈內克的技術之思
羅藝 謝建華
摘 要 從電視電影時期到大銀幕時期,劇中影像一直是邁克爾·哈內克電影中的重點描繪對象。在電影文本中,媒介所承載的影像有著通過編排與界面化重塑人物認知的功能。而在電影文本與觀眾之間,存在著導演精心創造的返觀內照的形式,媒介在此現身,觀眾由此辨清自我的處境。從技術哲學的角度出發,可以看出導演的創作根源在于展現媒介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焦慮與反思。哈內克在呈現一種致“盲”影像,“盲”在于影像對于世界的去真實化復現,“盲”也在于數字時代影像生產中對于“無”的追求。
關鍵詞 影像;媒介;媒介技術;技術哲學
邁克爾·哈內克,奧地利籍導演,戛納電影節“雙金棕櫚俱樂部”成員,憑借《愛》《白絲帶》《鋼琴教師》等作品在國際上大展拳腳。哈內克并非年少成名,46歲才拍攝了第一部電影。近20年在劇場與電視臺同時工作的經歷,給這位“大器晚成”的歐洲電影大師帶來了獨特的影像風格。而這其中,劇中影像的使用成為哈內克的標志性特征之一。
劇中影像,即影片內部用媒介轉載的影像。哈內克通過電視、數碼相機、電腦、手機、視頻播放器等媒體,在影片內播映電視新聞、訪談節目、娛樂節目、家庭錄像帶、DVD視頻、網絡社交界面和手機直播節目等,使作品帶有鮮明的媒體引用性質。通過轉載媒介觀察世界、思考現實,這位哲學家出身的導演借此給影片涂抹上了濃郁的哈內克色彩。
一、情感冰川——意識的重塑
1.意識代具化
斯蒂格勒指出,當前正在進行意識的代具化過程,即時間客體的工業化生產。這種意識的代具化成為了個性化過程的障礙,從而導致該意識完全被摧毀。[1]哈內克作品中的劇中影像對應著工業化生產的時間客體,而劇中影像作用于劇中人物,便呈現出意識的代具化過程:一間房,一個閃爍著的熒幕,一個人物背影,而人物總處在觀看狀態。人物不僅接受這些熒幕上所呈現出的影像內容,還借這種影像呈現的方式去認識世界。具體來說,導演作品中的影像有重塑人物認知的功能,這一功能通過編排與界面化兩種方式實現。
編排是指數字影像呈現的內容與邏輯。無論是愛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論還是“庫里肖夫效應”,抑或是格里菲斯的蒙太奇手段,究其根本,都可視為對影像的編排,并通過這樣一種編排去達到某個預期的效果。在《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中有大量的、整段的新聞內容呈現,這些新聞內容從某種意味上指涉著影像的編排“法則”。
首先是內容上的選擇,導演所選的新聞內容多為刺激性的話題,如戰爭、恐怖襲擊、暴力事件等。其次,對新聞呈現順序進行編排,將民生類、國際時政類、娛樂類的內容前后并置,如在該片末尾處的新聞播報中,第一條為民生類新聞,平安夜前夕當地的槍擊事件;第二條是國際時政類新聞,炮火中的薩拉熱窩;第三條為娛樂新聞,邁克·杰克遜孌童事件。這是一種對于暴力新聞的廣泛傳播,但同時展現的又是被閹割后的暴力。各類新聞的編排并置,使得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沖擊力相互抵消,暴力事件中的真實痛感也隨之止步于熒幕。
如果說《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還不足以凸顯影像呈現的編排意味,那么在《隱藏攝像機》中,導演則直接通過反身性的方式,展現出電視訪談節目的錄制及后期制作過程。導演將影像成品形成之前的內容選擇、拼接直接呈現在觀眾面前,讓影像的編排“法則”浮出水面。
界面化主要是指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哈內克在訪談中提到,在生活中我們眼見一切,但我們沒有在看。而當人們透過攝影機的觀景框時,觀看才會更專注。[1]因而,在哈內克作品中,人物傾向于通過影像框來觀察世界,這樣一種“框”主要通過相機來呈現:《班尼的錄像帶》中用數碼攝像機記錄一切的班尼,《快樂結局》中用手機鏡頭與世界交流的女孩,《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中用破相機記錄異鄉的羅馬尼亞孤兒……在他們眼中,世界是矩形框形狀的,正如界面上的影像。
具體來講,《班尼的錄像帶》中有大段錄像帶畫面的整屏呈現。這是由班尼拍攝的,也是班尼眼中的世界,一個界面化的世界。班尼住在一間陰暗的房間里,房間里的窗簾一直拉著。他的攝像機24小時監控著街道,通過信號傳輸外面的世界呈現在監視器界面上,真實世界由此被轉譯成一個可控制的虛擬現實。在班尼與無名女孩相遇時,女孩之所以能夠引起班尼的注意,正是因為在班尼的視角下女孩正好位于櫥窗框內。
安妮·弗雷伯格認為,繪畫、暗箱、電影與當今的數字移動設備的共同點在于“窗戶”這一隱喻。窗戶明確的邊框將現實切割,正如所有界面所呈現的那樣。“這是一個純粹的切割部分,有明確界定的邊緣,不可逆,不可侵蝕;圍繞著它的一切都被放逐到虛無之中,維持無名的原始之狀,而邊緣內的一切都被賦予本質、被照亮,由此進入視野。”[2]也就是說,當主體處于“框”內形成一個類似界面的狀態時,班尼才會集中注意力進行觀察。而界面化觀察之下,“畫框中的女孩”便成為班尼的第一認知。女孩已不再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生命,而只是框中的虛擬對象。與此同時,現實中的道德、規則也被分割在框外,消匿為虛無。
2.影像癥候群
《第七大陸》《班尼的錄像帶》與《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合稱為“冰川三部曲”。此前導演聲稱這些電影旨在反映“奧地利日趨明顯的情感冰川”。“冰川”即情感上的冷漠,指向哈內克電影中人物的疏離狀態。這樣一種疏離狀態并非只存在于“冰川三部曲”中,而是在大銀幕開山之作《第七大陸》之后便一直延續在其作品中的一種“癥狀”,即意識代具化后人物所處的狀態。
按照時間順序綜觀哈內克的作品,會發現《第七大陸》的結尾有著超越于單個影片的意義。在該影片的結尾處,中產階級的一家三口封閉在家中,摧毀掉一切他們賴以生存的、用以進行身份確認的所有物質(如賣掉車子、砸毀家具、剪爛衣物、將現金沖進馬桶等),只留下一臺電視機。最終,在電視機閃爍的熒光中,在電視歌唱節目音響的陪伴下,一家人服毒死去。
在某種意味上,這個結尾似乎成為了一種寓言,預示著此后哈內克電影中的人物狀態,在意識代具化后,人物處于一種圈囿于影像、疏離于現實與自我的狀態。
一方面是主體的自我疏離。重塑認知后的主體呈現出一種分裂狀態,過去衡量人之所以為人的評判標準開始失效。這樣一種狀態在人物身上最直觀的表現是普世道德觀建立的失敗。在《班尼的錄像帶》中,班尼模仿殺豬方式殺掉陌生小女孩后,表現出一種可怖的“異常”狀態:喝酸奶、上洗手間、伴隨電視欄目寫作業、清理血跡、洗床單、與朋友電話閑聊、拍攝尸體、回看尸體錄像帶、和朋友去酒吧、在朋友家過夜。人物的反應與行動是如此的從容、怪異,令人不適。而當班尼將殺人錄像帶向父母展示時,父母沒有道德辯論,只有掩蓋罪行的討論。而后,母親帶班尼去埃及度過豪華假期,當他們回來時,父親已經將尸體肢解并處理掉了。所有事情像沒有發生過一樣,一家人回歸日常。父母的態度將這種個別的“異常”轉向了一種普遍性的“常態”——一種自我分裂、疏離的非人常態。在之后的《快樂結局》中,我們可以看到處于同樣狀態的小女孩是如何用類似的手法對親生母親下毒并致其死亡的。
另一方面則是主體間的疏離。主體間的疏離表現為現實生活中的失語。哈內克的電影中極少展現正常的日常生活交流場景,即便是在同一餐桌上的人物也無法進行日常交談。人物之間要么無法溝通,要么必須借助媒介交流:班尼只能通過錄像帶或者攝像機與人交流,包括班尼對著攝像機敞開心扉的獨白、以錄像帶的方式告訴父母及警方殺人的事實;《隱藏攝像機》中同樣以神秘錄像帶進行信息傳遞;《快樂結局》中冷漠的餐桌對話、手機直播上的交談、女孩父親在社交網上與情人的互動、大女兒與情人通過電話維系情感;《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中在奧地利街頭游蕩的不會德語的羅馬尼亞小孤兒試圖以破相機與周遭產生關聯、老鰥夫辱罵自己的女兒、孤僻不言的女孩被養父母拒養、銀行職員對妻子說“我愛你”時被妻子嗤之以鼻并扇巴掌,等等。同樣在《鋼琴教師》中,由伊莎貝爾·于佩爾所飾演的鋼琴教師與長期沉迷于電視的母親無法正常溝通,母親以一種極端控制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女兒的愛。而女主人公自身被困于色情錄像帶所呈現的親密關系中,以致于在與現實中的戀人相處時呈現出一種扭曲狀態。
質言之,代具化過程不僅存在于內容的編排中,更顯現于承載這些內容的界面本身。這是對主體認知的摧毀,“憑借認知事物的獨特能力,人在賦予世界意義、價值和真實性的同時,也開啟了一個解體的進程”[1]。而摧毀隨即帶來的便是重構,從而在人物身上顯現出由影像所引發的癥狀。換言之,這個在此狀態下的劇中人物變得“盲”而不可見,在這之中一切真實可感的話語、動作都被攔截在空中,無法傳遞,也無法被解讀。
二、返觀內照——技術的現身
哈內克曾在采訪中提到,“我如何給觀眾一個機會,讓他們認識到現實的失落和他自己在其中的含意,從而把他從媒介的狂熱中解放出來……更確切地說,我給觀眾什么機會去認識我在展示什么呢?”[1]換言之,哈內克追求的是創造一種形式,一種能讓技術現身、揭露意識代具化具體過程與手段的形式,從而讓觀眾辨清自身處境。
哈內克通過由影像來開場與結尾的方式塑造出一個影像世界的閉合圈,并將現實世界封鎖在其中,形成一個影像世界包圍現實世界的結構。與此同時,觀眾被放置于圈外,即一個類似于上帝視角的位置。觀眾由此反觀自身,認清自我淹沒在技術世界的處境。可以看到在《班尼的錄像帶》《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隱藏攝像機》《快樂結局》中,哈內克均采用了這種結構安排,旨在揭露世界在媒介技術下的去真實化過程。
一種媒體(影像)依附在另一種媒體(影像)之上,就像勒內·馬格利特《禁止再復制》中男人在鏡子面前看見自己一樣。[2]在這里,鏡子里的主體不再是簡單的光學反應,而是另一種秩序下的“現實”。觀眾之于電影影像,就像男子之于鏡中世界一樣。觀眾在電影影像面前看見的不只是自身的影子,還有形成所有一切并隱匿其中的運行法則。而這種法則就是媒介技術操控意識、重塑意識的方式。
《機遇編年史的71塊碎片》中,影像圈內的現實世界慢慢被影像所吸納。從片名來看,“71塊碎片”表明整部影片由71個片段組成。從敘事層面來看,這“71塊碎片”構成了多線敘事的結構。第一層面,可分為電視新聞(即影像世界)與現實世界兩大板塊。而第二層面,則可以進一步將現實世界劃分為羅馬尼亞孤兒、銀行安保員與妻子、19歲大學生、試圖領養小孩的夫婦、與女兒不和的老鰥夫5個板塊。
第一步,影像與現實并行不悖。全片共出現5段電視新聞,分布在前中后三個部分。影片開場設計為一段電視新聞,新聞內容為“索馬里內戰”。緊接著,一個正在跨越邊境的小孩出現在畫面中,鏡頭跟隨著小孩進入這座城市,現實部分的板塊由此依次出現。中間部分,電視新聞與現實交替呈現。結尾處,在現實部分19歲學生槍擊案后,以圣誕節主題的電視新聞作為結束。結尾部分的新聞勾聯著影片中間的新聞,再與開場的新聞鏈接在一起,便形成一個閉合的影像圈。而另一大板塊的現實部分則以碎片的形式分散在影像圈中。
第二步,影像吸納現實。現實部分5個板塊下的零散片段游離在影像閉合圈中。毫不相干的5個板塊,最終在結尾處意外地連接起來,并一同出現在電視新聞中。于是,這便形成一種對比結構——現實的事件通過影像來復現。一是羅馬尼亞孤兒成為了訪談對象。走投無路的他走進警局,并接受電視臺的采訪,訴說自己的流浪經歷。二是19歲學生在銀行開槍并飲彈自盡的事件成為新聞。周圍市民成為被采訪對象,新聞報道試圖通過現場警方的辦案畫面與市民的話語去還原事情的原貌。巧妙之處在于,導演在結尾處先播放了1993年12月23日的電視新聞片段。接下來開始呈現現實部分的片段,5個板塊的主要人物各自行動,開始向銀行聚集。其中,19歲學生沖進銀行開槍射擊。緊接著,槍殺案以新聞的形式與之前12月23日的新聞并置進行再次播放,真實事件轉換為真實事件的影像。
哈內克認為,“人們常常在真實事件中的不安感與觀看人造影像中的現實形象時的情感安全感之間搖擺不定”,因而“對于觀者來說,真實的存在與圖像之間的界限很難從一開始就確定”。[1]易言之,正是由于觀眾位于熒幕面前而不是親臨現場的觀看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影像的人為處理方式,使得觀眾能夠在任何沖擊性的影像面前從容淡定、心安理得。正如導演在《班尼的錄像帶》中借班尼之口所表達的那樣:“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一些用在動作戲里的把戲,全是用蕃茄醬和樹脂做的。但看起來和真的一樣。”
在影像的包裹下,“隨著‘非真實很快成為‘真實的標準(兩者之間的分界線越來越難以確定),在人類互動的世界里,適宜于游戲和娛樂世界的審美標準很可能已取代現在不相關的道德標準”[2]。于是,假和真融為一體,無法分辨,以致于在對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施暴后,班尼也可以如此從容。
職是之故,導演通過結構上的設計安排,使得被模糊的、現實世界的邊界得以顯現,電影觀眾也得以清晰地辨析出現實被影像吸納的過程和方式。通過這樣的對比,影像似乎并未在復原現實,而是在改寫、重組、抹去現實。在新聞中,我們看不到19歲少年的掙扎、痛苦,也無法與遇害者感同深受。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個體,被共同歸結為一個遇害者總數。所有的真實被遮蔽在熒幕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歲少年槍擊案源自真實事件,導演將其改編成電影,又在電影中將其進一步轉化為電視新聞。這就正好應對了導演在采訪中所說的:“電視新聞只會報道災禍、暴力及苦難,然后劇情片又將其推成奇觀,好讓真實消失。”[3]
簡言之,導演所創造的電影文本本身便是“致盲”影像形成的過程。這是對于暴力的展示,更是對于媒介技術操縱手段的揭露。在《趣味游戲》中,哈內克更是將這一操控方式以一種更加暴力的方式展現出來。“殺人狂”成為了影像的象征,其用遙控器將整個故事進程倒放、改寫。這改變的不僅是劇中人物的命運,更是將觀眾的觀影位置暴露,以粗暴的方式讓觀眾瞬間清醒。
三、自我復制——數字時代的影像生產
1.停滯的批判——從影像狂熱到人工智能
1976年杰偉世(JVC)公司推出了第一臺家用攝像機,1995年索尼公司推出了第一部數碼攝像機DCR-VX1000、1999年DV機百花齊放,而到了2000年消費電子協會(Consumer Electronics Association)的加里·夏皮羅則直接把這一年稱作是“影像產品銷售的成功之年”[4]。可以看出,隨著影像產品的發展更迭,消費者對數字技術和家庭影院體驗的興趣越來越大。與此同時,電視產業也在蓬勃發展。1980年MTV電視臺開播,巴格斯(Buggles)樂隊的作品《錄像帶殺死廣播明星》(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被選為臺歌,這使得該作品成為世界上第一支電視MTV。從此,廣播音樂文化與電視音樂文化完成交接,聽眾被鎖在電視機前,享受畫面與聲音帶來的雙重刺激,“錄像帶殺死廣播歌星”一時也成為傳媒界的有趣現象。整個社會沉浸在影像的吸引力中,正如這首歌的歌詞所寫的那樣:“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圖像的出現正中死穴。”
這樣一股影像熱潮不可避免地引起理論界的關注。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期間,戰爭還未開始,鮑德里亞就已經在英國《衛報》上撰文,稱“海灣戰爭永遠不會發生”。而當戰爭結束,他仍然在法國《解放報》堅持“海灣戰爭從未發生”。這番論述引來軒然大波,諸多學者對他展開炮轟。然而鮑德里亞所要表達的僅僅是強調媒體在海灣戰爭當中的作用,在他看來,這場戰爭是一次視覺奇觀,真正的暴力和慘烈完全被“仿真”所覆蓋了;由于模擬的過程和邏輯,辨別真假、外表和現實變得越來越困難或不可能。哈內克贊同這種觀點,正如他在采訪中說的那樣,“通過媒體對世界的永久性篡改,導致我們只能用圖像來感知世界,一種危險的局面正在形成。”[1]
肇端于此,“冰川三部曲”及之后的《隱藏攝像機》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中產生。導演在這些作品中表達出這樣一種觀點,即“世界去真實化”是媒介技術發展的直接結果。哈內克精準地把握到了當時的影像或媒介是如何產生影響的,以及產生了何種影響。從表象上看,哈內克是在討論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但其根本是在呈現對技術的反思,一種對于媒介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焦慮。
然而,這種對于技術的反思似乎在《快樂結局》中發生了停滯。從1989年的《第七大陸》到2017年的《快樂結局》,電影中的媒介有著從錄像帶到流媒體、電視機到電腦、DV機到智能手機的轉變。進一步看影像產品的發展可以發現,媒介的數字化進程同時也伴隨著智能化的發展。智能手機問世后,傳統數字影像產品受到巨大沖擊。同時,智能手機也帶來數字影像的爆炸式增長。智能手機所代表的是整個智能移動端的發展,以蘋果智能產品為例,2010年蘋果手機4代iPhone4發布成為智能手機劃時代的標志;同年首款平板電腦ipad 發布,次年推出人工智能語音助手Siri,2014年蘋果手表iwatch初代發布。人們在被各種便攜式影像產品全面包圍的同時,智能化也在一步步逼近。一方面,智能技術的發展讓影像的“世界去真實化”更徹底。從美顏美圖技術到AI換臉技術,影像真實性徹底被摧毀,一種新的“真實”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智能化的推進意味著主體的數字化生存。從智能穿戴設備到智能家居生活,這樣一種基于算法的運行方式對于主體來說,實現了從外在世界的去真實化,到主體自身離散化的轉換。
由此來看,《快樂結局》似乎有種技術環境的錯位感。影片中的時間為2016年,對照數字產品的發展,人物所處的環境應該是一個被移動智能產品所包圍的世界。但導演依然安排了不少電視新聞和收音機戲份,依舊將傳統媒體作為人物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導演捕捉到了影像產品的發展更迭,但是沒有更好地挖掘影像產品背后的整個智能移動終端所帶來的巨大改變。一方面,在片中所呈現的媒介技術對于人物的影響與導演早前作品并無二致,該片中女孩可以說是女版的班尼;另一方面,在文本與觀眾之間,導演依舊以影像閉合圈的方式連接,但由于文本內的技術環境、人物與觀眾之間的不對稱,觀眾難以在其中映照自身。整個影片由于批判手法的停滯,而顯得力道不足。換句話說,與其說導演是在反思、批判,不如說是在向自我致敬。
2.“無”的范式——數字影像的復制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停滯?或許我們可以回到電影創作本身來做一個猜測。首先,這樣一種貌似停滯的反思實際是基于媒介技術與人的關系而得出的結論。而當我們回到電影本身,去觀照技術背景下的電影創作時就會發現,這種反思似乎在揭露數字時代的電影創作或影像創作的常用范式:復制。比如,爆款短視頻下智能化的“一鍵拍同款”,電影創作中的模版套用、翻拍再翻拍等。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一系列的復制行為在影像創作中顯得游刃有余,觀眾也樂在其中。
哈內克似乎在做相同的嘗試。暴力、戰爭、移民、情感疏離等話題反復出現在其作品中。在《快樂結局》中,導演則直接進行集合式的呈現,重復的不只是人物形象,更有文本的結構與框架。而這并非哈內克的首次嘗試,早在2007年他就做過更為極端的復制:自我復刻。
2007年美國版的《趣味游戲》,是哈內克的第一部英語作品,翻拍于導演自己在1997年奧地利拍攝的同名作品《趣味游戲》。不同于普遍意義上大家所熟知的翻拍,即保留基本的故事、人物、主題并在此之上進行二次創作的翻拍,哈內克的自我翻拍是逐鏡翻拍,除了演員與語言的更換,所有分鏡沒有做任何的修改。這是一個極端的翻拍,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復制。
在電影中,復制可以是對經典作品的翻拍、致敬、挪用。此時的復制代表著“有”,觀眾可以通過這樣一種復制行為,反復品味在某一經典橋段或作品中所觸發的深層次審美感受。而數字時代的復制只是復制行為本身。電影的創作轉換為一種基于可復制模版的、可形成表面視覺刺激的范式,意義消解在華麗的影像之中,影像由此體現為一種“無”的狀態,即我們看到了影像但我們什么也沒有看見。哈內克的“自我復制”正是對于這種“無”狀態的揭露。
概而論之,這便是哈內克電影中的致“盲”影像。“盲”代表的不僅僅是世界去真實化,同時也是當前大部分電影創作不再去追尋真理、不再尋求“有”的表征。哈內克的技術之思不僅體現在電影中,更體現在電影與觀眾的關系、電影之于電影本身中。
而今,“虛擬現實”的邊界正在進一步擴張。智能媒體庫、剪輯工具不斷優化。近日,米塔(Meta Platform Inc)公司甚至發布了 “文本生成視頻(Make-A-Video)”技術讓文字直接轉換成視頻,許多人認為影像的創作機制與呈現效果或將進入下一階段。在此基礎上,虛擬與現實、主體的認知將再次面臨新的挑戰。因而,重返哈內克的作品進行思考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