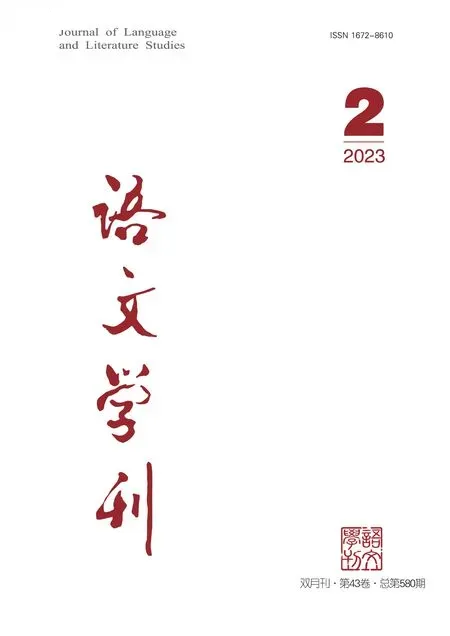《文心雕龍·通變》“五家如一”平議
○高宏洲
(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100705)
經過近百年的研究,有關《文心雕龍·通變》篇“通變”思想的來源、“通變”的內涵等,學界都有了較明確的認識①。時至今日,關于《通變》篇劉勰提到的漢賦“五家如一”的例子是褒義還是貶義,學界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因此,有必要在梳理過去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評衡哪種觀點更合理,從而進一步推進對這一問題的探討。
一、褒義派的主要觀點
褒義派認為,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篇提到的漢賦“五家如一”是“舉例以示方法”,代表人物是紀昀、黃侃、范文瀾、劉永濟、詹锳、周振甫、寇效信、王禮卿、張少康、劉文忠、楊明等。
褒義派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清代的紀昀,他在《通變》篇“五家如一”那一段眉批云:“此段言前代佳篇,雖巨手不能凌越,以見漢篇之當師,非教人以因襲。宜善會之。”[1]104明確指出劉勰所舉漢代“五家如一”的例子,目的是“見漢篇之當師”,“非教人以因襲”,應該善加領會。紀昀明顯是將劉勰所舉“五家如一”的例子視為褒義,開啟褒義說的闡釋路向。
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云:“彥和云:夸張聲貌,漢初已極,自茲厥后,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明古有善作,雖工變者不能越其范圍,知此,則通變之為復古,更無疑義矣。……彥和之言,非教人直錄古作,蓋謂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襲者,有不可因襲者,在人斟酌用之。”[2]104-106黃侃的觀點明顯來自紀昀,這可以從“明古有善作,雖工變者不能越其范圍”“非教人直錄古作”云云得到證明,是對紀昀觀點的復述。
在《文心雕龍注》中,范文瀾也強調劉勰舉此五例“非教人屋下架屋,模擬取笑也”[3]527,并引了黃侃的解釋。
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云:“至于后世文例相循者五家,正示人以通變之術,非教人模擬古人之文也。”[4]101
詹锳雖然肯定劉勰舉漢賦“五家如一”的例子,是為了說明描寫方式大多是繼承前人而又有所變化,但是認為,劉勰所舉的例子并沒有把創造的因素顯示出來,有抹殺創造性的嫌疑[5]68。
周振甫的觀點與詹锳相似,認為劉勰主張的新變與其所舉的例子存在矛盾:“在理論上,劉勰是主張新變的;在矯訛翻淺上,為了救弊,他可能認為與其崇尚新奇而陷于訛淺,還不如謹守規矩而不妨相襲,所以他要引五家如一的例。不過就通變說,崇尚新奇而陷于訛淺是錯誤的,謹守規矩而辭意相襲也不是通變。因此,劉勰的論通變是對的,用辭意相襲的例來說明通變,來矯訛翻淺,是不夠正確的。”[6]337-338詹锳和周振甫提出劉勰的觀點與其所舉實例存在矛盾的看法未必符合事實,但他們的觀點可能對貶義說的誕生發生過間接的啟發作用。
張長青和張會恩的《文心雕龍詮釋》不僅注意到“五家如一”有一脈相承的地方,即“因”和“通”的地方,而且發現他們都有自己夸張的特點,即“革”和“變”的地方。并且指出“五家如一”作為一種藝術手法,是可以推而廣之的,目的是推出“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的結論[7]161。這一判斷整體是比較準確的。
寇效信的《“通變”釋疑》是研究《通變》的一篇力作[8],認為劉勰舉出枚乘、司馬相如等“五家如一”的例子,是具體地說明“參伍因革”的方法,劉勰突出五家“循環相因”的一面是“意在糾正忽視‘相因’的‘訛而新’傾向”的特意行為。并強調研究者在理解這段話時,主要看到其“相因”“相循”的一面,而忽視了這些例子中“變”的一面,其實這些例子是有“變”的一面的,如寫池沼之大,有的是通望東海,水天一色,虹洞廣闊,有的則囊括日月的出入;有的用典,有的未用典;有的繁,有的簡。它們之間有錯綜變化,而不僅是“循環相因”。這與詹锳和周振甫的觀點明顯不同。
寇效信也是較早對牟世金提出的貶義說做出回應的學者。他從三個方面質疑了貶義說。第一,“循環相因”,“莫不相循”,是針對齊梁文壇不要繼承的“新變”論而發的,是強調名家名文也是“循環相因”的,其中并無貶意。第二,“軒翥出轍,終入籠內”,也不是貶抑和批判之詞。《宗經》篇說儒家經典乃“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這里的“百家騰躍,終入環內”并非對“百家”的批判和貶抑,而是說明五經之后寫文章的各家雖發揚了各自的創造性,飛騰跳躍,但終不能超越五經所體現的寫作法式。第三,如果將所舉五例看作對“近今疏古”的批評,就會與前面所引東漢桓譚采掇西漢劉向、揚雄的文章“常輒有得”的敘述相矛盾。而且從邏輯結構上認為“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從上面論述引出的結論,理應看作本段的結句,而不能看作下段的領句。寇先生的這三點質疑都是有根據的,貶義派的后續闡釋至今并未推翻其立論基礎。
臺灣學者張立齋的《文心雕龍注訂》云:“彥和舉此五例,以證‘循環相因’之理,藉知通變之理也。”[9]270-271王禮卿云:“此節遙承上之‘多略漢篇’,即舉漢文之通變以示例。……此亦舉為通變法例之一,其他通變之法尚多,至通神變貌,尤其高者。如宋人所謂奪胎換骨者即是。不舉彼諸例而舉此者,以茲之辭意顯明易見耳。”[10]575王先生指出“五家如一”之例與前面論述的“多略漢篇”在義脈上具有相承性,是有道理的;認為不舉“其他通變之法”,而舉此五例,是因為此五例“辭意顯明易見”也是頗具啟發性的。
張少康在肯定“五家如一”的各家有因有革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各家因革的程度和原因。他說:“這五家的描寫情況也不完全相同,例如馬融、揚雄的描寫,就有較多模擬的痕跡,這大約也是和這兩位是著名的經學家,受儒家‘述而不作’思想影響有關的。而從枚乘、司馬相如、張衡的描寫來看,雖有藝術上的繼承,卻又是頗有新穎的意境創造的。”[11]166盡管張先生認為馬融、揚雄的賦較多模擬痕跡,可能與他們受儒家“述而不作”的思想影響有關的結論還可以進一步探討,但是其指出枚乘、司馬相如、張衡的賦頗有新穎的意境創造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劉文忠也對牟世金的貶義說做出過回應,認為劉勰所舉“五家如一”的例子,用后代文論家和今天的詞語來說就是“化用”,而不能視作抄襲模擬;將其視作反面例證看是過分了一點,劉勰確實有“示人以變化之術”的味道,這是語言方面的“資于故實”。劉先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是,對《通變》篇的“通變之數”與“通變之術”作了區分。這是針對牟世金在《文心雕龍研究》中將二者等同而言的(詳下)。在劉先生看來,“通變之數”的“數”含有小技的意思,“通變之數”可以理解為“通變”的技巧。《通變》舉漢代五家為例,是“通變”中的小變,因循多,創新少,并非劉勰理想的“通變”;劉勰理想中的“通變”是大的“通變”,即“通變之術”,指“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等等。“資故實”指借鑒過去的作品,“酌新聲”指參考新的作品,兩者結合,才是“通變”的基本方法[12]155。劉先生指出“通變之數”與“通變之術”有區別是對的,但是將“通變之數”視為通變的小方法,“通變之術”視為通變的大方法,應該是不準確的。因為,“通變之數”是指通變的規律、準則,是形而上的概括;“通變之術”是具體的方法,是形而下的舉措;在內涵上,恰恰是“通變之數”高于“通變之術”,即理論高于實踐、指導實踐,而不是相反。而且,結合文意,劉勰指出的“通變之術”是最后一段“是以……”等,開頭的“酌新聲”等是對“通變”內涵的解釋,將其視為大的“通變之術”,容易搞混它們之間的關系。
楊明認為劉勰先舉出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馬融五家夸張聲貌的寫法為例,說他們雖然具體的文辭有變化,但關鍵的意象、寫法卻相因襲,這么說是想說明求新變不可能離開對前人的學習繼承[13]172。
以上是對主張劉勰所舉“五家如一”的例子含有褒義的代表性觀點的梳理。整體上看,這種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是主流。這種觀點的優點是照顧到了《通變》篇文章義脈的連貫性和劉勰立論的針對性,局限是除了寇效信和劉文忠對貶義派的觀點有所回應外,大多數學者未對《通變》篇中容易引起誤解的句子進行深入闡發,這就為貶義說留下了言說空間,而使褒義說頻遭質疑。因此,褒義說要獲得認可,必須針對性地解釋貶義派的疑問,使其觀點獲得進一步論證。
二、貶義派的主要觀點
貶義派認為劉勰所舉漢賦“五家如一”的例子是批評的反例,代表人物是牟世金、張燈、吳林伯、詹福瑞、涂光社、張國慶、周興陸、劉業超等。
牟世金應該是最早提出貶義說的學者。在1981年出版的《文心雕龍譯注》上冊的“引論”中,他說:“劉勰舉枚乘等人的五例,是用以說明‘競今疏古’的惡果,從而證明其‘文則’的正確,反證‘還宗經誥’的必要。所以,劉勰舉這五例,是對‘競今疏古’的批判,根本不存在是否示人以法的問題。在講這五例之前,劉勰已先予指出:‘夫夸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后,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這分明是對漢初以來‘夸張聲貌’的批判,所舉五例正是批判的對象;再聯系上文反對‘近附而遠疏’的用意,問題就更清楚了。明乎此,我們就可斷定后面所說‘諸如此類,莫不相循’,也是對‘五家如一’的批判。最后一段才是講‘通變之術’的,所以,‘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應該是最后一段的領句。劉永濟并此二段為一段,認為:‘末段即論變今法古之術。中分二節:初舉例以證變今之不能離法古,次論通變之術。’這個意見是對的。”[14]引論85 牟先生的意思是,劉勰舉漢賦五家的目的是,說明由于他們沒有“還宗經誥”,“競今疏古”,結果導致“循環相因”“五家如一”的模擬之弊,從而證明“還宗經誥”的必要。這一看法的問題是,將劉勰解釋古今文學演變為何“從質及訛,彌近彌澹”的原因中的“競今疏古”,與相隔一百多字的“夫夸張聲貌”直接關聯起來,跳過了中間對“多略漢篇”及引用桓譚“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的論述,這在行文邏輯上,無法解釋《通變》篇前后文義之間的連貫問題。而劉勰提出“近附遠疏”正是針對當時的文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的現象而言,其非否定“漢篇”確定無疑。因此,因劉勰對“近附遠疏”有批評,來證明劉勰對漢賦五家有批評,在邏輯上是不周延的。此外,牟先生引用劉永濟的觀點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也與劉的原意不符。劉永濟說得很清楚,“五家如一”至結尾,“中分二節:初舉例以證變今之不能離去法古,次論通變之術”。所謂的“舉例以證變今之不能離去法古”正是強調“五家如一”是“示人以通變之術”的正面例子。與牟先生主張的反面例子正好相反,牟先生似乎未覺察到兩者之間的差異。
在《文心雕龍研究》中,牟先生有進一步的論述。他說:“從本篇的邏輯上說,劉勰對文辭方面的‘循環相因’是否定的;從所用語意上看,對‘夸張聲貌’而又‘五家如一’是批判的;從‘通變’論的主旨看,是要求‘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而‘循環相因’者,不過是‘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更難允許‘不妨相襲’;劉勰何須出此下策而違背自己立論的主旨? 諸家之誤的長期存在,當非出于對紀、黃的盲目信賴,很可能與緊接在此段論述之后的兩句話有關:‘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劉永濟說:‘至舉后世文例相循者五家,正示人以通變之術,非教人模擬古人之文也。’‘通變之術’即‘通變之數’,長期來的誤解,就是這樣造成的。且不說劉勰這兩句本身是講交相因革才是‘通變之數’。關鍵在于這兩句是上文的總結,還是下文的領句。據以上所述,劉勰評漢人‘五家如一’既是否定的,就不可能以之為‘通變之數’。而對‘通變之數’的具體論述,正在下文。”[15]405牟先生是嚴謹的學者,但是這些理由還不能使人信服。首先,劉勰所說的“循環相因”,雖然突出的是“因”,但是并未否定“革”,這從其所舉五家用詞的差異可以看出。其次,從用語上說對“夸張聲貌”和“五家如一”是批判的,同樣也站不住腳。因為劉勰說“夸張聲貌,則漢初已極”,如果這句話有貶義,就否定了后世繼續因革的必要,因為漢初已經達到了頂點,就沒有必要再發展了。劉勰的原意應該是,漢初賦中的“夸張聲貌”已經達到了很高水準,因此需要向其學習。第三,牟先生認為“循環相因”與“通變”的主旨“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矛盾,似難成立。理由是將“循環相因”從具體的論述語境剝離出來,遮蔽了其針對當時忽視“相因”導致“訛而新”的創作傾向,而將其理解為模擬剽竊,從而造成與“通變”主旨“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的矛盾。實質上,劉勰強調“循環相因”正是為了溝通古今,在繼承古代的基礎上,奠定當下文學“日新其業”的根基,使其“通則不乏”。最后,牟先生將“通變之數”等同于“通變之術”也是欠妥的。如前所述,“通變之數”強調的是“通變”的規律,“通變之術”強調的是“通變”的方法,規律是抽象的,方法是具體的,規律對方法有指導作用,方法是對規律的實踐,兩者緊密相關但并不等同。牟先生將“通變之術”的方法等同于“通變之數”的規律,從而實現“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屬于下文的領句的論證,就更難站得住腳。當然,貶義說作為一種觀點是能夠自圓其說的,牟先生力圖解決困擾龍學界的疑難的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和令人欽佩的。
在牟世金之后,對貶義說做出過深入闡釋的應該是張國慶和周興陸。張國慶寫過針對“五家如一”爭論的專題論文——《關于<文心雕龍·通變>對漢賦的一段議論》。該文的貢獻在于,認識到貶義說將“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歸入最后一段,會使“夫夸張聲貌”一段文字失去照應:“劉勰將‘五家如一’的反例擺了出來,卻對之一言不發,不作任何評論,掉頭便去談論‘通變之數’去了,會導致‘夫夸張聲貌’一段文字、‘五家如一’的反例孤懸文中,顯得十分的突兀不當。”[16]105這個分析是允當的,有助于思考貶義說的局限。該文的問題在于,將引起“諸家之誤”的原因歸結為劉勰本人的文字表達存在不足。張文分析道,劉勰本來就是要舉反面的例子,并且要用這些例子從反面推出“通變”的正面結論,但是當他用反例來推出正面結論的時候,彎子轉得急了一點,在語句上并沒有完全處理得當。具體說,就是在“五家如一”一段的末尾“諸如此類,莫不相循”與結論“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之間,缺少一句承上而來具有否定性總結意味的話。作者認為如果加上類似“故通變術疏,百家似一”這樣的話,前句與后句之間就能夠順利地承接轉折,就可以通過前面的反面例子順利地推出后面的正面結論了。張先生的思考不無啟發,但是所得結論卻難以置信,因為他所提議增加的文字毫無版本依據,完全是在把“五家如一”視為反面例子無法自圓其說的基礎上推演出來的。
周興陸對貶義說從四個方面進行過論證[17]165-167。第一,從用語上,認為這段話中的“終入籠內”就是“局步”而不能“奮飛”的意思,有否定意思。第二,從劉勰提出五家的先后順序(枚乘、司馬相如、馬融、揚雄、張衡)與他們生存的時間順序(枚乘、司馬相如、揚雄、馬融、張衡)不一致來說,劉勰調整順序的原因是要說明枚乘為首創,司馬相如、馬融、揚雄、張衡都是“影附”“因循”枚乘。然后結合劉勰對這五個人的賦的評價,認為對枚乘《七發》“信獨拔而偉麗矣”(《雜文》)的評價最高;對司馬相如的《上林賦》“繁類以成艷”(《詮賦》),馬融的《廣成賦》“弄文而失其質”(《頌贊》),已有貶抑;對揚雄的《羽獵賦》“鞭宓妃以馕屈原……虛用濫形,不其疏乎”(《夸飾》),張衡的《西京》“海若游于玄渚”等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夸飾》)的評價越來越低。第三,聯系《辨騷》篇,認為劉勰是肯定“取镕《經》旨,亦自鑄偉詞”的“通變”,而“循環相因”正好是“自鑄偉詞”的反面。況且,劉勰在《辨騷》篇說“驅辭力”“窮文致”的正確方法是“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特別提到“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如果劉勰肯定司馬相如、馬融、揚雄、張衡等的“循環相因”,不是在稱贊“乞靈于長卿”就是“通變”的正法嗎? 第四,聯系《通變》篇的上下文,認為前面一段用“青生于藍,絳生于蒨”的比喻說明“雖逾本色,不能復化”的道理,司馬相如、馬融、揚雄、張衡四人在文辭上因循枚乘,就是“雖逾本色,不能復化”。劉勰說他們“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意思也是他們是“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盡管周先生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證,但其論證過程仍有值得商榷之處。關于第一點,對“終入籠內”的理解,周先生與寇效信恰好相反。筆者認為寇效信的理解更合理,因為這可以從《宗經》篇說儒家經典乃“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獲得佐證,也可以與首句“夫夸張聲貌,漢初已極”相呼應。關于第二點,周先生發現劉勰介紹五人的先后順序與他們進行文學創作的先后順序不一致,是建立在對文本的細讀和對漢代文學演變的熟稔基礎之上的,但還不能據此得出“五家如一”含有貶義的結論。因為劉勰用的是“循環相因”,就不可能是枚乘為首創,其他四人因襲他。在筆者看來,劉勰所舉五例的順序與其歷史先后不一致,正可以說明劉勰在此只是隨意舉例以說明“相因”的重要性。如果是批評模擬因襲,一定會按照歷史的先后順序排列,因為只有后面的才會抄襲前面的,不可能是前面的抄襲后面的。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太可能是劉勰因粗心而誤,因為《才略》篇是揚雄在前、馬融在后。周先生通過梳理《文心雕龍》全書對五家的批評來論證劉勰對他們有貶義,這個思路是正確的,但是對部分批評的闡釋并不是無可挑剔。這涉及如何準確理解劉勰對這五家的評價問題。在我看來,劉勰對五家的整體評價是比較高的。《詮賦》云:“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凡此十家,并辭賦之英杰也。”[3]135《通變》提到的枚乘、司馬相如、張衡、揚雄都屬“辭賦之英杰”的“十家”之中。而“辭賦之英杰”是非常高的評價,僅次于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辨騷》對《楚辭》的整體評價是“體慢于三代,而風雜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劉勰在《才略》篇也比較全面地評價過這五人,說枚乘《七發》“膏潤于筆,氣形于言”,毫無疑問是肯定。雖然認可揚雄批評司馬相如“文麗用寡”有一定的道理,但這是針對其缺點而言的,前面的“致名辭宗”是很高的評價,與《詮賦》的“辭賦之英杰”相一致。評價揚雄“子云屬意,辭義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鉆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顯然屬于褒義。說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范,華實相扶”,也是肯定得多。說“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同樣是肯定得多。相反,周先生所列舉的批評意見大多是局部的。比如,說司馬相如的《上林賦》“繁類以成艷”(《詮賦》),馬融的《廣成賦》“弄文而失其質”(《頌贊》),是從文辭的繁艷而言的;說揚雄的《羽獵賦》“鞭宓妃以馕屈原……虛用濫形,不其疏乎”,衡的《西京》“海若游于玄渚”等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夸飾》),是針對夸飾的具體句子而言的。周先生似乎忽視了劉勰在不同的語境中論述角度存在差異的問題。而在筆者看來,劉勰《通變》只選取“夸張聲貌”角度進行論述,正是為了從“文辭氣力”的角度說明語言方面的“通變則久”的道理。關于第三點,盡管劉勰在《辨騷》末談到如何對待《楚辭》云:“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3]48好像在貶低司馬相如和王褒,其實這是在屈原與司馬相如和王褒的對比中而言的,并不意味著對司馬相如和王褒的整體否定。最后一點,周先生認識到將“青生于藍,絳生于蒨”的比喻,與所舉五例的上下文聯系起來考慮的重要性,卻忽視了上一段中“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而近附而遠疏矣”及引用桓譚“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而這些話正是強調學習“漢篇”的重要意義。
除此之外,張燈、吳林伯、詹福瑞、涂光社、劉業超等都認為劉勰所舉“五家如一”的例子是反面例子,繼承的多,變革的少,而真正的“通變之道”應該是“因革結合”、有因襲有創造②。整體而言,從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主持貶義說的學者越來越多,甚至有超過褒義說的趨勢。但是他們的解釋至今還不能使人信服,下面將重申褒義說的合理性,以就教于貶義說的方家。
三、褒義說更符合劉勰原意
相比較而言,筆者認為褒義說更合理,理由有四。
第一,褒義說照顧到了《通變》篇語義的前后貫通。《通變》先是通過與“有常之體”的“名理相因”的對比,提出“通變”的對象是“無方之數”的“文辭氣力”③。劉勰這樣說是因為,劉勰所處的時代是各種文體“文成法立”的階段,大多數文體剛剛在成功范作的基礎上確定了基本寫作規范,還沒有發展到后世所謂的某一種文體因相沿日久而產生弊病需要改革的狀態,這從《定勢》“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獲得證明。而作家的創造性主要體現在遵循文體規范基礎上的“文辭氣力”。從理論上說,一種文體的基本規范一旦確定,由于人類社會的不斷變化,每個時代的不同作家所寫的內容必然不同,只要善于“通變”,文學創作就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而之所以出現衰敗,“非文理之數盡”,而是“通變之術疏耳”。然后通過梳理歷代文學演變的過程,揭示后世文學出現“從質及訛,彌近彌澹”的原因在于“近今疏古,風末氣衰”。這一問題在當時的突出表現是“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從《文心雕龍》全篇來看,“近附遠疏”的“遠疏”當包括“漢篇”與之前的“經典”和楚辭,但是由于“文之樞紐”部分討論了如何對待經典和楚辭的問題,所以這里重點是討論如何對待“漢篇”。
對于劉勰批評“多略漢篇”的原因何在,學界有不同的解釋。吳林伯分析說這里提到的“師范漢篇”與上面提到的“楚漢侈而艷”之間并不矛盾:“蓋劉勰之于漢作,實非全盤否定。乃如相如《子虛賦》、子云《甘泉賦》,雖以‘侈’著,亦取其‘體國經野’的‘光大’之‘義’(《詮賦》),譽為‘辭賦之英杰’(《詮賦》);他若西漢賈山《至言》、賈誼《陳政事疏》、劉向《極諫用外戚封事》、揚雄《法言》等,皆本書《體性》所謂‘熔式經典,方軌儒門’的‘宗經’之作,故欲后世取則。”[18]347周興陸將劉勰對“多略漢篇”的批評解讀為劉勰提倡師范“漢篇”,是通過師范“漢篇”來“昭體”,即掌握各種文體的寫作規范,因為許多文體的體制規范、典型作家、典范作品都是在漢代出現的[17]163。姚愛斌則除了肯定“漢篇”在確定文體“有常之體”的地位外,另一原因是盡管劉勰認為楚騷漢賦開啟了后世繁縟、艷麗的文風,但是漢代文學畢竟去圣未遠,遺澤多有,相對近代文學的“淺而綺”“訛而新”,其麗未淫,其采未濫,整體上還是值得取法的[19]。從“多略漢篇”的上下文語境來看,將其歸結為通過“漢篇”來“昭體”缺乏根據,因為“通變”的主體是討論“文辭氣力”,盡管“昭體”與否是影響“文辭氣力”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這是一個比較隱性的因素,劉勰在本文中并無文字上的暗示。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吳林伯和姚愛斌指出的“漢篇”的整體成就,因去圣未遠而有值得效法之處。從“多略漢篇”也可以看出,劉勰并非徹底否定學習“漢篇”的價值,而是針對魏晉的“顧慕漢風”“瞻望魏采”缺乏“宗經”的規范引導,導致走向魏晉“綺而淺”宋初“訛而新”的弊病。這里涉及一個“師范漢篇”與“還宗經誥”有無矛盾的問題。陳拱的《文心雕龍本義》云:“按此即就當時創作上風尚之卑劣而特提之耳。蓋當時風尚,競今、疏古,止宋集而求,不惟不讀上古,即漢篇亦少研矣。故進之以漢篇。非謂漢篇即足師范也。此征之下文‘還宗經誥’之言,其意固甚明顯也。”[20]723那么,“師范漢篇”和“還宗經誥”有無矛盾呢? 不矛盾。“矯訛返淺,還宗經誥”是對“鮮克宗經”導致的文弊的克服,而非對過去文學新變的徹底否定。師范“漢篇”是在“宗經”的基礎上學習“漢篇”,而且這種“宗經”并非復古不變,而是通過“斟酌質文”“隱括雅俗”實現古與今的貫通。只有這樣理解,才能將“多略漢篇”與桓譚之論及之后所舉的漢代“五家如一”的例子貫通起來。如果將“五家如一”視為反例,“多略漢篇”就沒有了著落,整個《通變》前后照應不起來。劉勰舉“五家如一”的例子正是為了在此基礎上得出“通變”的規律:“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文章最后提出的“通變之術”是結合整個創作而言的。其中的“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主要指通過博覽掌握各體文學的基本寫作規范,而各體文學的基本寫作規范在上篇的“論文敘筆”部分有詳細的論述。這是“通變”的前提和基礎。然后才能在此前提和基礎上發揮創作主體的主觀能力:“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憑情以會通”強調的是會通古今,《物色》云“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馀者,曉會通也”,《體性》云“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都是強調作者的會通能力。“負氣以適變”強調的是根據自己的才氣確定“文辭氣力”的變化,如《麗辭》云“至于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章句》篇云“隨變適會,莫見定準”,都是強調作者能夠根據文情變化而變化文辭的能力。如果缺乏“會通”和“適變”能力,只是局限在“偏解”“一致”的促狹范圍里,必然創作不出偉大的作品。“庭間之回驟”強調的正是不重視繼承而導致根基不深厚的創作樣態,而“萬里之逸步”則是強調奠基于繼承前人優秀作品的基礎之上的創作才能行之久遠。如果把“參伍因革,通變之數”置于本段之首,不僅會顯得突兀,而且會削弱強調繼承基礎上的新變的觀念。貶義說的最大問題,就是割裂劉勰所舉“五家如一”之例與前后段落之間的聯系。
第二,從用詞上說,劉勰對漢代“夸張聲貌”的整體評價是:“夫夸張聲貌,則漢初以極。自茲厥后,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其中的“極”和“終入籠內”都是褒義,否則就無法理解整個句子。如果漢初“夸張聲貌”已經達到頂點,那么之后只能討論漢初的理想狀態,而不會舉漢代“五家如一”的例子來說明問題。如寇效信先生所言,“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和《宗經》的“百家騰躍,終入環內”一樣,盡管都注意到之后的發展對經典和漢賦有超越,但是整體上還是在經典和漢賦的籠罩之內,這正是強調經典和漢賦的巨大影響力。盡管周興陸先生也意識到這兩處含有褒義的事實,但是他結合《夸飾》篇將“軒翥出轍”與“終入籠內”對立起來,將“軒翥出轍”理解為“奮飛”的意思,將“終入籠內”理解為“局步”的意思,從而得出劉勰有否定的意思。筆者認為,這樣的理解值得商榷。
第三,從“贊”言的“參古定法”上說,“五家如一”的“循環相因”應該就是所“參”的“古”。“贊者,明也”(《頌贊》),《文心雕龍》的“贊”往往對全文的主旨進行概括說明,那么,《通變》贊中的“望今制奇,參古定法”的“參古”指什么呢? 詹福瑞將“參古定法”理解為:“即《辨騷》篇所說的‘憑軾以倚《雅》《頌》’,《通變》篇說的‘矩式周人’,也就是以經書為文變之法。”[21]199強調的是楚辭學習經典的成功經驗。這樣理解似乎還不夠貼切,因為“憑軾以倚《雅》《頌》”是《辨騷》篇提出的對待楚辭的態度,以此來概括《通變》篇未必恰當;“矩式周人”雖然是《通變》提出的,但文中并未展開具體論述,“矯訛翻淺,還宗經誥”只是一句方向性和原則性的話。文中前后呼應的是對當時文壇“多略漢篇”的批評、漢代桓譚“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的經驗之談、漢賦“五家如一”的例子,從文意上看前兩者又是為后者的舉例做鋪墊的。因此,這里的“參古”應該指文中所舉漢賦“五家如一”“循環相因”的例子,“定法”就是從中引申出來的“參伍因革”的“通變”規律。大多數譯注將“參古定法”泛泛地翻譯為“參考古代的杰作來確定寫作的法則”,停留于字面意思,沒有將其與《通變》正文的論述緊密結合起來。如果將“五家如一”視為反面的批評,同樣否定了“望今制奇,參古定法”與《通變》正文文字上的照應關系,應該是不妥當的。
第四,從文學史演進的角度上說,劉勰要引申出的通變規律“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如寇效信所言,是特意針對當時追求“訛而新”的文壇風氣而言的,目的是強調“相因”“相循”的繼承對于創作的重要意義。劉勰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的時代,是一個“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穿鑿取新”(《定勢》)的時代。這樣的創作態勢必然走向“唯新是求”、追新逐奇的狹窄道路。劉勰指出的拯救辦法,就是繼承五經、《楚辭》、漢賦等文學傳統。由于前兩者在《宗經》《辨騷》篇論述過了,所以這里重點論述繼承漢賦優秀傳統的重要意義。關于舉例是否恰當的問題,褒義派和貶義派都提出過質疑。筆者認為,這主要與劉勰“示人以法”的目的有關。為了顯豁地傳達“相循”“因革”的范例,劉勰選擇了漢賦中比較明顯的“五家如一”的例子予以說明。誠如王禮卿所言,劉勰完全可以舉更具有“化境”的例子,但是沒有舉,正是為了顯明主旨。至于“相循”過度,導致模擬剽竊,“相循”是否有個“復”和“變”的度的把握問題,這還不是劉勰考慮的重點。這個問題唐宋以后雖然不斷有人論及,如皎然的“復忌太過”(《詩式》卷五)等,但是直到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詩學導致大量的模擬剽竊才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時,如何在復古與新變之間取得平衡才變成許多論者關注的重心。如顧炎武強調的“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日知錄》“詩體代降”),葉燮的“變能啟盛”(《原詩·內篇上》),才更具理論自覺。現代一些學者之所以認為“五家如一”模擬太甚、創造不足,一方面是警醒于明代前后七子復古有余而新變不足的模擬之弊,另一方面則與近代以來廣受洗禮的線性進化論思維密不可分。尤其是后者,對現當代學者影響至巨,使他們更重視文學創作的新變,而忽視復古對于文學創作的奠基意義。這種理論視域的古今差異,是貶義派包括部分褒義派學者不能理解劉勰從漢賦“五家如一”的“循環相因”中推演出“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們思考劉勰舉例的“五家如一”觀點時一定要顧及劉勰立說的歷史語境,以了解他為文的良苦用心和立言的針對性。而且從劉勰所舉句子的用詞看,也是有因有變,不存在完全因襲的問題。
如前所述,《通變》篇所舉五例是褒義還是貶義,是困擾準確把握該篇主旨的難點,盡管前人時賢多有努力,但是至今仍疑竇重重。筆者對這個問題也曾有過反復,但是終究覺得褒義說更合理。于是,在這里提出自己的粗淺看法,希望引起龍學專家的進一步探討。其中所言,未敢必是,懇請龍學專家教正。
【注 釋】
①可參看寇效信《“通變”釋疑》(《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 年 第4 期)、牟 世 金《文律運周 日新 其業——<文心雕龍·通變>新探》(《文史哲》1989年第3期)等論文。
②參看張燈:《文心雕龍辨疑》,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頁;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頁;詹福瑞:《中古文學理論范疇》,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93頁;涂光社:《<文心雕龍>論模擬》,《貴州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劉業超:《文心雕龍通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8-1469頁。
③寇效信的《“通變”釋疑》(《陜西師大學報》1985 年第4期)、牟世金的《文律運周 日新其業——<文心雕龍·通變>新探》(《文史哲》1989年第3期)已經指出了這一點。新近發表的張麗華的《<文心雕龍·通變>文術論發微》(《語文學刊》2020年第4 期)重申了這一觀點。不過牟先生認為“可與言通變矣”之前是講九代詠歌中楚漢以后未能“名理相因”,之后講漢人之作的“文辭氣力”方面未能“通變則久”,將《通變》前后截然分開,與本文的觀點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