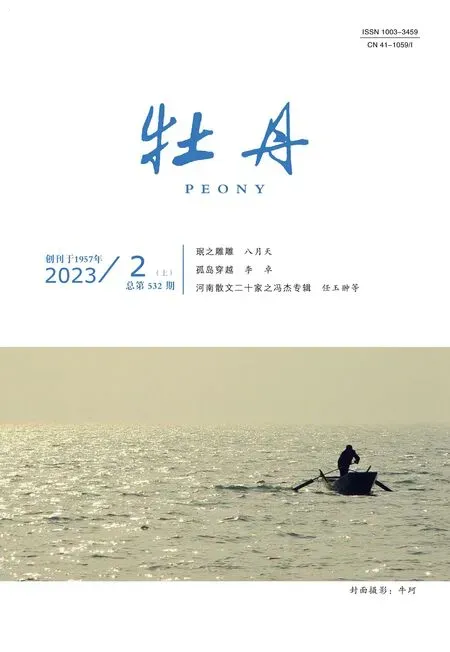水峪
李青松
在這里,水是如此的豐沛,甚至連名字都溢出了水。
京東金海湖鎮境內,有一個詩意淋漓的村莊——水峪。何謂峪?兩山夾一谷,謂之峪。水峪,即為有水流淌的山谷。我隨施海來到水峪一看,果然如此。然而,水能造福,也能泛濫成災。物無美惡,多了即是問題。
仰觀之,村莊往上是一道水壩,攔住了整日嘩嘩流淌的水流,生生憋出了一座水庫。水壩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修筑的。當時全村男女老少都動員起來了,家家出義務工,用小推車推土,用扁擔擔石頭,壯勞力喊著號子打夯,小學生放學后也來參加義務勞動。工地上紅旗招展,鼓聲喧囂,人人干勁兒沖天。水峪人用了整整兩年時間,終于把水壩修筑成了。
水壩的功能主要是蓄水防洪,另外的功能就是“叫水”(用水泵從水庫提水上山,澆灌山上的旱田)解決山上幾百畝旱田用水問題。大壩有三層樓那么高,前些年,為了泄洪方便,生生削掉了兩米。家住水壩附近的村民擔心萬一爆發了更大的山洪怎么辦?是攔呢?是泄呢?
村主任假裝沒聽見,眼睛看往別處。
水庫上游還有兩個水塘,呈狹長形狀,似是相對獨立的,又似隱隱約約相通的。一曰大水塘,水面闊達;一曰小水塘,水清如碧。從高處看,感覺就像大水塘用手揪著小水塘的耳朵,生怕小水塘溜號,瞬間隱于山林中。盡管性野的小水塘拼命想掙脫那只手,可是力不能勝,只得嘟嘟囔囔地跟隨服從了。
兩口塘里魚蝦蟹甚多。晌午陽光飽滿時,喧囂歡騰,不時有魚躍出水面。大魚有六尺長,是黑魚,足有七八十斤,早年被人捕獲過。人摳著魚頭鰓部背在身上,魚尾拖在地上行走,地面被劃出一道濕漉漉的印痕。
施海是我的朋友。他額頭挺闊,目光炯炯。飛燕眉,兩端翹,絡腮須,硬朗粗糲,面相陽剛。他屬于那種話多,但還不能定性話癆的人。他有話從不憋在心里,總是要說出來,痛痛快快表達自己的看法。施海出生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他開玩笑說,每年的這一天,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要放假慶祝他的生日,也太隆重了吧。
水峪村是施海的出生地。水峪村共有三百四十二戶人家,一千一百一十三口人。多為平房,也有幾戶是樓房。村委會在村中央,是二進院,門口掛著多塊牌子。
水峪村現任村主任叫李富東,一九八二年一月九日出生,畢業于北京機械學校,專業是機械制造。畢業后沒造出一件機械,卻回到了村里,立志要改變鄉村。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李富東高票當選村主任,上任后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造地,準確地說是造可利用的耕地。李富東認為,制約水峪村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可利用耕地太少。水峪,除了水,就是荒山荒地荒坡,人均可利用耕地不到四分。李富東從區里爭取到“農發項目”,以小流域為單元,山水林田湖草統籌治理,挖掘機開上山,該打壩的地方打壩,該挖渠的地方挖渠,該整地的地方整地,用了四個月時間,硬生生造出可利用耕地兩千畝,水峪村的可利用空間闊達了許多。第二件事是進行“改水革命”,家家戶戶的“上水”(生活用水)“下水”(生活污水、廢水、殘水)各走各的管道。廁所改成了“三格式化糞池”(三層網格過濾),對沉淀物進行過濾凈化,在村西頭建了一個污水處理池,統一處理污水,使其達到中水標準,實現再利用。村民用水既干凈又衛生了,過去又臟又亂的狀況被徹底改變了。第三件事是發展特色種植業。種核桃種板栗種大棗種辣椒。光是辣椒就種了一百畝,種的品種叫“小米辣”,吃過的人說,能把人的魂兒辣出來,辣的人恨不得從地球上跳下去。好嘛!一個“辣”字,每年給水峪村帶來四十萬元的收益,種辣椒的村民個個眉開眼笑。
這三件大事辦完后,村民給李富東豎起大拇指!背后悄悄議論說——選大富(李富東小名叫大富)當村主任選對了,這小伙子能干事,有作為!不賴!
在村委會,我見到李富東時,他說:“新農村建設,不能是喊喊口號,刷刷墻,寫寫標語,換幾片新瓦。必須發展產業,壯大集體經濟,積累公共資金,集中力量辦一些大事。”他說,“不搞產業,一切都是空談。”
在美化村容村貌方面,李富東也有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把村里那條狹長的水溝種上蓮荷。一來蓮藕能凈化水質,二來荷花盛開時可以起到美化的效果。不過,他又有些擔心。擔心什么呢?擔心蓮荷長起來后,引來青蛙。夏季,一片蛙鳴,吵得老人們睡不著覺怎么辦呢?他說:“就這件事要開一次村民代表大會,村民投票表決,到底種不種蓮荷。”我聞之笑了——這個村主任還挺民主嘛!
村委會外側臨街的三間房是村衛生所,藥架上擺著各種各樣的藥。有中藥,有西藥,也有一些康復器材。村委會門口對面是一家超市,名字挺大,其實就是一家日用品雜貨店。賣油鹽醬醋,賣鉛筆田字格橡皮擦,賣毛巾手紙面巾紙,也賣饅頭花卷豆包等食品。
村街轉角處是一輛三輪車上擺著的菜攤,豆角黃瓜西紅柿白蘿卜圓白菜等一應俱全。車上綁著一個喇叭,用略帶方言的口音,一遍遍地播報著菜價。攤主呢?唉,攤主躺在車底下一塊草席上睡覺呢。而三輪車旁邊,兩個抱孩子的婦女,正面對面東一句西一句地聊天。不遠處矮墻下,一只黃狗端坐著伸出紅紅的舌頭,一邊哈哧哈哧哈哧不斷地縮動,一邊疑惑地看著那兩個婦女聊天。
村街不寬,但很干凈。施海說,峪口東端與西端相距五百米左右,原本各有一塊狀如龜頭的巨石對望,栩栩如生。某年,修高速路取石料,兩只完整的龜頭被爆破炸成碎石,鋪在高速路路面上了。可不久,聽說高速路通車后,那段路面上總是出事故。爆破手所乘通勤車通過那里時,莫名其妙地發生了爆胎,爆破手被炸得血肉模糊,再也沒有睜開眼睛。
水峪村不算大,但山美水美生態美。一提起水峪村,施海的眼里就放著光。水峪村大壩底端有一眼山泉,曰之水泉。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泉水歡涌,四季不歇。施海說,此泉底下的水脈通著金海湖呢。湖水滿盈時,泉水沖勁兒就特別猛。小時候,施海常去擔水。泉水映著他的身影,閃著亮亮的光。施海父親干農活回來,便舀一瓢泉水,一仰脖兒,喝下去,然后抿一下嘴角的水珠,心滿意足。施海在旁邊看著,心里舒坦極了。
施海說,他小時候最怕的人是看青的知青夏宗鐵,此人很少說話,是個狠人。一提他的名字,小伙伴們腿就發抖。那時,他和小伙伴也偷梨,也偷玉米棒子。可是,夏宗鐵從不追趕他們,他總是在他們回家必經的路口埋伏著,出其不意地跳出來,抓獲他們。抓獲后,讓他們把腰帶解下來,把鞋脫下來,然后用腰帶把鞋捆上,讓他們各自背著,他在后面押解著,把他們送到生產隊。“我的媽呀,赤腳走在山路上,灌木和草尖扎得腳丫子實在是痛啊!”——施海回憶起當年,仍然叫苦不迭。
施海家人口多,沒有存糧,總是吃了上頓接不上下頓。母親唉聲嘆氣,為一家人沒有吃的發愁。一天夜里,門外哐當一聲響,母親拿手電筒出去一照,一個黑影在墻角閃了一下,就在夜幕中消失了。母親回頭發現,一個鼓鼓囊囊的麻袋倚在門后。打開一看,里面裝的全是青玉米棒子。
母親聲音低低地問了一句:“是夏宗鐵嗎?”
無人應答。夜,寂靜無聲。
早年,水峪村有一位捕蛇的奇人,就連夏宗鐵對他也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的真名叫什么沒有人知道,村里人只知道他叫老槐。槐者,鬼入木者謂之槐。人說,有一種神秘的東西附于老槐身體上了——不然,蛇為什么怕老槐呢?老槐在山上行走,蛇會遠遠躲開他。如果躲避不及,蛇會立刻僵住,待老槐走遠,蛇才能活動。
有一天,老槐在田里鋤草,不小心將一只青蛇蛇尾誤當野草鋤掉了。青蛇哀鳴不已,立時遠處傳來隆隆巨響,聲如滾雷,越來越近。老槐定睛一看,有千萬條青蛇蜂擁而來,層層包圍了老槐。老槐手持鋤頭大喝一聲,所有的蛇便立時僵住了,隆隆的巨響戛然而止。老槐不慌不忙,將鋤掉的那截蛇尾拾起,對準斷尾的青蛇就那么一捋,說了一聲——走呀!青蛇就蜿蜒而行了。
老槐低頭掀起田里一塊石頭,石頭下面是一個洞口,青蛇消失在了那塊青石下面。頃刻間,所有的青蛇蠕動起來,魚貫入洞。不消半個時辰,那些青蛇無影無蹤。
老槐喜歡喝酒。家里酒壇長年泡著蛇酒。
某日,老槐打開酒壇,用提具提酒,不想,酒壇里的蛇卻突地竄出來,咬住了老槐的手腕。——啊呀!老槐驚叫一聲,手腕上鮮血淋漓。幸虧搶救及時,才保住了性命。傷口痊愈后,老槐痛下決心,再也不捕蛇了。老槐成了村里護林員,整天在山上轉來轉去,那些樹和草都熟悉他的面孔了。
一九七〇年,一個叫李喜琛的城里人,成了水峪村的上門女婿。他嘴巴能講,干農活實在不行。那時,生產隊一個男勞力一天能掙八分,女勞力最少也能掙六分,可李喜琛一天只能掙四分半,丟人啊,連女人都不如。生產隊長說,算啦,你省點力氣吧,干脆去開手扶拖拉機吧,李喜琛就成了手扶拖拉機手。水峪村出產“大白”(石頭風化后形成的土,俗稱白灰土,是一種保溫材料),三河那邊一家收購站收購這種東西,每噸十八元。李喜琛每天開手扶拖拉機往三河送“大白”,可是三河這邊一轉手賣給北京城里一噸就是三百元。李喜琛了解到情況后,心情很是不爽。他不再往三河送“大白”了。
幾天后,李喜琛的身影和他開的手扶拖拉機出現在北京化工二廠。李喜琛嘴巴就是會說,把水峪村的“大白”描繪得溫暖生花。于是,此廠每年收購水峪村“大白”三百噸,一噸三百元。三百噸是多少錢呢,算算就知道了。好家伙,水峪村靠賣“大白”一下就闊了。生產隊買了一臺“德律風根”黑白電視,裝在一個木箱子里,白天一把大鎖鎖著。鑰匙在老兵屈兆增(曾是志愿軍某部機槍連連長)腰帶上掛著,一走路嘩嘩直響。只有到了晚上,屈兆增才開鎖把木箱門打開,電視播放兩個小時,全村老老少少都來收看。老輩村民心里都清楚,沒有上門女婿李喜琛,要想看上電視恐怕還要晚一些年呢。
歷史上,水峪村是有名的大棗之鄉。傳統品種有尜尜棗、葫蘆棗、老虎眼子棗。七十年代,村里引種泡桐和洋槐不慎,結果使棗樹染上了瘋棗病,樹齡百余年以上的棗樹主干從底部往樹梢上潰爛,一片一片的老齡棗樹不到半年時間相繼死掉了。現場情形慘不忍睹。
若干年前,村委會決定,用組培和嫁接技術將野生酸棗馴化,培育大棗新品種——盤棗,重新發展大棗產業。畢竟,大棗的基因還在,根脈還在。盤棗,頗有卡通意味,形狀扁圓,個頭偏大,又甜又脆。如今,水峪的新一代棗樹已經進入盛果期,連年豐產,顆顆飽滿。深秋,打棗的季節一到,棗園里激蕩著歡聲笑語。啪啪啪!啪啪啪!有棗沒棗打幾桿子,打過的棗樹就壯實了。農家院里,柳條簸箕里曬的是大棗,柳條笸籮里曬的是大棗。大棗,就像水峪人的日子,越曬越紅呢。
除了大棗,水峪豆腐也是遠近聞名。村里有個叫紀大華的村民開了一家豆腐坊取名“大華豆腐坊”。她做的豆腐,每天供不應求。村民喜歡吃不說,城里一些酒店餐館,也常年訂購水峪豆腐,每天凌晨,車在豆腐坊門口等著豆腐出屜。水峪豆腐好取決于三個因素,一則豆子是當地梯田產的黃豆,不上化肥不打農藥;二則點的是鹵水,時間和用量掌握得好;三則用的水是水泉的泉水,清冽甘甜。
水峪村北面有一座名叫云祥觀的古廟,早年間,這里是一所小學校所在地。施海的小學就是在這里讀的。古廟院落里有四株古樹,樹齡已有五百多年了。水峪村是先有古樹后有古廟,還是先有古廟后有古樹呢?施海也不得而知。古廟分前院和后院。前院的兩株古樹是國槐,后院的兩株,一為油松,一為側柏。四株古樹各具形態——斜松直柏并肩槐。
施海說,他上學時常爬古樹玩耍,爬得最多的是那株油松,因為它是斜著生長的,爬起來相對容易。歘歘歘,三下兩下就猴子一般爬上去了。他在作文里曾寫過那四株古樹的故事,記得當時的語文老師叫張忠志,把那篇作文當成范文在課堂上給全班同學朗讀,很是讓他風光了一次。
某年,北京市園林綠化系統舉辦古樹知識答題比賽,作為考官的施海,在海量答卷中,發現了張忠志的名字,大筆一揮給了滿分的成績,并獎勵張忠志一條毛毯。
當然了,試卷答得確實好,找不出半點瑕疵。
在施海眼里,每一株古樹都是活物,它們理應得到尊重,并應得到善待。古樹,有著超乎尋常的生命本能和昂揚向上的精神。古樹,遠比我們想象的神奇更神奇。
然而,凡上了歲數的生命,必易染病,必易致殘,必易遭蟲蛀,必有抗性和免疫力下降的問題。古樹亦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四株古樹不同程度地呈現出了弱勢狀態。枯枝漸多,蟲害肆虐。某日,施海回水峪村探親發現情況后,立即采取了救助措施——除蟲害,堵樹洞,立支柱,用拉桿牽引有危險隱患的主枝,并施肥澆水,注射營養劑,進行生物技術復壯。措施果然奏效,來年春天古樹返老還童,恢復了樹勢。蓊蓊郁郁,聚氣巢云。
云祥觀離施海家很近,聽到上課的鈴聲,從家里往學校跑都來得及。后來,不知什么原因,學校就沒了,只剩下一座空空的古廟,一個搞奇石的人就把古廟租下來,古廟就成了奇石館。四株古樹的日常養護和管理也就由奇石館的人代為進行了。或許,施海對于古樹的認識,就是從這四株古樹開始的吧。
如今,云祥觀古廟里這四株古樹成了名樹。許多名人來水峪村必進云祥觀院落里看這四株古樹。瞿弦和、蔣大為、賈平凹等都來看過,并在古樹旁邊與奇石館館長照相合影。畫毛澤東的畫家劉文西也來看過,臨別時,他提筆留下四個字:美在自然。字有些清瘦,但風骨硬朗。
八月的某一天,我走進云祥觀。哎呀,一地的槐花呀!如同清晨剛剛下過的一場清雪,彌漫著芳香。一個穿花裙子的小女孩正揮動著一把竹掃帚,嘩嘩嘩地掃著槐花。喳喳喳——!喳喳喳——!一只喜鵲飛來,落在槐枝上,一跳一跳,槐花便撲簌簌噴雪般濺落地面。有幾朵濺落到小女孩的頭上和肩上,小女孩輕輕抖了抖,笑了。屋檐下,一個坐在小板凳上用鉤針打著毛衣的婦女,抬頭望一眼掃槐花的小女孩,滿臉的喜悅和幸福。
水峪,水峪,水是如此的豐沛。是的,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因之水,水峪人的每一天都朗潤飽滿,氣息別樣。那一地的槐花,也是水的另一種存在形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