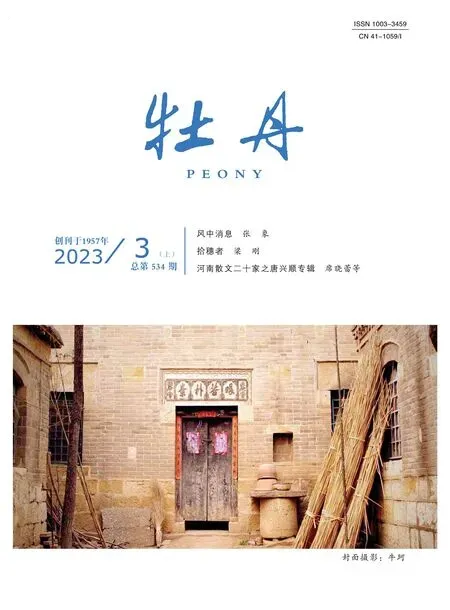犄角
馮耀民
一邊是賣金銀首飾,一邊是賣服裝。賣服裝的一面墻與賣金銀首飾的一面墻相接,但凸出了兩尺來寬,形成了一個犄角。
犄角外是人行道。人行道外是街道。街道兩側的法國梧桐,棵棵粗大,樹冠高過四五層樓。離犄角三四米是十字街。
犄角掩映在濃綠的法國梧桐下,居鬧市,卻清幽、安適。
他就在這犄角擦鞋。一口長方形木箱,一把藤條圈椅,兩只矮板凳,是他做事的工具。圈椅有些年代了,靠背的藤條磨得光亮,左邊的半圈也許壞了,用一塊藍布包著。木箱是三層,黑漆斑駁不堪,也是許久以前的物件。矮板凳的木頭面磨得照見人影兒,尺把長,四條腿呈“外八字”,疑心是否坐得穩。來顧客了,顧客坐圈椅,腳搭一只矮板凳。他坐另一只矮板凳,給顧客擦鞋。沒有顧客,他就坐圈椅,背靠圈椅,仰著面,抱著雙臂,伸長腿,腳搭板凳,打盹。圈椅靠著犄角。他就靠在犄角。一棵法國梧桐正對著犄角,枝葉遮著犄角,遮著人行道。晴好天,細碎的陽光銀子似的落在他臉上身上。
有時,也見他抱著雙臂,在人行道上踱步。就在犄角左右四五步的范圍。“擦鞋吧。”“擦不擦鞋?”之類招攬生意的話,沒聽見他說過。
他長得胖,肚子像扣了個大臉盆。中等個子,背負著大肚子,走路蹣跚。臉胖得肉往下墜。面色灰黑,像鉆了煙囪沒洗干凈。平頭,有很多白發。擰著眉頭,眉心舒展不開。我知道那是歲月使肌肉失去了彈性,就算熟睡,那眉心的幾道杠杠也不得舒展。
這個犄角,我天天都能看見。因為我上班經過時,還沒走過十字街,遠遠地就能看到。以前,我站在十字街等紅綠燈,看的是犄角的最上方,它與藍天相接,養眼。自從看見他在犄角擦鞋,我自覺不自覺地看向了犄角最下方。除了下雨天,我上班都能看見他。
我第一次看見他在犄角擦鞋是秋天。法國梧桐葉色青黃,稀稀疏疏地飄落。他在給顧客擦鞋。低著頭,弓著背。因為肚子大,身子向前傾斜很多,屁股撅起老高,他幾乎沒有坐著矮板凳。黃昏時,夕陽從遠處投來一束光,照在對面高樓上的玻璃墻上。一團紅紅的光,反射到犄角上,像掛著一盞紅光燈泡,給有些昏暗的犄角以光亮。我走過他身旁,我看他,他一點兒也沒察覺,他正專心給顧客擦鞋。擦得好吃力。
在小城,像這樣在街上露天擦鞋,我很久沒有看到了。以前,人多的街頭、巷子,會有一個男性老人或男性中年人,撐一把土黃色大傘,擺上工具,給人們修鞋,順帶擦鞋。不幾時,街上有了專門擦鞋的。繁華的街道,相隔不遠就會有一個擦鞋的。汽車站進出街道旁的人行道上,更是不講距離,一溜擦鞋的。男的女的都有。女的以大媽居多。她們擦鞋手腳麻利,興頭高漲。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從小城開了第一家擦鞋店,掛起了擦鞋招牌。接著,就有了第二家,第三家……擦鞋這份工作,跟其它生意一樣就有了門面,不再是地攤。莫說街上,就是車站,地攤擦鞋的也銷聲匿跡了。當然,擦鞋店也修補鞋子,街頭巷尾自然也沒有了撐起大傘修鞋的老大爺。修鞋、擦鞋這種低微的營生,也成了規范、體面的職業。還是全國連鎖。比如我住在學府路的“XX 擦鞋”店就是全國連鎖店,擦的是品牌。
擦鞋全部轉入店內,人行道似乎寬敞了些。擦鞋有了門面,美化了市容。
我以為他在犄角的營生不會長久。
幾場秋雨后,法國梧桐葉焦黃了,打了卷兒,在枝頭顫動。晴天、陰天還是見他在犄角擦鞋或打盹。也許,他在這犄角占用的地盤不大,也不影響行人行走的緣故,使他沒有被攆走吧。
兩三個月了吧。可是,不知為什么,我沒有照顧他一次生意。有幾次,我走近犄角,腳步慢下來,想坐到圈椅上,讓他給我擦鞋。可是,看他腆著個大肚子的吃力勁兒,就又走過去了。因為總感覺他比臨產的孕婦坐在凳子上洗衣服還艱難。
他應該是認得我了。我也覺著他認得我了。是他的眼睛和神情告訴我的。我從穿風衣到穿上羊絨大衣了。法國梧桐葉也紛紛披離。環衛工早上打掃干凈了,很快又滿地都是。我上班下班會看到他拿著一把竹子扎的掃帚掃犄角周圍的落葉。掃帚小,掃把不長,他需要弓身很多。他似乎掃一下,就要直一下腰。我下班了,踏著落葉走向犄角。在我看向他,他也看向我時,他箍著的眉頭上揚了一下,箍緊的眉心似乎舒展了一點,眼睛也亮了一下。也隨即看向了落葉,繼續掃著落葉。從這次偶然目光相遇后,當再次相互看見時,他眼神挺溫和的。只是我沒見他笑過。也沒聽到過他的聲音。因為沒有一次見他和路人聊天。也許我沒看到他遇見熟人。
他是喝茶的。地上近一尺高的玻璃杯,那是個老物件,里面泡有茶葉。他家應該就在老城區,從離這里不遠處的巷子進去,只有老城區的老人們才會保管著一些老物件。
他應該沒有掙到多少錢。雖然這里人流量還可以,但找他擦鞋的不多,我多數看到他坐在圈椅里打盹,也沒見他玩智能手機。晴天、陰天,沒顧客就打盹。雙臂抱在胸前,仰著面,很安詳。行人從他身邊經過,鞋跟的嗒嗒聲,他也不受影響。這個犄角就是他的世界,其他與他無關。
冬天來了,他穿著蓋過膝蓋的深藍色羽絨服,戴著黑色的絨帽,穿著高幫的雪地鞋。犄角雖然能擋風,但這作用不大。冬天,他的臉瘦了,贅肉沒有了。
下雪了,紛紛揚揚的。早上上班時沒見到他。中午下班時,看到了他。他用那把破掃帚把犄角四周的雪掃干凈了。沒有顧客,他臥在圈椅里打盹。雪不大但還沒停歇,有雪片落在他身上。不光我看他,也有行人看他。只是下午下班時,沒見著他。
小城下了一場大雪,從半夜時下起,下了一天多。積雪尺把厚。臘月是小城最冷的時候天晴了,出太陽了,他又來了。
正月,想他應該在家玩。可街上店鋪開業了,他也在這犄角擺好了他的工具,像往常一樣擦鞋、打盹。
覺著他又瘦了些,精神頭也差了些,眼睛有些凹陷。肚子似乎消了點兒,從側面看去,傾斜度平了些。他看見我,眼神閃了一下,有些許笑意。
您這么早就來做事了。我笑著對他說。
嗯。他應答,眼睛里的笑意沒散。
原以為我這樣問,他會像其他老人一樣打開話匣,會多說一些話。可他沒有再多說一句話,神情嚴肅地喝著茶,沒有多說話的意思。一時間,我也不知再說什么好。這是我第一次和他說話,沒想到,就這一句話,一個字,就沒有了。其實盤旋在我心里的話是很多的。他的寡言,他的嚴肅,使話無法說出來。我甚至覺著是不是我一直沒有照他做生意而使他不愿和我多說一句話。可我又覺著不像。因為找他擦鞋的人不多,他好像不在乎。因為他照樣天天來,也沒有吆喝生意。
可是看見他,成了我的習慣。走到這個范圍,我的視線總會第一時間落到犄角。
法國梧桐葉嫩綠的時候,一天下午,我遠遠看見一個小女孩和他在人行道上打羽毛球。小女孩八九歲的樣子,穿件火紅色的外套。天晴得好,沒有明顯的風。法國梧桐樹上芽葉稀疏,不足以把枝頭掩蓋,在斜陽的輝映下濃淡有致,嬌嫩得如同小女孩的臉。小女孩仰著頭,揮著羽毛球拍,打過去一個球,咯咯笑著:“爺爺!接好!”他也笑著,眼睛笑成了彎月。后來幾個黃昏,小女孩也來陪他打過幾次羽毛球。他的笑,像歡欣的輕音樂縈繞在臉上。
春天很快過去,進入梅雨季。出了梅雨季,也沒見到他。直到九月開學,我還是沒有看見他,犄角顯得空蕩,落寞。
犄角斜對面的人行道旁,有個二十幾年的配鑰匙攤兒。我在那兒配過幾次鑰匙,配鑰匙老人認識我。想他應該知道擦鞋老人的事,黃昏下班了,就去問他。
伯伯,那位擦鞋的伯伯咋沒來了?
兩個月前死了。
得的啥病?
唉,他得了肝病,等查出來,晚了。
什么時候查出來的?
去年秋天。他還堅持了這么長時間。
去年他咋沒去住院治,卻來擦鞋?
治了也不起作用,他不去住院,在家吃藥。
我再次望向犄角。仿佛看見他弓著背、腆著大肚子、臀部翹起的情景。犄角上的一枝法國梧桐,葉子泛著淡淡的黃。夕陽余暉從對面高樓上的玻璃墻上反射過來,給犄角上的樹葉、墻壁,涂上了金粉,好看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