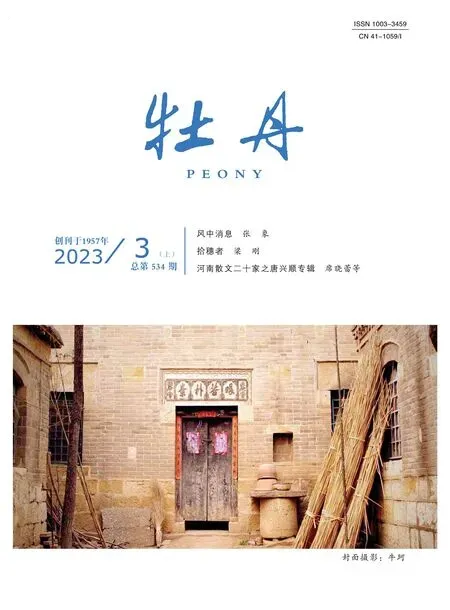春到河窯
楊亞麗
河窯村韓書記要帶我去看“龍頭”——青龍山的。
那天立秋,金風颯颯,略嫌燥熱。
從高空俯瞰,盤踞在黃河之濱的青龍山,就是一條土龍。勤勞的人民,除了用力氣換取糧食,還會用智慧生發故事,青龍山,當然也不例外。
在河窯,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
新安名門望族呂氏家族,在明清之際創造了“忠孝簪纓,五世進士”的奇跡,并綿延興盛200多年,是“甲于全豫”的“中原望族”。史料顯示,新安呂氏家族成為“中原望族”,與呂鄉、呂孔學、呂維祺祖孫三代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然而,在河窯村,呂氏家族號稱“呂半朝”,意思是朝廷里一半的重臣都出自新安呂氏。話有點滿,卻很有意思。老百姓羨慕呂氏人才輩出,就說人家既占了天時、人和,還占了地利。地利是什么?因為呂氏的老宅按在了青龍山的龍頭附近。人們還說,如果不是那個南方術士眼紅嫉妒,率領官府的人挖了三天三夜,挖斷了龍脖,挖斷了龍脈,呂家恐怕要出個皇帝呢。
傳說很有趣,本身就是莊戶人閑暇聚首閑聊間碰撞出來的一種民間文化,不能深究它的真實性,但他們的想象力和故事組合力的確為辛苦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樂趣。
1
四野蒼莽,一條小路,越發逼仄難行。林林總總的樹木,手牽手、肩并肩拉起一道道屏障,阻擋著我們的去路。棄車后徒步走了十幾分鐘,來到一個相對平坦的地界。
眼前不聞水聲,沒有去路。可韓書記說,這里三面環水。經過他的介紹,我有點明白自己的處境,我站在探出萬山湖的一塊長條狀的土地上。韓書記想讓我親眼目睹“龍頭”的風姿,可幾經試探,也沒有撥開眼前茂密的雜樹。
他只好指著一個方向說,喏,龍頭就在那個地方。我去過鷹嘴山,去過偉人仰臥,深諳造物者造型造物的能力,雖然沒看到龍頭那直觀又奇妙的景象,但也被韓書記熱切的心情所感染了。作為一村之主,他多么想讓河窯這個古老的村子煥發出新的生機。被荒草雜樹占據的地方,原來都是莊稼地。雖然河窯村的耕地面積是730畝,荒地面積是600多畝,可莊稼人怎舍得讓地荒著呢,雖然靠天收,卻也春種秋播,絲毫不會懈怠。
六七年前,河窯村的土地流轉給了一個企業,只開發了200 多畝,多數土地還沒有很好的規劃措施,這些人老幾輩開墾的土地,只能是荒草樹木的天下了。雖然,老百姓年年不用種地,還能拿到一些錢糧,眼看著土地荒蕪,可不是農民的天性啊——我明白韓書記的一片苦心。
一路上,不斷傳來挖掘機作業的隆隆聲響。一路上,韓書記手機鈴聲頻響,無不是平整土地的有關事務。一塊塊布滿荊棘荒草灌木、巴掌大的荒地,要被韓書記們一塊塊平整出來。它們就像一顆顆蘊藏希望的水珠,被匯聚在一起,從而連成一片,連成一大片,只到連成希望的海洋。“海洋”里的油菜花、櫻花,將在春天里展露笑顏,迎接四方賓朋。
2
關于河窯,我并不陌生。從東嶺到河窯,走的仍然是新-孟-洛古道——這是一條溫暖之路。
河窯地處倉頭鎮西北部,煤炭資源豐富,周邊有北冶煤礦、石寺塔山煤礦、仝家坡煤礦、云水煤礦等等。過去,河窯管孟津、洛陽叫“東鄉”,從這兩個地方來的拉煤人,叫做“東鄉人”。他們不知道,我家在洛陽,我們管河窯這一帶叫做“北山底”。小時候,最不耐煩聽得就是嬸子大娘一本正經地挑唆小孩子說:你知道嗎?你不是你爸媽親生的,你是從“北山底”的煤窯里挖出來的。五六歲的年紀,哪兒知道這是善意的卻充滿負能量的玩笑呢,于是記得有一次,受到母親訓斥后,我居然跑出門外,哭著喊著要去“北山底”找“親媽”去……于是,對于北山底,幼年的我,是神秘的,是充滿想象的一個地方。
父親來過北山底,拉煤,來一次,不亞于爬了十座山。五更起身,大半夜到家,除了一口白牙,通身漆黑得像是非洲人。弟兄幾個做伴,一個駕轅,一人拉套繩,一人推車幫。可苦了沒有男丁或男人不在家的人家,只好讓人送煤,不但要付煤錢,還要多掏運載的工錢,還要舍上兩碗荷包蛋。送煤人我見過,褲腿挽得高高的,褐色如鐵的肌肉上,拱出一條條青紫色的“蚯蚓”,他們起身走后,竹椅上能掃下一捧煤灰。
韓書記說,舊時的河窯,雖然藏在山仡佬里,卻興旺得很哩。這是因為河窯的位置關系,它成了南來北往客旅歇腳之地。崎嶇漫長的山路,在車拉肩扛的年月,沒有誰能一口氣把北山底的煤運到外鄉去。
現在的河窯,只是一個移民后靠村。從前的河窯,在如今的萬山湖底下,那里有大車院,有騾車院,有大染坊,有中藥鋪,有鐵匠鋪,是個標標準準的繁華之地。
大車院和騾車院,是當地人自己的院子,只不過分了前后院,前面留宿,后院喂牲口。自帶干糧的,只需掏出幾分錢,要一壺開水泡饃果腹。地利之便,讓種著莊稼的河窯人又多了一份現錢的收入。我相信,我父親是來過河窯的,因為他給我講過“捎坡”的故事。說東鄉一個人到北山底拉煤,遇到一個坡,實在上不去,看到后面來個牽牛的小伙子,就央求人家推上一把。小伙子說:“大哥,推上去可以,得掏錢。”東鄉人說,掏錢就掏錢。上來坡,東鄉人看小伙子面熟,就問姓啥。小伙子實誠,照實說了。倆人一攀談,結果小伙子得管東鄉人喊三爺,他們是沒出五服的本家。故事很真實,也講明了捎坡這個職業的本質,是靠地利衍生的一個民間行當,雖然得付出一定報酬,但卻在艱難之時得到了援助,不亞于雪中送炭。
3
看似貌不驚人的河窯,卻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河南省委牽頭拍攝的電影《畛河兒女》的誕生地。河窯,原名衡窯,村子中穿過一條小河,是黃河二級支流畛河的支流。它和畛河一樣,能照顧到村民的生活,卻照顧不到河窯村的坡地。為了讓荒坡變為良田,河窯人出了大力。靠著騾拉肩扛,炮崩釬鑿,人們披荊斬棘,逢山開路,一塊塊石頭運出了大山,砌成了一道道水渠,一座座提水站,一個個大水塘。萬物之靈的水被引到了山上,莊稼得到了灌溉,人們收獲了糧食,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
《畛河兒女》沒有文藝片的含蓄,沒有武打片的熱鬧,我感覺它更像一部戰爭片,只不過,戰斗的對象是山,是水!也是人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艱苦奮斗歷程的真實寫照。艱苦而輝煌的歲月,已經離我們遠去,可那種催人奮進的精神,如滔滔不絕的黃河之水,將會永遠流傳。
時間到了1999 年,河窯人再次經歷了山鄉“巨變”。為了建設小浪底水庫,河窯被劃入了淹沒區。故土雖然難離,可為了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河窯人又一次積極響應了國家號召,有的搬離了家鄉,有的住進了后靠村。幽深的老井沒了,綴滿“小船”的老皂角樹和皴皮的古槐樹也沒了,大車院、騾馬院、大染坊、大石渠、提水站,都淹沒在了歷史的江河。那個老人口中古老的河窯村,也會漸漸被歲月的風沙遮掩。但歷史的車輪不會停滯,一代又一代的人還要生活,更好地生活。
4
河窯,原本沉默的山村,要煥發生機啦。
為貫徹落實習總書記在河南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時強調的“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講好‘黃河故事’”的重要精神,傳承創新河洛文化,樹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市領導“立足生態保護謀劃發展思路,鞏固提升沿黃生態綠化成果,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實踐中展現擔當、作出貢獻。”精神的指導下,新安縣倉頭鎮乃至河窯村的干部群眾,從上到下形成合力,為河窯的發展振興謀取福祉。
經多方考察論證,河窯村的騰飛,依然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閑置的坡地,在人們的辛勤耕耘下,也將變成花海、樹林,勤勞的河窯人,依托近在咫尺的萬山湖,要將三面環水、背靠青龍山的河窯打造成山清水秀的“小江南”。
在這里,人們或漫步林間小道,或登臨望河,都不失為一個遠離都市之外、放牧身心的好去處……
河窯,冥冥中安排,我知道了你的前生。河窯,你的現在和未來,我也會時刻注視著,看到你的蛻變,看到你的騰飛,分享你的每一寸成長與興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