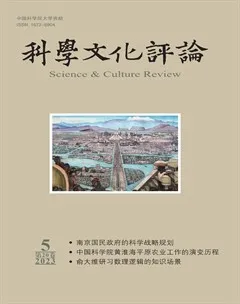男女有“別”評《更好的那一半
——關于女性的遺傳優勢》
李 昂

圖1. 《更好的那一半——關于女性的遺傳優勢》(1)該書中文標題為本文作者譯。書影
作為標題中所指“更好的那一半”中的一員,筆者在書店看到此書封面時,心情真是相當舒適。雖然筆者本人的生活經歷中并沒有遭遇過什么明顯的性別歧視,但是幾千年男權社會留下的遺產絕對不會讓人無感。作者沙倫·莫勒姆(Sharon Moalem)的名字挺有迷惑性——在英語世界中,Sharon常用作女名,因此,乍一看還以為是一本關于女性自我覺醒和重建信心的作品。然而莫勒姆其實是一位男性加拿大醫生、企業家和作家。在此之前,他已經出版過三本科普作品:《病者生存:疾病如何延續人類壽命》(2)Survival of the Sickest:The surprising connections between disease and longevity,2007。中信出版社2018年翻譯出版。,《性是如何運作的:為什么我們會這樣看、聞、嘗、感覺和行動》(3)How Sex Works:Why we look,smell,taste,feel,and act the way we do,2010,未見中文版。和《基因革命:跑步、牛奶、童年經歷如何改變我們的基因》(4)Inheritance:How our genes change our lives——and our lives change our genes,2015。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翻譯出版。,都很受歡迎。他的敘事總是從自己從事過的工作開始,得益于其豐富的學術經歷——其研究對象包括從蜜蜂、土豆到人類等不同物種,研究的問題主要涉及遺傳學和免疫學領域——莫勒姆每每在提供豐富案例的同時,又能給出業內人士的經驗和思考,因此作品生動、有說服力,形成了一種討喜的風格。《更好的那一半——關于女性的遺傳優勢》這本書,則集合了他作為醫生、遺傳學家、創業者和丈夫的多重思考。他的名字曾經給他帶來一些生活中的困擾([1],p.192),同時,可能也使他對女性相關的問題更為敏感。此書在初版的次年就得到重印,可以說這樣的敏感性也讓他收獲了更多的關注。
筆者以往看過的一些女性主義作品,總是基于這樣一種判斷,即女性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由其生理特征決定;對女權的主張,也脫不開女性是弱性別、因而需要被照顧的觀念。難道終于有人要打破這一論斷了么?但是,讀完該書其實略感失望。書中并沒有談及兩性的社會角色,對遺傳基礎帶來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差異也沒有全面論及。作者稱此書旨在論證:女性在遺傳上優于男性([1],p.4),但主要只談到了免疫和神經發育兩方面,并且說來說去其真正的依據只有一條,即女性有兩個X染色體,可以選擇其一表達,因此較之只攜帶一條X染色體的男性更具遺傳多樣性和遺傳可塑性。
當然,作者提出的這一論證可以分解出若干知識點。首先,X染色體和Y染色體在攜帶遺傳信息的體量上并不是對等的(5)染色體編號是按大小排序的,人類X染色體的大小介于6號和7號染色體之間,Y染色體則是最小的。——X染色體有1000多個基因,而Y染色體只有70多個。在X染色體的1000個基因中,多數都與性別無關,有些還是看家基因(6)是指在生物體內所有細胞中都表達,并且為維持細胞基本生命活動所需而時刻都在表達的高度保守的基因。。其中已知有100多個與腦部發育有關([1],p.61),另外與免疫功能相關的一些重要基因也在X染色體上。而Y染色體上的基因則多數只與精子的形成過程相關。第二,以往認為女性的兩條X染色體中有一條是失活的——它們在胚胎發育早期凝聚成染色異常的巴氏小體,于是其中的基因不再表達。然而,新的研究表明靜默的X染色體上仍然有1/4的基因是活躍的([1],p.31)。因此作者把女性比做混合動力車,而多出來的X染色體就提供了額外的遺傳動力。這類知識的介紹,在書的各章重復了多次,雖然有些啰嗦,不過對于不熟悉生物學的讀者,也許還是需要的。
在該書的前兩章,作者首先以一些個人的觀察來說明在人類生命的初始和臨終階段,女性的存活率比男性高。他講到自己的一項研究需要男女比例相當的老年受試者,但是在老人院里找不到足夠的志愿者,因為男性太少了;又講到在新生兒ICU實習時,發現男嬰總是比女嬰存活率低。同時他也列出了各種統計數據來證明這些是普遍現象。接著,他舉出了幽門螺旋桿菌、HIV、結核桿菌等一系列微生物感染在不同性別間的發病率,想說明女性更能抵抗感染類疾病的侵襲。這些講述從吸引讀者的角度看,無疑是成功的。但是要作為論證步驟,邏輯上就顯得不太嚴密了。并且,有很多非感染類的病癥,女性的發病率明顯高于男性,例如對人類健康福祉威脅極大的老年癡呆就是女性更易罹患。最新的研究認為老年癡呆與X染色體上的去泛素化酶基因USP11的高表達有關[2],恰恰證明了女性在這一點上的遺傳劣勢(7)2020年還出版了一本同樣在封面上印了兩個大寫X的書——《XX 大腦:讓女性有能力預防癡呆并最大程度保持認知健康的開創性科學》(The XX Brain:The groundbreaking science empowering women to maximize cognitive health and prevent alzheimer’s disease),講的就是這方面的問題。。
該書的第三、四章試圖說明男性大腦的劣勢以及分析女性何以活得更長。在第三章作者提供的證據,包括:一些國家對兒童智力發育的統計數據;關于“X連鎖智力缺陷”、個別基因突變帶來的男性暴力和認知障礙的研究結果(同時述及女性獨有的“四色視覺”);并從神經發育的角度對上述案例做了一些解釋。但是作者同時也承認“今天的遺傳學還處在學齡前兒童的階段”([1],p.86 )可以做的解釋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在第四章,作者同樣使用的是舉例法,他給出山地自行車、超級馬拉松等長距離的體育比賽中,女性運動員勝過男性運動員的例子;以及一些歷史上的探險故事,用來證明:盡管男性有更多的肌肉和身高、體能上的優勢,但是到了要在艱難條件下生存時,總是女性勝出。在這一章里,他還提到在其他物種中(如鳥類、爬行動物等),也是同配性別更具生存優勢(8)在已有的54個國家的統計中,女性壽命都比男性長。擁有一對X染色體帶來的優勢并不僅限于人類,另外對344個物種的研究也是如此(鳥類ZZ優于ZW)。。第五章則是一系列反例,指出女性免疫力高的代價,是更容易罹患自身免疫疾病。這一章的敘述無疑是誠實中肯的,但是對照標題和書中關于“優勢”的強烈論點,就顯得頗尷尬。
如果說該書前面這幾章從標題到內容都有博人眼球之嫌,且“論證”也不算多么嚴密,書的最后一章——“健康福祉”(Well-Being:Why women’s health is not men’s health),落腳點倒是很有可取之處。它提醒讀者關注一個值得嚴肅對待的現實問題,即目前醫療實踐所基于的實驗數據,絕大多數來自雄性動物或男性受試者,而沒有考慮女性在解剖、代謝和免疫等方面的不同,都會導致對藥物響應上的差別。例如安眠藥安必恩給男女開的劑量應該不同,因為女性對它的代謝速度慢。常用的退燒藥泰諾也是如此。然而,對女性(乃至雌性動物)生物學特性的研究,甚至是在解剖學這樣古老的學科,都非常欠缺(尤其是涉及性器官、性生理、和性行為等方面)[3]。在缺乏積累的情況下,要進行相應的對比研究顯然也是困難重重。事實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是從1993年才開始要求其資助的藥物研究項目,必須包括兩種性別的樣本。這意味著之前開發的藥物理論上都需要做補充研究,以更好地掌握用藥劑量([1],pp.182—184)。并且,在開展臨床之前的動物實驗中,簡單的加入雌鼠可能還不行,因為常規供應的實驗動物一般都被同系繁殖了好幾代,雌鼠的兩個X染色體是一樣的,不能很好地代表真實群體。這樣的細節問題,若非親身從事過相關研究,恐怕壓根不會意識到,幸而本書作者沙倫·莫勒姆確實有過不少藥物開發的經歷。
總的來說,莫勒姆的這本書把一些大家熟知的事實和另外一些可能比較冷僻的故事、一些來源權威的統計數據和研究結果以及他自己在醫院、實驗室和野外的親身經歷編織到一起;所講述的案例都有可靠的出處,閱讀體驗還是不錯的。特別值得表揚的是,他在講述各部分研究進展時,很自然的插入了幾個在科學史上常被忽視的女性角色的事跡,如發現性別決定機制的內蒂·史蒂文斯(Nettie Stevens,1861—1912)(9)1905年,她首先觀察到雄性黃粉蟲產生兩種精子,分別帶有一條大染色體或一條小染色體。前者使卵子受精時,產生雌性后代,而后者則帶來雄性后代。這就是XY 性別決定系統。但后來的教科書中,總是只提同時代男學者埃德蒙·威爾遜 (Edmund Wilson)的工作。;發現神經生長因子的麗塔·萊維·蒙塔爾奇尼(Rita Levi-Montalcini ,1909—2012)(10)意大利猶太人,1986年與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1922—2020)分享了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和18世紀倡導接種人痘的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1689—1762)(11)她出身英國貴族,嫁給了英國駐伊斯坦布爾的公使,以其在駐外期間寫作的大量書信聞名。她在土耳其生的兒子,是第一個接種“天花疫苗”的英國人。等。
然而,作者關于“女性具有遺傳優勢”的論點,在筆者看來若非是為了迎合市場,那就是矯枉過正了。不過這倒是很可以理解。在有“人權燈塔”之稱的美國,女性實際上至今也沒有獲得平等的法律權利(12)美國憲法并沒有賦予女性平等的權利,1920年生效的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讓美國女性有了選舉權,但是,更進一步的平等權利修正案(ERA)自1921年首次被遞交至美國國會至今,歷經多次審議、一直沒有通過。,因此各種層面的斗爭不斷,而一些男性知識分子也愿意對此做些反思。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作品,如果表現出同情女性的傾向,則很容易受到歡迎。莫勒姆在此書中,就不時拿自己和妻子在經歷若干流行病時的表現做比較,表達對妻子抵抗力強的羨慕。估計凡有類似經驗的丈夫,讀到這里必然感同身受,而女性讀者則不免竊喜。總之,本書從標題到內容都有著取悅女性讀者的意味。
也許,指出女性在生物學意義上具有某種“優勢”,能夠給在社會上仍處于弱勢地位的她們帶來一些自信。但是,就這一話題,以對立的、競爭的方式進行討論,認為一個性別必須“優于”另一個性別,竊以為無益于社會進步。以往將女性看作弱性別的舊習雖然不值得提倡,但也沒必要將其提升為強性別。而本書最具價值的一點就是:明確提出“女性的健康與男性的健康不能等量齊觀”。畢竟,以科學的態度正視并深入理解兩性的生理差異,在研究中給予二者同樣的重視,才是追求人格和社會權利平等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