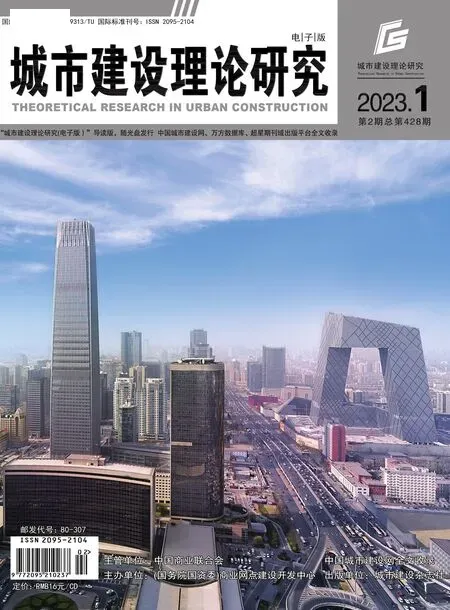淺談鄉村旅游業發展模式探索
——以北京市延慶區千家店鎮花盆村為例
熊笛
北京建筑大學 北京 102616
1 引言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獨具魅力的中華文化旅游體驗”。將鄉村的文化產業和旅游結合相結合可以使鄉村的建設體系更完善,最終推動鄉村的經濟和教育發展,提高村民的生活質量。根據北京市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21年北京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0269.6億,在北京市16個市轄區GDP排名中,延慶區GDP為204.7億元,是GDP最低也是GDP增長速度最慢的地區。根據《延慶區2019年低收入產業資金使用方案》,區農業農村局安排4667萬元資金用于支持鄉鎮低收入村戶發展特色民宿、特色種植、休閑觀光產業。以延慶區千家店鎮花盆村為例,對其進行整改,為城市郊區的農村旅游提供借鑒及方向。
2 城市郊區花盆村發展旅游業的可能性及問題探索
2.1 花盆村基本情況
花盆村距延慶城區72公里,距鎮區12.5公里,下轄花盆、前山、耗眼梁、大隊溝4個自然村,全村330戶,人口895人,耕地面積2600畝,山場面積17000公頃。主要農作物:大田玉米。花盆村西有一關帝廟,始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嘉慶二十年(1815年)重修。1985年被確定為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關帝廟為兩進院落,由山門、正殿、后殿、東西配殿、鐘鼓樓等7個部分組成。關帝廟每年的農歷四月二十八關帝廟都要舉辦廟會,周邊十里八村的村民們都來關帝廟前看大戲。
2.2 花盆村發展的困難
2.2.1 貧困人口基數大
延慶區人力社保局在2019年低收入農戶摸底統計中,發現花盆村全村328戶,有188戶屬于低收入農戶,涉及394人,占比57%。花盆村貧困人口基數大,超過一半人口處于低收入區且低收入人口年齡普遍偏大,人均耕地不到一畝,無主導產業。
村內不能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福利待遇普遍較差,農民無法掙到足夠的錢去支持龐大的家庭開銷,只能選擇外出打工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生活。
2.2.2 人口流失嚴重,土地大量荒廢
隨著思想觀念的轉變,花盆村中近九成80后、90后青壯年不愿意繼續留在農村種地,基本都去北京城區和延慶打拼。留在花盆村的人口越來越少,高學歷的年輕人更愿意也更有可能選擇在北京城區或延慶區內安家落戶。農民為了自己工作、子女學習、交通便利、醫療保障、結婚等生活需求選擇進城,進而導致農村房屋閑置,土地大量荒廢。
2.2.3 花盆村建設缺乏規劃
現有村落格局形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起初村民住房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簡單地履行一個報批手續,建多大面積、建什么式樣房屋沒有規劃,也沒有專門部門管,再加上每家農戶的經濟實力不一樣,一旦房子建好以后就無法改變[1]。花盆村也有相同的問題,建筑的形狀樣式及布局都按照各自喜好而成,沒有有效的村鎮規劃,花盆村亂搭亂建的現象仍存在。這些因素導致花盆村建設格局較為混亂,地下管網線等基礎設施無法規范鋪設,加大了人居環境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的難度。近年財政投入大量資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并投向相對較為單一,對直接關乎農民生活的教育、文化、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較少。
2.3 花盆村發展的優勢
農村旅游業的發展目前有受益面大、綜合拓展力強、有著較強的推進后續發展進程的能力,我國農村旅游業的大力開發有助于帶動農村產業經濟鏈的提升[2]。花盆村在土地資源、交通、自然資源、人文資源、人口等方面有充足的可待挖掘優勢,符合發展旅游業的條件,而旅游業的發展也可以使花盆村的產業結構更加多元化,加速助推了花盆村的振興戰略。
2.3.1 土地資源豐富
土地制度是農村經濟制度中最根本的制度[3]。 花盆村耕地面積2600畝,其中退耕還林地200畝,山場面積17000公頃。由于花盆村人口的流失,土地未得到合理的開發利用,在花盆村有65%以上的土地面積都是待使用狀態。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土地資源成為促進農村地區發展,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是推動農村經濟水平提升的關鍵因素[4]。花盆村的土地資源是很好的待開發資源。
2.3.2 當地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豐富
千家店鎮鎮域面積371km2,占延慶區域面積的1/6,生態林面積31733hm2,占延慶區生態林面積的1/4,是延慶乃至北京最邊遠的山區大鎮[5]。花盆森林公園距離關帝廟僅100m,花盆村背靠大山,境內山巒重疊,其中有豐富的山林物資,野菜有薺菜、野蒜、苜蓿、苦苣菜、車前草等,果樹包含延慶地區獨有的脆八棱海棠果以及較多的蘋果樹、桃樹,動物有野兔、狐貍、灰鶴以及豹貓等等,可以將其打造成山地果園和旅游景觀。花盆村距離全國第一個涵蓋全鎮域范圍的“鎮景合一”大型國家4A級旅游景區——百里山水畫廊僅16.2公里,僅需20分鐘的路程,一小時內路程還包括朝陽寺、烏龍峽谷等眾多鎮域內景點,為吸引游客前來打造了堅實的資源基礎。
2.3.3 人口結構優勢
整個千家店鎮經過多年的環境整治,加上延慶區政府極力推廣旅游業的發展,千家店鎮已經構成了良好的旅游產業形勢。花盆村的村民對民俗旅游發展理念的認同感整體較強,雖然有人口流失,但當地人口的平均年齡在52歲,還有較強的勞動能力,而且外出打工的年輕勞動力中有96%的人口均在北京城及延慶區內工作,如果有需要隨時可以回村參與建設。
2.3.4 交通優勢
千家店鎮花盆村位于延慶區東部山區,現如今都已鋪上了水泥路。沿京藏高速延慶城區62出口出,沿S309直達花盆村。花盆村有兩條公交線,一條為Y13,一條為925支菜木溝,公交路線環繞百里山水畫廊景區。從北京城六區或從延慶區出發,適合兩日自駕游。
3 花盆村旅游商業模式的探索
3.1 中國鄉村發展的十大模式
根據農業部在“鄉村夢想——美麗鄉村建設與發展國際論壇”上的報告,中國鄉村發展存在十大模式,分別為產業發展型模式、生態保護型模式、城郊集約型模式、社會綜治型模式、文化傳承型模式、漁業開發型模式、草原牧場型模式、環境政治型模式、休閑旅游型模式、高效農業型模式。
3.1.1 花盆村產業發展型模式分析
產業發展型其特點是產業優勢和特色明顯,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發展基礎好,產業化水平高,初步形成“一村一品”、“一鄉一業”,花盆村背靠大山,境內山巒重疊,有豐富的山林物資,野菜、果樹、動物等,比較容易實現農業生產聚集、農業規模經營,進而實現產業帶動村落發展。
3.1.2 花盆村休閑旅游型模式分析
休閑旅游型美麗鄉村模式主要是在適宜發展鄉村旅游的地區,其特點是旅游資源豐富,花盆村處在“鎮景合一”大型國家4A級旅游景區——百里山水畫廊附近,并且當地具備關帝廟、花盆森林公園等旅游資源。雖然花盆村目前住宿、餐飲、休閑娛樂等設施不夠完善,但花盆村交通便捷,距離城市較近,并且有人口優勢等,可以在此基礎上注重住宿、餐飲、休閑娛樂等的開發和完善。整體來看花盆村發展鄉村旅游潛力較大,適合休閑度假。
3.2 花盆村鄉村建設方式
通過對以上鄉村建設模式的分析,我選擇用產業發展型和休閑旅游型兩種模式結合的進行農村建設。在如今的時代背景下,越來越快的工作和生活節奏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人們迫切需要釋放在心中積攢的郁壘,遠離城市,去農村游玩成為了當下人們的主流選擇,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可以完美的契合在一起,二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3.2.1 以往農村旅游業發展方式分析
農村旅游產業主要有兩種發展模式:其一是以村委會為主的自主開發式農村旅游開發模式,其二是以旅游開發公司為主的農村旅游模式[6]。雙方各有缺陷,前者理論知識缺乏、實踐經驗不足,不具備長遠的戰略眼光,在策劃、管理和宣傳方面處于劣勢,但同時擁有全部的決定權,不被旅游開發公司的規定束縛,利潤相對較高;后者正好相反,在方案的制定、人員的培訓以及旅游服務方面更加專業,能夠帶領農村旅游業朝高精尖方向塑造。但相對的,旅游開發公司權力的增加,就意味著農民話語權的減少,當地村民往往被動地成為了旅游開發的客體而非主體,并且外來的強勢資本與弱勢農民群體之間難以實現平等對話,致使大量經濟利益從當地流走,難以形成良性機制[7]。
3.2.2 花盆村旅游業發展方式探索
從促進鄉村旅游產業能有更好的作為來講,加速促進第一產業的農業與第三產業的旅游業深度融合發展,促進農旅結合型鄉村旅游產業更快發展,不但能夠促進鄉村產業振興,還可以給農業帶來新動能,激發農村內生動力,調動農民參與鄉村旅游的積極性,順帶推動農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促進農民增收等益處。
花盆村旅游業發展方式建議多維一體的抱團發展,村委會、開發公司、當地村民等組成開發小組。村委會作為鏈接的紐帶具有非常重要的橋接作用,以村委會作為中間主體,一方面聯系鄉鎮政府,與國家溝通,能在政策和制度上獲得支持,可以進行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的轉移,讓農村實現產業化。農村旅游開發公司提供經濟和人才管理上的援助。對當地居民進行有關旅游業的相關教育和培養,不但能推動農村產業的優質發展,也促進鄉村產業振興進而實現鄉村旅游的提質升級。
3.3 花盆村旅游業商業模式的組成及分工
3.3.1 花盆村旅游業建設商業分工
政府分工:提供閑置土地,出臺政策扶持花盆村旅游業的發展,設置獎勵機制、成立專項撥款給當地村民以及管理外來企業,在不過度開發環境的情況下建設鄉村,外加以政府渠道宣傳推廣當地鄉村旅游。
村民分工:在政府的補貼下,將村落空余和閑置房屋打造成民宿供游客居住休息,為游客提供旅游規劃以及線路等引導工作。
企業分工:旅游開發公司建設中心游樂場(例如北京歡樂谷、鄭州方特歡樂世界等方向),周邊企業建設小娛樂設施,比如在地勢允許有落差的地方修建蹦極場地、在靠近河流的地方打造漂流景點等。
3.3.2 盈利模式思考
建設游樂場的大企業主要的獲利來源為門票、景區內商店及餐飲、娛樂等;小企業則打造周邊小型游樂設施,依靠門票、娛樂設施等獲取收入;村民主要收入來源為游客購買門票提成、農業土特產的販賣以及果園菜園等采摘園的收入。
3.3.3 運營模式探索
構建旅游圈:分期進行建設:一期實驗階段,最先打造的是核心的大型游樂園。游樂園設施初步建設小型過山車、觀光塔和小型超市等初具規模,逐漸外擴。對比兩個項目的運營情況,若過山車更受歡迎則建設跳樓機,若游客對觀光塔更感興趣則添加富有當地特色的文化表演,比如關帝廟的傳說改寫成話劇或評書形式等;二期是經過對周邊山地的考察,尋找合適的地方打造采摘園和動物園(無大型野獸),在靠近河流的地方成立漂流項目,在坡度適宜的地方修建蹦極項目等;三期則是根據游客的意向進行項目的優化和拓展,以及配套設施例如周邊的餐飲、商業、娛樂等。
4 結語
根據艾媒咨詢發布的《2020年中國鄉村旅游發展現狀及旅游用戶分析報告》可知,從2012年至 2019年末,國內鄉村旅游接待的游客總數從7.2億人次增長到了 2019 年的 35億人次,但從2020年開始,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國內旅游市場遭受較大沖擊。一開始國內旅游人次有顯著減少,但隨著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工作推進、疫情防控態勢的穩步好轉,2020年下半年中國國內旅游市場迎來復蘇期。伴隨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恢復,城鄉居民被抑制的需求將持續釋放,農村旅游業因其種種優勢成為了農村經濟發展和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手段[8]。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相比無論在基礎設施、教育資源還是收入福利等方面都還存在著顯著差距。政府主要從政策的角度推動鄉村旅游業的發展,企業帶來的經濟支持屬于雙贏的投資,村民自身也要積極參與,努力提升文化水平,提高素質教養,三方協同合作,共建美麗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