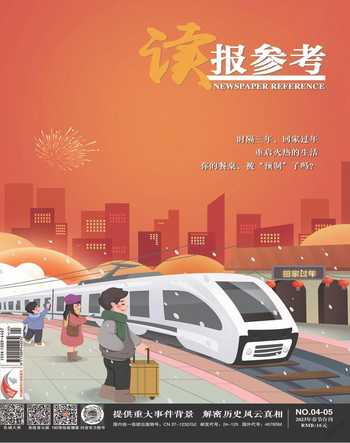他們選擇這樣老去
中國眼下正在進入或是已經進入老年的人,與上輩人相比,擁有更豐富的知識和經歷、更開放的社會環境。他們選擇不同的方式老去,衰老不再意味著對孤獨和死亡的恐懼,或是對日復一日生活的妥協。以下是他們的自述故事——
孫天翼:我給自己更新了17年病歷
? 我81歲了,當了38年醫生。
? 從2005年開始,我給自己準備了一本個人病歷,已經連續更新17年。這本病歷是基于我作為醫生的知識,對自己身體情況的了解來記錄的。病歷的第一頁寫著:“我的終極疾病可能有兩種,一是缺血性中風,二是肺部腫瘤。當我意識不清時,預先留下有關疾病的預防和護理信息,可能會有一定的用處。因此,在我清醒時,就本人的病史、治療、護理三個方面的情況作逐一敘述,會對今后疾病的預防及病后生活質量有幫助。”
? 我為什么預測自己可能會因為這兩種病走向生命末期?一是因為我受過外傷,年輕時曾經騎摩托車摔傷,右側椎體動脈供血不足,容易導致腦供血不足,嚴重的情況下就會中風;二是我以前查出過胸膜炎,也復發過,常常有咳嗽的現象,以后很可能會有肺部的毛病。
? 在病歷里,我還記錄了自己的藥物使用情況,強調要少量使用,“寧可死于藥物不足,也不要死于藥物反應”。我還強調一點,“不要過度搶救”。我見過很多搶救病人的場面,有些癌癥、腫瘤病人已經到了晚期,心功能、腎功能都衰竭了,搶救已經沒有多少價值,病人還被疼痛折磨得非常痛苦。但家屬不懂也放不下,會要求醫生積極搶救。醫生當然知道意義不大,但從情理上說,也不會拒絕,有時候還不得不給病人的心臟注射腎上腺素。總之用上各種辦法,直到病人的呼吸、心跳都沒有了,才宣告結束。
? 我特地和孩子們提到,到了后期,不要作徒勞的搶救,既看不到希望,還對家屬的護理要求很高。
我對自己的生死一直看得很淡。這可能和我當醫生的經歷有關系,看過太多死亡,另一方面也是性格影響。我從小就不怕鬼神、不怕談死亡,你提出來關于死亡的問題,我也不覺得冒犯。
后來,我又學會了攝像和剪輯視頻。70歲那年,我花9000元買了一臺攝像機,這在當時算是比較高檔的了。視頻剪輯的技術,我是自學的,用電腦上的一款好操作的軟件,花錢買幾個視頻教程,邊看邊學著做。我應該是全鎮上第一個會作視頻的人,他們有很多活動都會叫我去拍。后來,我在老年大學還教給了另外幾個年輕點兒的老人。因為我年齡大了,這兩年因為老是玩手機,視力也不太好,我希望他們也能學會,能把我現在的“工作”繼續下去。
郁馥馨:和三狗兩貓的獨居生活
? 前一陣子,我在小紅書上發了一篇筆記介紹自己的生活。我60歲,沒有結過婚,也沒有孩子,獨居在山東棗莊,養著三只狗、兩只貓。那篇筆記收到許多私信,幾乎都是20多歲的年輕女孩,她們來問我:“不婚不育,一個人生活,要攢多少錢才夠?”
? 我的祖籍是山東棗莊,因為父親年輕時流亡去了臺灣,我出生在臺灣的一個小縣城,在那里長大。大學畢業后,我在一家報社當了12年版面編輯,平時自己愛寫文章,也出版了一些作品。在報社時,有人問過我:“你現在工作生活怎么樣?”我說:“很平靜,跟死了一樣。”那種狀態之下,自己也希望能有契機作出一些改變。
? 轉變發生在千禧年初。2000年左右,互聯網剛剛興起,大家都在網上聊得火熱。那時上網的人都比較時髦,文化水平也不錯。我在一個寫文章的網站上認識了許多大陸的網友,還和其中一個男人網戀了。他比我小15歲,我們在網上交往了兩年。2003年,我41歲,辭職從臺灣來到深圳和他一起生活。但年齡差距確實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加上他的工作變動,4年后,我帶著來時的兩個行李箱,最終輾轉回到了臺灣。
? 后來,我又在臺灣和大陸之間輾轉了幾年。2010年,臺兒莊古城要重建了,我拎著兩個行李箱就來了臺兒莊,后來就在古城里做一些文化宣傳方面的工作,還主編過一本雜志。
? 60年里,我談過好幾段戀愛,但一直沒有結婚。其實,我不是大家想象的“不婚主義者”,只是因為一直沒有遇到合適的、想步入婚姻的人。我還養了三只狗、兩只貓。養寵物一直是我的夢想。一個人生活也會遇到些瑣碎的麻煩,但仔細想想,也沒有太復雜的事情。我現在已經能自己修水電、燃氣灶了,獨立完成一件小事的愉悅感,他人無法體會。總之,不管結不結婚、有沒有孩子,人最終還是要面對一個人的生活。
? 很多人會問我,老了以后沒有人照顧怎么辦?我對這點倒沒有太焦慮,可能是因為我還沒有老到那種程度。另外,我始終覺得,身體機能的衰退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事情,當一個人老眼昏花、腿腳不便時,生活質量必定會極大地下降,對一些自我意識很強的人而言,這種無法控制自己身體的感覺甚至是無法接受的。那時候,有沒有錢、有沒有人照顧,真的會有很大影響嗎?
? 至于經濟方面,我有一定的儲備,絕對算不上多。除了以前工作攢下一點錢以外,往小城市置換房子也留下了一些積蓄。不過,自從我發現每個月只需要2000多塊錢,就能把自己和貓狗照顧得很好,也就不擔心了。“去日苦多”,來日已經不多了,我不需要那么多錢。
韓仕梅:生活的苦累不影響寫詩
? 去年11月,我去北京參加了聯合國婦女署紀念活動,還上臺演講了。會場里坐著30多人,有中國人、外國人,還有兩個人在大屏幕里連線。我太緊張了,完全記不得他們說了什么,一直在心里練習我要講的內容。我在稿子里寫:“我叫韓仕梅,是一個來自河南的普通農婦,也有人稱我為詩人。半個世紀里,我一直呆在農村,不曾想到,有一天我會參加聯合國的活動。”
? 我難得出遠門。50歲以前,我的生活范圍就是以村子為中心的幾公里之內,和所有農村婦女一樣,種地、打工。平時偶爾上一趟縣城,最遠的一次還是18歲那年,我嫂子生小孩,我去了湖北。這次在北京,朋友帶我去逛了故宮。電視劇里常常演發生在故宮里的歷史,我踩到那些地磚上,想象幾百年前的人也是這樣走著,就覺得特別神奇。
? 現在回頭想想,真不知道前半生是咋走過來的,渾渾噩噩。這大半輩子,母親、丈夫、孩子都在牽絆著我。我19歲時,我媽幫我和老頭子(如今的丈夫)定了親。家里姐妹四個,都是我媽包辦的婚姻,她很強勢,不給你選擇權和發言權,沒人敢反抗。老頭子天生反應慢、木訥,我不肯跟他,但是我媽已經收了人家3000元的彩禮錢,拿去修房子。就這樣拖了3年,我最后還是嫁過來了。
? 我沒有一個人能依靠。老頭子的腦子不聰明,以前愛跟人打牌,四個人里三個人贏,每次都是他輸,這個家欠了不少外債,我嫁過來以后得掙錢還債、養家、蓋房子,去工地抬過鋼筋,給人看過倉庫,懷兒子的時候身子都站不起來,一條腿跪在地上干活。家里有個事情也沒人商量,老頭子想不來麻煩的事,當時要考慮送兒子上大學,送去哪里、花多少錢,我好幾個晚上沒睡,一邊想一邊流眼淚。至于我寫詩,他更不懂了。
? 不過,這些沒有影響我寫詩。我覺得,寫詩還是得看靈感和天賦,靈感來了,很多話就紛紛往外冒。很多詩都是來自生活里的感觸,我這一生過得不開心,也不幸福,寫的詩大多數看起來很苦悶。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吳淑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