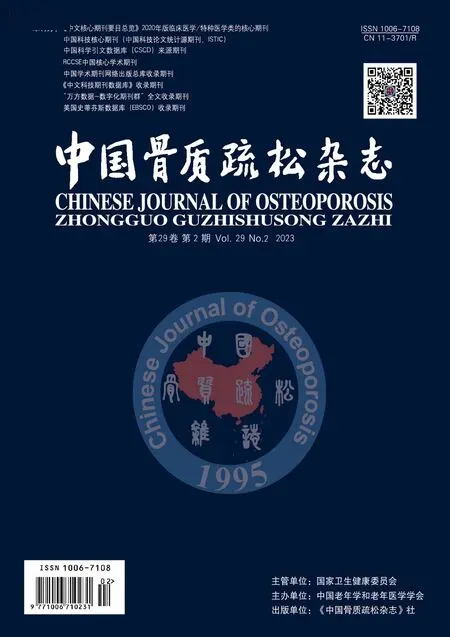骨質疏松性椎體骨折級聯的風險因素
樊宇宇 丁立祥 宋紅星 侯宇 易蒙 王普石 喬軍杰 方秀統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北京 100080
隨著世界人口老齡化的進程,骨質疏松性骨折成為一個日益增長的醫藥、社會和經濟問題。據估計,在全球范圍內,骨質疏松性骨折每3 s發生一次。椎體骨折是最常見的骨質疏松性骨折。作為一種骨質疏松性骨折,椎體骨折的發病率隨年齡呈指數增長,它增加了其他脆性骨折的風險,并導致較高的社會成本和死亡率,椎體骨折患者的死亡風險是無椎體骨折患者的2.7倍。這種死亡率的增加與椎體骨折的數量和嚴重程度都有關[1]。
一個椎體發生骨折后,繼發其他椎體再骨折的風險增加4~7倍,隨著椎體骨折數目的增加,風險呈指數增長[2]。Habibi等[3]報道117例胸腰椎骨折的患者在6個月內有11例出現新發的椎體骨折。Ganguly等[4]發現既往椎體骨折患者發生新的椎體骨折的風險是其他患者的5倍,且有陳舊性椎體骨折的患者在隨訪過程中,每100例患者中有26.2例發生骨折。這種先前發生過椎體骨折的患者椎體骨折的發生率更高,這種連續發生的椎體骨折被稱為“椎體級聯骨折”(vertebral fractures cascade,VFC)。VFC發生的原因復雜,風險因素眾多。在一些研究中,糖皮質激素的使用、先前骨折的部位、程度、數目、一些內分泌疾病、椎體成形術、抗骨質疏松藥物的使用等都是VFC發生的相關風險因素。本研究通過收集患者的臨床資料,進一步分析骨折部位、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體質量指數等是否為VFC發生的風險因素。以確保醫療機構可以有效地整合椎體骨折預防的途徑,讓更多患者得到有效治療,以減少繼發骨折的發生。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診斷為骨質疏松性椎體骨折的444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存在骨質疏松性椎體級聯骨折的患者共136例。納入標準:(1)第一次椎體骨折發生在2015年1月1日之后,再次骨折發生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2)椎體骨折的發生沒有明顯的暴力外傷史。排除標準:病理性椎體骨折的患者,包括多發性骨髓瘤及椎體原發及轉移癌的患者。所有患者對于本次研究均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統計所有患者的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骨折的部位、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是否有糖尿病、是否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否有口服糖皮質激素史。按照是否發生椎體級聯骨折分為兩組:椎體骨折級聯組和非椎體骨折級聯組。分析兩組患者間年齡、性別、BMI、骨折的部位、骨密度、是否有糖尿病、是否有COPD、是否有口服激素史的差異,分析椎體骨折級聯反應發病的風險因素。
其中將椎體骨折級聯定義為在統計期間曾兩次及以上發生椎體骨折的患者;患有糖尿病定義為曾在醫療機構診斷為糖尿病,包括1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1,T1DM)和2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2,T2DM);口服激素史定義為曾因各種疾病長期口服糖皮質激素激素治療(每日劑量大于等于強的松當量10 mg,治療時間大于等于12個月);胸腰段骨折定義為首次骨折部位在胸10至腰2節段;為了區分骨質疏松癥的嚴重程度,本研究將骨密度測定中,椎體(L1-L4)T值≤-3.0 SD的病例分開,使用第一次骨質疏松性椎體骨折時測定的骨密度,將T值≤-3.0 SD定義為嚴重骨質疏松。
1.3 統計學分析
先對患者數據進行描述性分析,其中連續變量采用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形式,分類變量統計其百分比。為了確定各種風險因素和椎體級聯骨折是否存在關系,采用非參數檢驗對連續變量進行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顧模型分析分類變量風險因素。對單因素分析中P<0.1的變量進行多因素分析以評估危險因素。P<0.05則認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統計分析使用SPSS 25.0版本。
2 結果
2.1 椎體骨折級聯發生的風險因素特點
在非椎體骨折級聯組,共有308例患者,其中女性有231例(75.0%),年齡(77.58±9.07)歲,既往有糖尿病史的有53例(17.2%),曾口服激素治療史的有72例(23.4%),有COPD病史的26例(8.4%),骨折部位發生在胸腰段的共185例(60.1%),T值≤-3.0的有116例(37.7%),BMI≥28 kg/m2的有116例(37.7%)。在椎體級聯骨折組的患者中,有108例(79.4%)女性,既往有糖尿病史的有33例(24.3%),曾有口服激素治療史的有46例(33.8%),有COPD病史的20例(14.7%),骨折部位發生在胸腰段的有109例(80.1%),T值≤-3.0的有63例(46.3%),BMI≥28 kg/m2的有63例(46.3%)。
2.2 各類風險因素對椎體骨折級聯發生的影響
如表1所示,在單因素分析中,椎體骨折級聯的危險因素包括既往有糖尿病史(P=0.084)、既往口服糖皮質激素治療史(P=0.022)、患有COPD(P=0.048)、骨折發生在胸腰段(P<0.001)、嚴重骨質疏松(T值≤-3.0)(P=0.087)、BMI≥28 kg/m2(P=0.012)。采用非參數檢驗對年齡進行分析,說明兩組間無明顯差異(P=0.506)。且性別在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14)。多因素風險分析中,椎體骨折級聯的風險因素包括有糖尿病史(風險比為1.689,P=0.047)、既往口服糖皮質激素治療史(風險比為1.839,P=0.010)、患有COPD(風險比為2.103,P=0.026)、骨折發生在胸腰段(風險比為2.686,P<0.001)、BMI≥28 kg/m2(風險比為1.769,P=0.010)。見表2。

表1 單因素分析中椎體骨折級聯的危險因素

表2 多因素分析中椎體骨折級聯的危險因素
3 討論
本研究在多因素分析的危險因素評估中,有糖尿病史、既往口服糖皮質激素治療史、患有COPD、骨折發生在胸腰段、BMI≥28 kg/m2確定為骨質疏松性椎體級聯骨折的危險因素,重骨質疏松在多因素分析中不顯著。
在之前的觀念中,認為肥胖對骨折具有保護作用,因為肥胖會導致更高的BMD以及跌倒時軟組織填充的保護作用。然而,最近的研究正在挑戰肥胖對所有骨折都有保護作用的概念[5-7]。Paik等[8]研究表明,低體重與更低的椎體骨折獨立相關。腰圍越大,椎體骨折的風險越高。一項薈萃分析表明,在調整BMD后,較高的BMI與女性脊椎骨折風險顯著增加相關[9]。這些發現表明,脂肪分布是VFC的一個重要預測因子,避免中樞性肥胖以及保持肌肉質量可能會降低老年女性患VFC的風險。本研究中,BMI≥28 kg/m2無論在單因素風險分析還是多因素風險分析中,均為VFC的顯著風險因素,這與上述各報道結論部分一致。本研究沒有單獨分析在不同性別中BMI與VFC發生的相關性,且本研究數據中女性個體約占總樣本的3/4,故結果可能具有一定的偏差,之后的研究可以更進一步。
一些研究發現,T1DM患者的面骨密度和體積骨密度均顯著低于非糖尿病患者。相反,T2DM患者則均高于對照組。盡管T1DM和T2DM的BMD存在差異,但大型病例對照研究、系統評價和薈萃分析表明,這兩種類型的糖尿病都與骨折風險增加有關[10-11]。Ha等[12]一項對6 548 784名韓國受試者進行的大規模、縱向、基于人群的隊列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的骨折風險高于非糖尿病受試者。在T1DM中,骨質疏松可能由于成骨細胞活性缺陷、胰島素對骨骼合成代謝作用的缺失、骨-胰腺負反饋回路的去調節以及高血糖導致骨基質內晚期糖基化終產物(AGE)聚集,從而導致骨密度降低[13]。在T2DM中,與肥胖相關的脂肪因子和炎癥因子的作用以及胰島素和IFG-1升高引起的合成代謝效應可能導致骨量增加,但骨小梁評分(TBS)降低。TBS是T2DM患者骨小梁質量惡化的標志,已被認為有助于糖尿病患者骨折風險評估[14-15]。Koromani等[16]研究表明,T2DM患者與非T2DM患者相比,其股骨頸和腰椎的BMD較高,但TBS較低,這與年齡、性別、藥物使用和BMI無關。Yamamoto等[17]的研究也表明,在2型糖尿病患者和由各種病因(包括1型糖尿病和類固醇治療)引起的糖尿病人群中,TBS降低與椎體骨折風險增加之間存在關聯。本研究中,既往有糖尿病史在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中均定為VFC的危險因素。說明在VFC發生過程中,患有糖尿病是VFC的獨立風險因素。本研究由于數據統計有限,僅統計所有患者是否患有糖尿病,并沒有進一步研究糖尿病的類型對VFC發生的影響,之后的研究可以對此進行進一步研究。
COPD和骨質疏松癥有一些共同的危險因素,如吸煙、體重低、營養不良和缺乏運動。慢性阻塞性肺病骨量丟失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很可能是多因素造成的,包括女性性別、皮質類固醇的使用、性腺功能減退、吸煙、缺乏運動、維生素D缺乏和慢性炎癥[18-19]。本研究中,COPD為VFC的獨立風險因素。之前的研究中,COPD可能與骨質疏松、跌倒高風險相關。在Gazzotti等[18]的研究中,COPD組骨質疏松癥的發生率為29.7%,對照組為18.3%。COPD組椎體骨折發生率為18.6%,對照組為9.0%,導致骨折的跌倒頻率分別為36.3%和7.3%。在Adas-Okuma等[20]的研究中,與對照組相比,患有COPD的受試者的BMD較低,骨質疏松癥的幾率增加了2.6倍。骨折的幾率也比對照組個體高出近5倍。發生椎體骨折且既往患有COPD的患者,應高度重視其再次發生椎體骨折。
本研究在單因素和多因素風險分析中,骨折發生在胸腰段均為VFC發生的顯著風險因素。更重要的是,骨折發生在胸腰段(T10~L2)是發生新椎體骨折的最重要的危險因素(風險比為2.686,P<0.001)。發生在胸腰段的骨質疏松性椎體骨折可導致胸部和腰部的后凸畸形。脊柱后凸度增加與脊柱骨盆參數惡化相關,即導致矢狀面不平衡。進而患者的重心向前移動,行走時身體前傾,行走困難。因此,骨盆(包括脊柱)向后旋轉以移動重心。在這個過程中,椎體前柱受力過大,會增加壓縮性骨折的可能性[21]。在胸腰段椎體發生骨質疏松性椎體骨折后,其他椎體的彎曲力矩會隨著整體矢狀線的改變而改變。更高的扭矩可能與更高的椎體負荷以及隨之而來的骨折風險增加有關[22]。Langella等[23]研究表明,脊柱對中不良與胸腰椎連接椎體骨折以及缺乏強有力的代償機制(如胸椎后凸降低和下腰椎前凸過度)密切相關,從而導致椎體骨折級聯的發生。對于椎體骨折發生在T10~L2的患者,要高度警惕該區域內骨折的再次發生。
BMD降低是骨質疏松的一個重要表現,同時絕大多數發生椎體骨折的病人其BMD都是降低的。在單因素分析中,嚴重骨質疏松被確定為一個重要的危險因素,而在多因素分析中沒有,說明在危險因素之間的補償過程中,其他因素在骨折的發展中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
長期糖皮質激素(glucocorticoid,GCs)治療是骨質疏松性骨折的主要危險因素,也是繼發性骨質疏松癥的最常見原因。GCs對骨脆性的影響主要通過其對成骨細胞、骨細胞和破骨細胞的直接影響來實現[24]。GCs誘導的骨質疏松癥的骨丟失是雙向的,第一年內BMD降低6%~12%,隨后每年約3%的骨丟失較慢。在GCs治療開始后的前3個月內,骨折風險迅速增加[25-26]。在本研究中,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為VFC發生的獨立風險因素,在之前的報道中也有相同的結果。在Koh等[27]的研究中,1 896 159例受試者經過2年的隨訪過程中,共有4 793例(0.25%)出現骨折,包括3 988例脊椎骨折和880例髖部骨折。與非使用者組相比,低劑量組、中等劑量組、高劑量組的脊椎骨折風險分別高出1.39倍、2.43倍和1.94倍。GCs使用的劑量、頻率、持續時間以及用藥方式等可能導致椎體骨折風險不同程度的增加[28-29],之后的研究可以從這些方面進行。
4 結論
本研究表明,有糖尿病史、既往口服糖皮質激素治療史、患有COPD、骨折發生在胸腰段(T10~L2)、BMI≥28 kg/m2被確定為椎體骨折級聯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中骨折發生在胸腰段(T10~L2)被確定為發生新椎體骨折的最重要的危險因素。醫生在臨床工作中對首次發生骨質疏松性椎體骨折進行診治時,需要更多地關注患者是否有發生VFC的風險因素,以確保更多的患者及時得到干預,從而減少后續骨折的發生。此外,通過了解VFC患者的骨折風險因素,醫生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和定制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