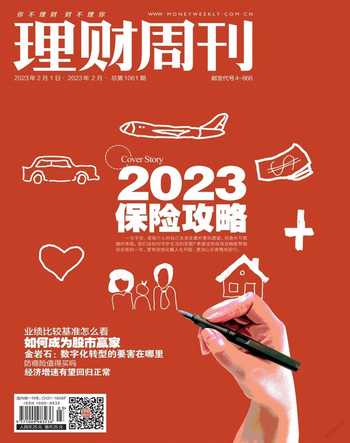異地夫妻怎樣實現團圓夢
王力 魯婕


30歲的史小姐與丈夫分居已3年有余,育有一女的他們雖然已習慣于分居生活,但也感到再這樣下去,感情會變淡,對孩子也絕對不是件好事。史小姐憂愁地說:“所以我們真的很想找個辦法,看看是否能保證我們一家團圓,又不過多影響事業發展。”
史小姐與丈夫蔡先生青梅竹馬,憑借自己的努力,一起從家鄉唐山考入了上海的大學,分別攻讀語言與生物工程專業。畢業后,重回故鄉的史小姐尋得了一份令家人與自己都非常滿意的工作——中學英語教師;而蔡先生選擇了出國留學,進一步深耕自己的專業,直到獲得碩士學位后,才回到家鄉與史小姐團聚。
“他回來之后我們就結了婚,1年后,也就是2018年,我們的女兒蹲蹲出生了。”史小姐回憶道,“因為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且我的工作也比較穩定,所以即便有了蹲蹲,生活壓力也不算大。不過,我丈夫那時是比較‘痛苦’的。”
在史小姐與蔡先生所生活的城市,生物工程并沒有太多的工作機會,即便蔡先生依舊從事的是相關工作,但他還是覺得體現不出自己的價值,沒法實現自己的職業抱負,收入也與預期完全不符。史小姐說:“在幾次討論之后,我們一家最終決定,還是應該讓他去上海,尋找更好的機遇和發展。”
2019年,史小姐一家的“雙城記”正式拉開帷幕:史小姐與孩子留在唐山,蔡先生則前往上海打拼奮斗。
到上海后,蔡先生的學歷與專業知識很快就讓他找到了一份雖然忙碌卻令他滿足的工作。“感覺他心情都變好了,用一句肉麻的話來說,一切都是充滿希望的樣子。”史小姐笑著說,“盡管日常開銷變大了,但他賺得也更多了,每個月打給蹲蹲的生活費比他留在唐山時多。”
只要沒有特殊情況,史小姐和蹲蹲每晚都會與蔡先生一起視頻通話,到了春節或蔡先生有假期的時候,他也會趕回老家與家人團聚。然而,時日一長,許多原本被兩人所忽略的問題也隨之而來。
首當其沖的,便是孩子對父母的情感需求。由于疫情的反復以及相應的防控措施,蔡先生已有1年多沒有回家了,錯過了孩子整個幼兒園階段。“孩子經常問我,為什么爸爸一直不在家、不來陪我玩呢?雖然每晚都會視頻,但父親不在身邊,總會讓孩子有缺失感。”史小姐無奈地說。
除了孩子的情感需求外,夫妻雙方長期分居也可能導致情感淡漠,讓兩人必須重新審視當下的生活狀態。“思來想去,我們還是決定由我帶著蹲蹲,去和我丈夫一起生活。”史小姐說,“正好孩子也要上小學了,上海的教育資源對孩子來說也更加理想。”
然而,一家人的團圓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
首先,他們遇到的是資金問題。無論是蔡先生還是史小姐,在上海都沒有根基。蔡先生單獨打拼的3年多時間里,也是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一室戶住,每月租金約為4500元。
蔡先生目前的月薪為稅后1.6萬元,去除租房及生活開銷,每月結余約為8500元,其中的5500元會作為蹲蹲的生活費,而剩下的3000元則一般會被蔡先生存起來用作不時之需。而史小姐的稅后收入則在5000元左右。“如果我們一家要在上海生活,我們在住房上的支出會增加,光靠先生的收入肯定是不夠的。”史小姐說。
史小姐與蔡先生在老家有一套婚房,目前出租,為了更好地在上海立足,史小姐考慮是否應將婚房出售,并在上海購買一套房產。“那套婚房大約值110萬元,我倆的存款加在一起差不多是40萬元,因為我丈夫在上海還沒繳滿5年社保,我們還有2年才能獲得購房資格。不過我們也沒覺得有什么不好,正好能讓我們再攢攢,這段時間租房應付就行,等到可以買房的時候,首付款應該就足夠了。”史小姐這樣盤算道。
“問題在于,除非求助父母,否則那時我倆很可能就‘傾家蕩產’,把家庭所有的資產都用來付首付款了,但到時蹲蹲又上小學了,支出肯定也不會少,所以我們很矛盾,到底要不要買房?或者就這么一直租房算了?”
其次,是史小姐的工作問題。史小姐目前的選擇有二:一是在上海尋找一份英語教師相關的工作。她說“:教師工作相對穩定,寒暑假也有更多時間來帶孩子,但我作為三線城市的英語老師,在一線城市可能會競爭力不足,需要進一步深造。另外,我也考慮到教師收入不是特別高,所以我很猶豫。”
史小姐的第二個意向是找個翻譯公司的工作,這樣的話,收入相較教師會高些,但問題在于工作會比較忙。因為他倆的父母還沒有退休,也不會跟著他們一起來上海,所以他們不可避免地需要請阿姨來帶孩子。
最后,就是父母的養老問題。考慮到未來,史小姐與蔡先生預計會長時間生活在上海,雙方父母則會留在老家。雖然小城市的日常花銷不大,但因為以后他們會長期不在父母身邊,在生活照顧上肯定會有欠缺。史小姐擔憂道:“特別是遇上生病住院的情況,他們除了醫保也沒什么別的保險,所以我們還想要留出一些錢,以備父母急用。”
期望一家人團圓,但又不得不面對現實問題,史小姐說:“所以我很想知道,像我們這樣的情況,有沒有辦法通過理財來實現我們的心愿,給我們一家團聚的生活增添一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