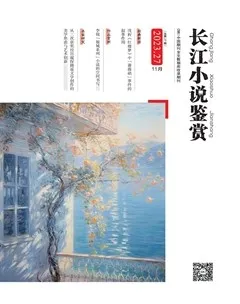論精神創傷及其修復
[摘? 要] 心理學中的精神分析法在文學界已具有公認的共通點和可比性。從作家的文化背景和小說文本呈現來看,茨威格的創作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并表現在文學作品中。《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是他心理描寫的代表作,文本以C夫人為中心,用獨具風格的大量心理描寫回憶了她年輕時情難自控的逸事。小說模擬再現了人的心理結構和癥候的治療過程。茨威格作為舉世聞名的短篇小說家,以文學作品展示了人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研究小說文本中出現的心理學表現,包括人物心理的矛盾、矛盾原因以及如何解決矛盾,可以更好地理解茨威格的藝術創作特色并進行文本的多維度解讀。
[關鍵詞] 茨威格? 《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 跨學科? 精神分析? 創傷修復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27-0053-04
一、引言
茨威格在20世紀初的創作十分活躍,其作品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茨威格對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學說充滿尊重和崇敬,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對弗洛伊德的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描述了人的心理結構,包括意識、潛意識和無意識三個層次,其中潛意識是一切心理活動存在和活動的基礎。茨威格對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有著獨特而深刻的理解,他部分借鑒并運用這些學說于自己的小說創作中,形成了獨特的心理現實主義風格。茨威格的心理現實主義風格在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下與傳統的心理描寫有所不同,表現出現代性的特征。心理現實主義注重揭示人物心理的復雜性和層次性,茨威格在描寫人物多層次的心理活動時著重描述了人物的性本能、欲望和無意識沖動以及相應的行為。在《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中,作者細膩地描寫了C夫人年輕時的女性意識流露。茨威格的心理現實主義通過心理分析來間接反映社會現實,《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反映了傳統封閉的社會環境對性的壓抑以及對女性的道德苛求。心理現實主義受精神分析的影響,關注人性的本能,關注社會現實和道德倫理,以分析人性問題為核心。因此,從精神分析學說的角度來解讀茨威格的作品是十分恰當的。
《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是茨威格的代表作之一,文本以C夫人為中心,通過獨特的風格和大量的心理描寫,回憶了她年輕時情難自控的逸事。C夫人的回憶展示了被壓抑的潛意識部分,在持續的抵抗后產生了病態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受到道德譴責的醫患之間的治療過程。本文通過分析C夫人具體的心理矛盾以及她如何實現創傷治療,驗證了精神分析對于創傷修復的有效性,并探究了作品中心理問題的現實意義。
二、癥候產生:C夫人二元失衡的心理矛盾
弗洛伊德將人的心理結構分為意識和潛意識,其中意識與外部世界聯系緊密,受理性的限制。神經癥的產生與潛意識和意識的內部心理沖突有關,形成神經癥的原因在于其無法應對一個強烈的情緒體驗[1]。在茨威格的作品《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中,C夫人在短暫的二十四小時內與一位年輕男子發生了一夜情,她渴望追求愛情卻遭到拋棄。此后漫長的歲月中,C夫人一直執著于那段經歷,并承認其對自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心理癥狀是自我與被壓抑的分裂部分之間對立的結果。弗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中認為,從分析實踐的角度來看,要追溯神經癥根源于意識和潛意識是困難的。因此,我們可以選擇一種具體的對立,即清晰現實的自我與被壓抑的分裂部分之間的對立來取代意識與潛意識的沖突[2]。對于神經癥的癥候分析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執著事件發生的動機、目的;執著事件發生的過程、心理背景;推知更重要的心理歷程。
首先確定C夫人的創傷情景,她作為體面的貴族夫人,受激情吸引與沉迷賭博的青年發生一夜情,事后被賭博青年欺騙并拋棄。創傷情景產生于C夫人的意識與被壓抑部分的潛意識之間的沖突。C夫人的生活始終處于受意識指導的體面生活與道德克制中,包括從小的生活環境、青年的婚戀經歷以及中年時期的婚姻生活,C夫人的前半生始終處于理性意識的指導之下。然而從意識結構來看,潛意識中非理性對激情的渴望始終存在,但受到意識的壓抑。雖然此時這種壓抑并沒有進入意識層,自我無所知,但抗拒始終存在,因此意識與潛意識在無意狀態中處于一種失衡狀態。小說中,C夫人在沒遇到賭博男子之前就傾向在賭場中看極具二元性的“輪盤戲”,在綠呢賭臺上,黑或紅、偶或奇、贏或輸、幸運或毀滅,全都壓縮到輪盤滾動的一瞬間。這種輪盤戲與C夫人平日里四平八穩的生活完全對立,刺激C夫人的正是這種機緣巧合下與個人命運完全相反的激情。C夫人的潛意識始終存在,并渴望這種非生即死的激情,只是這種潛意識長期處于一種被抗拒中,她注定不可控地被富有激情的青年人吸引。C夫人癥候的產生目的在于解決長久以來形成的精神矛盾,她形成這種執著的創傷情景在當時可以免去精神上持久被壓抑的痛苦,用著魔般的獻身緩解當時的精神空虛和寂寞,這種飛蛾撲火般的獻身反映了當時C夫人潛意識和意識矛盾之間的不和調和。
然而事物與感情的發展走向非人力可以控制。C夫人用以平復意識與潛意識矛盾的激情發泄最后卻造成了更嚴重的自我斷裂。從精神分析來看,自我是個體對其存在狀態的認知,包括對自己的生理狀態、心理狀態、社會角色的認知,追求完整連貫性、內在一致性和復雜性。由于自我是個體社會化的結果,作為自我認知范疇之一的身份是自我投射的面具[3]。人存于世以復雜多元或變動不居的身份來確定、展示、規范自我。對《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中的C夫人來說,這二十四小時發生的事,造成了自我身份認知的斷裂。作為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身份高貴的婦人,她是“天使”,她不應該在孀居期間對身份低微的年輕賭徒產生激情,并與對方發生一夜情,甚至準備放棄一切與之私奔。種種想法和行為對于她的家庭和社會角色來說是一種禁忌。這二十四小時發生的相遇、一夜情、私奔未遂被親戚發現等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主體意識的斷裂。
三、癥候修復:C夫人與“我”的移情對話
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癥療愈在于解決力比多與自我的矛盾。治療的工作在于解放力比多,使其擺脫先前的迷戀物。神經癥患者的力比多依附在癥候之上,要想消滅癥候就必須追溯癥候產生的出發點,將矛盾引入到一個新的場所再想法解決。凡屬力比多與力比多相反抗的力量都集中在一點,就是病人與醫生的關系,因此,解決的關鍵在于病人與醫生的移情作用。文中C夫人與“我”的交流模擬了醫生與病人的治療過程,C夫人在移情作用下,通過四場層層深入的對抗模擬,看到了自身的心理矛盾可以獲得被理解、被修復的可能性。
從C夫人的實際經歷和處境來看,她應當是同情昂立艾特太太的一方。然而她與“我”交流時卻站在對立面駁斥昂立艾特太太的行為,并反常地在神態和細節上泄露出對于“我”堅持支持昂立艾特太太的贊賞和欣慰。文中集中出現了產生移情作用的四場模擬。首先,C夫人認為從道德和法律層面來說,昂立艾特太太應當為自己沖動的行為負責,因為她違背了作為上層社會體面貴婦人的社會角色,犯了“激情罪”,而“我”對于昂立艾特太太無罪“堅信不疑”。其次,C夫人又從社會責任的角度指責昂立艾特太太對自己的家庭和兒女不負責任,有違妻子和母親的家庭角色,這種行為在她的口中是不知檢點的,而“我”仍然堅持己見,再次重申昂立艾特太太的行為是真誠的。再次,C夫人又試探了斷裂修復的可能性,“您自己,您到現在還對她懷有同樣的敬意和尊重嗎?一個是前天還和您在一起的那個值得尊敬的女人,另一個是昨天跟素昧平生的男人離家出走的女人,對這兩個女人,您完全會不加區別嗎?”[3]由此可見,經過“我”始終堅定的回答,已經讓C夫人放下戒備,試圖尋求斷裂修復的可能。在這第三場詢問中,C夫人對昂立艾特的質疑同樣適于自己,她終于問出自己的內心訴求:跟陌生男人離家出走的女人是否可以再次獲得之前體面女人同等的尊敬和評價——斷裂的身份認知是否有修復的可能?“沒有區別。毫無區別,一點區別都沒有”,“我”又給出了無比堅定的肯定。最后,C夫人從具體的社會關系角度出發,詢問現實生活場景出現的可能性。這時候C夫人的預設都是積極地指向“是否會向她問好”“是否會把她介紹給您的太太”[3]。從道德的要求、法律的制裁、責任的要求,最后具體到與其生活息息相關的人際交往,由大到小、由遠及近,C夫人扮演的現實阻礙在一次次“潰敗中”看到修復斷裂自我的可能性。C夫人最后的積極場景預設展示了她在移情作用中獲得了積極的暗示,在看到修復的可能性之后,C夫人內心的抗拒開始松動,主動尋求對“我”追述她的往事,使自我斷裂的創傷癥候在意識層面出現解決和治愈的可能。
C夫人在之后的敘事過程中逐漸以更真實的態度面對自身,包括承認從不敢說出口的二十四小時內對于年輕男子的期待與愛戀、自己內心深處的道德譴責。C夫人將自己難以啟齒的事件暴露,并賦予合理的解釋和連貫的自我構建,消除了創傷癥候 ,獲得了真正完全優雅的體面自我。“不,您什么也別說……我不想要您給我什么回答或者對我說什么……我感謝您認真地聽我說話,祝您一路平安。”[3]在敘述之前,C夫人用連續的移情對抗期待“我”堅定的支持,從“我”的回答中獲得她直面自我的勇氣。在敘述之后,C夫人通過藝術性升華完成了創傷療愈,她已經不再需要“我”的任何回應。從此對這段往事的回憶再也不是C夫人的夢魘,而升華成一段可以釋懷的、重回青春的禁忌之戀。
四、癥候消除:C夫人愛情的藝術性升華
精神分析理論認為作家的文學創作以一種藝術性升華緩解了心理矛盾。他們也受本能的欲望驅使同時缺乏滿足的手段,需要用構成的幻念轉移失衡的力比多。敘事心理學從人格發展與整合的角度認為自傳敘事具有癥候價值,自傳者追求內在一致的、平衡的生命故事[4]。在這個過程中,經歷過心理創傷的生命故事能夠表現出他們使用了哪種防衛機制,使用什么方法來詳述創傷情景,以及在詳述創傷事件中所處的自我狀態。弗洛伊德強調了藝術性創作中虛構對于欲望的補償作用。C夫人的往事在內容上從自我意識衡量來看是一種不體面的過往,在形式上又有超出人體記憶極限的連貫性,因此C夫人對于往事的回憶呈現出“不可靠敘述”的虛構特征,發揮了藝術敘事的治療性功能。
C夫人回憶創傷情景的過程中在防衛機制的作用下出現了否認、重新體驗、過度敘事的現象。首先,C夫人在回憶敘事中反復出現否認的現象:“我已經六十歲,對流言蜚語已無所畏懼”“不要認為我有別的動機”“我根本沒有想過和這個陌生人會有……會有什么關系……”[3]C夫人的否認內容主要分為自我對拯救動機的否認以及對創傷事實的否認,她否認自己對賭博的青年男子有除了拯救以外的動機,否認這段往事對自己有無法解決的道德負擔和心理困擾。C夫人的否認本質上是一種敘事而不是隱瞞,弗洛伊德也提出否認在某種方式上是對被壓抑內容的明智接受。因此,這種否認在時間推移的幾次重復后獲得了療愈效果。“今天,我才清楚地知道:當時使我痛苦的是……他僅僅把我當作一個在他生活道路上出現的圣女來表示尊敬而沒有感覺到我是一個女人。”[3]C夫人最后承認了自己對于賭博的青年男子有除了拯救動機以外的性需求,并且他的欺騙和拋棄令自己非常受傷,耿耿于懷。不僅如此,這種否認技巧直接表現出C夫人富有道德且真誠的人物形象。其次,重新體驗指創傷情景的產生對于個體在將來的生活中對人際關系的看法和人際事件意義的生成產生重要作用,使個體在經受心理創傷時,將自己的體驗轉移到真實的生活情景中。C夫人的回憶敘事早在先前對“我”對話時就已經開始,文中C夫人與“我”對話的移情現象就是一種重新體驗現象。昂立艾特太太的事件與C夫人在之前二十四小時內發生的事件性質相同。由于曾經的創傷情景影響到C夫人對于社會道德和人際關系的看法,此時的C夫人即使可以感同身受,支持昂立艾特太太的行為,但是她更知道孤立無援受道德譴責不被理解的痛苦,于是她將自己受過的社會評價和道德譴責轉移到當下發生的類似事件中。這是一種創傷后尋求認同的試探求助,也是利用當下道德評價機制的形象塑造。最后,C夫人的回憶出現了過度敘事現象,這種記憶類型的特點是控制敘述的自我反思。在回憶遇到賭博的青年男子時,她無法接受自己著魔似的飛蛾撲火,“我身不由己地跟著他,我自己并不愿意這么做”[3];與青年男子發生關系后,她無法控制地產生厭棄自己的情緒,“我感到惡心、羞愧、只求一死”[3];在被拋棄,私奔未成后,她自慚形穢,覺得無法接受親人們的好意,“但是他們的柔情使我痛苦,我羞于接受他們的敬畏”[3]。在回憶過程中,類似這種無法控制的反思和解釋數不勝數。這些過度敘事體現了C夫人應對心理創傷的困難,也反映出她曾經難以面對的創傷情景正逐漸擺脫束縛,被個體重新回憶、面對、修復、塑造、認同。
C夫人在整個回憶敘事過程中,在防御機制下利用妥協的敘事方法,包括否認、重新體驗、過度敘事的方法逐步展開真實的自我,在事后回顧的過程中修復和塑造自我,使自我認同得到恢復。隨著時間的流逝,當下回憶過往的C夫人已經不再有當時的性沖動。因此,C夫人在回溯過程中,用富有藝術性的敘事塑造了矛盾又富有獻身、救贖精神的自己,在整個自我上修復了道德斷裂的二十四小時,連貫起自己一生體面、富有道德感的自我。
五、結語
茨威格在《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中用C夫人的回憶敘事呈現了一場癥候消除、修復自我的心理治療過程。在這場模擬中,C夫人逐漸展示出更真實的女性形象,包括她內心的矛盾、禁忌的欲望和道德的制約。這場成功的治療,賦予了C夫人光輝體面的形象,展現了人豐富復雜的心理圖景。不僅如此,這場治療在現實意義上同時具有反諷的效果。精神分析學說認為沖動與情欲是人的自然心理。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念和倫理規范認為理性是一切沖突的解決辦法,對人的自然性欲在道德規范上避而不談。在兩性地位懸殊的時代背景下,這種社會規約和倫理習俗對女性有著更嚴苛的要求,給女性心理帶來了嚴重壓抑。因此,從精神分析學說的角度可知,封閉壓抑的環境與女性自然需求的矛盾造成了C夫人的心理失衡。在《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中,茨威格以科學客觀的態度和人道主義精神,創造出復雜的C夫人形象,展現出他對人精神世界的關注與探索,以及對現實世界中女性群體的理解與包容。
參考文獻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2] 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M].林塵,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3] 茨威格.象棋的故事[M].張玉書,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4] 拉斯洛.故事的科學:敘述心理學導論[M].鄭劍虹,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責任編輯 羅 芳)
作者簡介:朱孟佳,西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