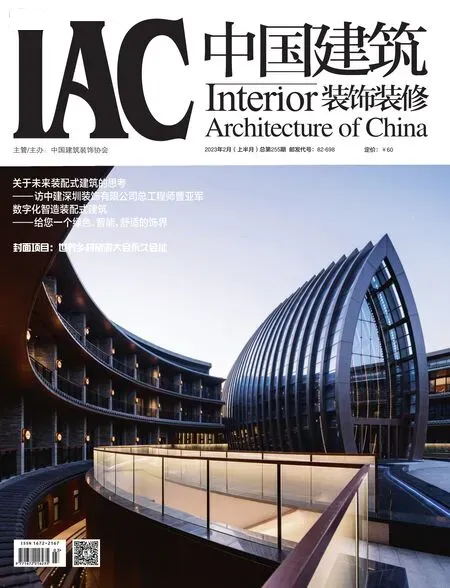基探于索地方重塑的鄉(xiāng)村設(shè)計方法創(chuàng)新與實踐
——以上海三個實踐案例為例
霍 瑜 蔣亞娜
作者簡介:霍瑜,女,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博士在讀,注冊規(guī)劃師、高級工程師;[通信作者]蔣亞娜,女,理想空間(上海)創(chuàng)意設(shè)計有限公司主創(chuàng)建筑師,注冊建筑師、工程師。
鄉(xiāng)村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被長期忽視,出現(xiàn)基礎(chǔ)設(shè)施陳舊、空心村嚴重的現(xiàn)象。近年來,在各地政策的推動下,鄉(xiāng)村基礎(chǔ)設(shè)施、風貌環(huán)境得到顯著改善,但同時也出現(xiàn)了鄉(xiāng)村“城市化”、風貌“同質(zhì)化”、產(chǎn)業(yè)“空心化”等現(xiàn)象。一方面,村民缺乏傳統(tǒng)村落風貌保護意識,存在盲目崇拜城市生活的心理,急于求新求變;另一方面,鄉(xiāng)村建設(shè)大多迫于時間壓力,未能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照搬了城市風貌建設(shè)的經(jīng)驗,造成“千村一面”的現(xiàn)象。
浙江省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江蘇省的“特色田園鄉(xiāng)村建設(shè)行動”、廣東省的“嶺南秀美農(nóng)村”、上海市的“鄉(xiāng)村振興示范村”等鄉(xiāng)建運動都是對2018 年國家新一輪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回應(yīng)。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輪鄉(xiāng)村工作的重點落到了“產(chǎn)業(yè)興旺”和“文化振興”上。飽受詬病的“千村一面”,其本質(zhì)原因在于未能形成良好的地方特色和地方感,加之現(xiàn)代社會信息碰撞、文化融合,地域文化正在逐漸消失。因此,如何挖掘地方文化,營造地方感是當下鄉(xiāng)村營建中亟需解決的問題。本文從實用性出發(fā)運用地方理論研究鄉(xiāng)村地方性,結(jié)合3個實踐案例,提出基于實用性且符合我國鄉(xiāng)村實際的地方重塑思路與方法。
1 地方理論
1.1 地方性與地方性建構(gòu)
地方理論萌芽于20 世紀50 年代,在20 世紀70 年代,以段義孚為代表的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率先意識到地方不止是一個物質(zhì)形態(tài),還包含了人與地方產(chǎn)生的特定情感與其他復(fù)雜關(guān)聯(lián),并發(fā)展成為人文地理學中“人——地”關(guān)系的重要內(nèi)容[1]。人文主義學者的研究衍生出了地方感、地方依戀、地方認同等概念,結(jié)構(gòu)主義學者則更關(guān)注資本、權(quán)力、政策、經(jīng)濟行為和制度等因素對地方性的影響與建構(gòu),也有學者綜合兩大理論,認為地方是由區(qū)位、場所和地方感所構(gòu)成。
在地方性建構(gòu)研究方面,人文主義與結(jié)構(gòu)主義也有著不同的觀點。人文主義認為地方性建構(gòu)源于地方物質(zhì)空間、人地情感、行為活動構(gòu)成;結(jié)構(gòu)主義認為地方性是在復(fù)雜社會關(guān)系互動中產(chǎn)生的動態(tài)過程。基于人文主義視角,國內(nèi)學者將研究對象集中在歷史文化街區(qū)、老城區(qū)菜市場、傳統(tǒng)村落、城中村及古鎮(zhèn)等;結(jié)構(gòu)主義的研究關(guān)注資本、權(quán)力和政策在建構(gòu)地方性中的作用,譬如以三里屯為例研究地方性建構(gòu)中的社會結(jié)構(gòu)與個體行動、國家政策制度和現(xiàn)代化對民族村寨地方性建構(gòu)的影響、本土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中地方性的嵌入與重構(gòu)。
1.2 地方性設(shè)計方法
地方性設(shè)計也稱為地域性設(shè)計,近年來一些城鄉(xiāng)規(guī)劃、建筑及景觀領(lǐng)域的學者也在嘗試總結(jié)地方性設(shè)計方法。這類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基于理論研究的宏觀指導原則,譬如張彤提出了地域性建筑設(shè)計的原則[2];二是基于實踐案例的微觀設(shè)計手法,譬如林箐等人以國外景觀實踐案例,解析設(shè)計形式如何取材于地域特征[3]。宏觀理論原則不足以指導具體實踐操作,導致最終設(shè)計內(nèi)容零散化、堆砌化現(xiàn)象普遍,具體設(shè)計手法表征化、粗淺化、符號化明顯[4]。
依據(jù)哈維的說法,“地方既是與資本合謀又是抵抗的場所”。地方性重構(gòu)的任務(wù)就是要在全球化進程中,化解鄉(xiāng)村“城市化”、風貌“同質(zhì)化”、產(chǎn)業(yè)“空心化”等危機。本文基于以上實踐中存在的普遍問題,從實踐訴求入手,結(jié)合案例提出具有實用性的鄉(xiāng)村地方性重構(gòu)的方法及路徑。
2 重塑地方性的方法探索
2.1 基于集體記憶的地方重塑——以上海市浦東新區(qū)萬祥鎮(zhèn)新振村為例
2.1.1 集體記憶的斷裂與修復(fù)
鄉(xiāng)村文化是一種在特定的歷史、地理、經(jīng)濟和政治環(huán)境下,形成于人們長期以來的生活觀念、習俗和方式。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學術(shù)界首次提出“集體記憶”的概念,認為集體記憶是同一群體對過往事件的集體建構(gòu)[5]。
鄉(xiāng)村記憶是村落起源、變遷和發(fā)展過程中依托各種地理媒介、符號和載體所涵蓋的記憶,不僅包含主體對鄉(xiāng)村風光、歷史建筑、文化遺產(chǎn)、風俗民情等自然與人文地理要素的歷史記憶,更強調(diào)記憶過程中呈現(xiàn)出的社會環(huán)境因素和空間映射。然而大都市鄉(xiāng)村地區(qū),受全球化與城市化的影響,鄉(xiāng)村記憶正在快速的消失。
新振村在美麗鄉(xiāng)村創(chuàng)建工作中強調(diào)重拾鄉(xiāng)村記憶,秉承“地方重塑”的核心價值,在規(guī)劃設(shè)計前期,采用深度訪談形式,圍繞語言、文本、景觀3 個要素與村里多位80 歲以上老人多次交流。第一,以口頭語言為主要媒介的記憶傳承與擴散,通過俗語諺語、歷史故事為載體的口頭語言體現(xiàn)了當?shù)厝宋奶厣瑑Υ娴胤接洃洠坏诙晕谋拘问綖橹饕挠洃涊d體,主要以村史、鎮(zhèn)志為代表的文本較為完整地記載了“新鎮(zhèn)”集市的店鋪種類和位置布局,印證了新振村“先市后村”的形成過程;第三,以景觀標志物或重要建筑為主要符號的記憶承載。
由于鄉(xiāng)村田園風光和代表性符號建筑具有明顯的識別性與獨特的符號性,因此,在鄉(xiāng)村集體記憶中往往具有穩(wěn)定性和持久性。通過多次深度訪談,激發(fā)了老年人之間的相互交流,修復(fù)了村民集體的記憶,最終確定了本次美麗鄉(xiāng)村設(shè)計圍繞著再現(xiàn)“新鎮(zhèn)集市”的愿景,以場景再現(xiàn)和商業(yè)復(fù)興的形式重構(gòu)鄉(xiāng)村地方性。
2.1.2 地方性的表征
表征與非表征是地理學學者研究時常用的兩種分析工具[6]。表征手法是運用相關(guān)素材,通過文本、圖像展示地方意義事件過程,關(guān)注元素、符號與情景,更為日常的、實踐的、具體的;非表征手法認為需要地方意義由直接、即時、動態(tài)的空間體驗生產(chǎn),強調(diào)文化符號與實踐情景的再物質(zhì)化。
新振村地方重塑的表征手法是通過文本和圖像建構(gòu)的景觀意象,提煉村民集體記憶中的“新鎮(zhèn)集市”的景觀標志物、重要建筑、各類店鋪等意象,對這些鄉(xiāng)土景觀有深刻的認識和把握;分析蘊含地方特性的意識、觀念、歷史、文化及社會關(guān)系素材,并以文化墻的形式呈現(xiàn)“新鎮(zhèn)集市”的景象,建構(gòu)了江南水鄉(xiāng)中“新鎮(zhèn)集市”的場景。
2.1.3 非表征地方性
表征手法形成了都市人對鄉(xiāng)村地方性的感性預(yù)期,非表征手法則提供了都市人在鄉(xiāng)村空間滿足地方性感知欲求的工具。非表征地方性伴隨著主體的身體行為產(chǎn)生,通過日常性、時間性、具體性的形式,由身體互動、身體經(jīng)驗、情感等行動細節(jié)共同詮釋。新振村通過復(fù)興“新鎮(zhèn)集市”,在村口以節(jié)慶運營方式恢復(fù)鄉(xiāng)村集市昔日的繁華商業(yè),在實踐性、具體性的景觀體驗行為中產(chǎn)生身體經(jīng)驗和身體記憶。
2.2 基于非遺文化的地方重塑——以上海市寶山區(qū)塘灣村為例
2.2.1 非遺的認同與傳承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以下稱“非遺”)是一種活態(tài)文化,包含了人的主體性與互動性活動。廣義的非遺是指來自過去,在當今具有某種價值但卻存在消失的危險;狹義的非遺是指經(jīng)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家認證的文化要素。本文所指皆為廣義的非遺。地理學對非遺的理解與“地方”始終緊密相關(guān),非遺是具有空間屬性的,且與地方性相互建構(gòu)[7]。
塘灣村具有較好的鄉(xiāng)村美學價值和生態(tài)價值,擁有四喜風糕、十字挑花等區(qū)級、市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和滬劇傳統(tǒng)文化。然而,卻存在“有內(nèi)在無外顯”“有技藝無傳承”的普遍現(xiàn)象。塘灣村作為這些非遺文化的空間載體,在鄉(xiāng)村規(guī)劃設(shè)計過程中,始終圍繞著將這些非遺文化“外顯”出來的思路,讓它們被更多的人關(guān)注和認可,進而得以傳承下來,通過文化展陳和景觀意象相呼應(yīng)的手法,讓非遺得到認定和表征,從而建構(gòu)鄉(xiāng)村獨特的地方感與歸屬感。
2.2.2 非遺的創(chuàng)造與重塑
塘灣村的非遺文化展現(xiàn)不僅有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振興館、十字挑花展示館、滬劇文化展示館的展陳方式,還有通過建筑裝飾元素、室內(nèi)軟裝設(shè)計、室外景觀小品等與展陳相呼應(yīng)的“硬件”設(shè)計手法,更強調(diào)結(jié)合未來鄉(xiāng)村長效運營中的形象設(shè)計、logo 設(shè)計、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及衍生品開發(fā)等,每一個細節(jié)都要與主題呼應(yīng),凸顯文化價值。
通過鄉(xiāng)村旅游產(chǎn)品多元化、在地化開發(fā),打造具有非遺價值的鄉(xiāng)村旅游產(chǎn)品體系,傳承并創(chuàng)新非遺文化,激發(fā)其與塘灣村第三產(chǎn)業(yè)融合,壯大非遺實踐者隊伍,從而帶動鄉(xiāng)村全面富裕。
當非遺實踐者獲得更多的認可與回報,才能具有更強的凝聚力和歸屬感,圍繞著技藝的文化表征和交流也更加頻繁,進一步探索與時代接軌。在這一過程中,傳承人、織女、政府、學者、設(shè)計師、非政府組織及外來商人等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影響力參與到地方性建構(gòu)中,通過聚合多重行動者和元素,凝聚成新的文化、經(jīng)濟和社會價值,使得非遺文化獲得活化循環(huán)的機會,為鄉(xiāng)村發(fā)展提供了新機會。
2.3 基于農(nóng)耕文化的地方重塑——以上海市浦東新區(qū)老港鎮(zhèn)建港村為例
2.3.1 農(nóng)耕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隨著新型城鎮(zhèn)化快速推進,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和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化正在消失,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農(nóng)耕文化作為鄉(xiāng)村村民日常生活、生產(chǎn)方式的集中體現(xiàn),是最容易被認同的鄉(xiāng)土文化。文化認同是個體將特定文化內(nèi)化,以產(chǎn)生歸屬感、認同感、安全感及人文情懷的社會心理過程,屬于一種肯定的價值判斷。在鄉(xiāng)村設(shè)計中應(yīng)該強調(diào)農(nóng)耕文化這一根本,運用農(nóng)耕文化中的技術(shù)、工藝、模式和方式等物質(zhì)化載體,深入挖掘農(nóng)耕文化所蘊含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農(nóng)耕文化,營造鄉(xiāng)風文明和地方文化新氣象。
建港村位于老港鎮(zhèn)中心區(qū),由于村莊靠近鎮(zhèn)區(qū),城鎮(zhèn)化水平高,傳統(tǒng)文化遺失嚴重。本次美麗鄉(xiāng)村創(chuàng)建深挖“耕讀傳家”這一村訓,一方面響應(yīng)浦東新區(qū)創(chuàng)建國家農(nóng)業(yè)科技園區(qū)、國家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園以及老港鎮(zhèn)建設(shè)國家級農(nóng)業(yè)強鎮(zhèn)的目標,另一方面主題化打造“耕讀傳家”場景,與高校黨建聯(lián)建,通過此次創(chuàng)建為未來建港村打造成農(nóng)耕文化體驗地、人才培養(yǎng)集中地提供可能性。
2.3.2 農(nóng)耕文化的空間表達
“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這條樸素的古訓,經(jīng)常被古人刻在門柱上或掛在廳堂中,是他們對自我理想生存狀態(tài)的凝練表達。至今在一些老宅子門前還能看到,與之相伴的還有一塊木匾,上面寫著4 個大字——“耕讀傳家”。
所謂“耕讀”,是農(nóng)耕和讀書的合稱,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最普遍的一種生活狀態(tài)和價值追求——“耕讀并舉”“半耕半讀”。耕讀一體成為古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狀態(tài),耕讀傳家成為社會推崇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國文化中。
鄉(xiāng)村設(shè)計由此獲得了靈感,以“牌匾+楹聯(lián)+江南農(nóng)耕圖”的形式創(chuàng)作沿街“耕讀傳家”系列文化墻,通過形式統(tǒng)一、內(nèi)容靈活變化的方式,打造“耕讀傳家”文化街。牌匾、楹聯(lián)既是中國古建筑和民居建筑中重要的文化元素,又是書法藝術(shù)重要的物質(zhì)載體,很符合“耕讀傳家”的景觀意象。
此外,在中國詩歌文化中,農(nóng)事詩是一種重要的題材,數(shù)量可觀,從《詩經(jīng)》“風”“雅”“頌”到《歸園田居》,從《齊民要術(shù)》到《憫農(nóng)》,都與農(nóng)事相關(guān)。鄉(xiāng)村設(shè)計中將農(nóng)事詩作為一種素材,展現(xiàn)在鄉(xiāng)村的稻田、墻壁等場景中,既是對“耕讀傳家”這一村訓的發(fā)揚,又是對農(nóng)事詩、農(nóng)諺以及農(nóng)耕知識的普及,為打造鄉(xiāng)村未來耕讀文化體驗提供空間介質(zhì)[8]。
在中國古代社會,農(nóng)耕哺育了大量的讀書人,讀書人則借助自己的優(yōu)勢,反哺農(nóng)耕,兩者相互促進、相互補益,這一哺一反的循環(huán),也正是當今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所提倡的可取之舉。
3 結(jié)語
地方性既是人與自然互動的成果,又是鄉(xiāng)村吸引力與價值的來源,目前鄉(xiāng)村設(shè)計的研究正在從“普適性”向“在地性”轉(zhuǎn)變,因此研究基于地方重塑的鄉(xiāng)村設(shè)計方法與路徑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鄉(xiāng)村實踐中可以發(fā)現(xiàn),近年來城鄉(xiāng)規(guī)劃、建筑學與風景園林的相關(guān)研究也在不斷發(fā)生轉(zhuǎn)變,將更加關(guān)注蘊含于空間中的在地性挖掘,喚醒集體記憶、非遺文化、農(nóng)耕文化等鄉(xiāng)土文化,并有選擇性地引導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實現(xiàn)鄉(xiāng)村文化與產(chǎn)業(yè)同步振興。
地方性重建不是對地方文化系統(tǒng)簡單復(fù)位,它是在經(jīng)歷多元文化激蕩之后的理性復(fù)歸,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凝聚民族精神、培育新的地方認同的本質(zhì)力量。鄉(xiāng)村振興的目的不是把鄉(xiāng)村建設(shè)為城市,而是通過“美麗鄉(xiāng)村”“特色田園”“秀美農(nóng)村”等,讓鄉(xiāng)村不僅留住村里人,還能把更多的人才和資源從城市吸引回來。一方面城市在經(jīng)濟上反哺鄉(xiāng)村,另一方面鄉(xiāng)村在文化上反育城市,真正實現(xiàn)城鄉(xiāng)資源與要素的有效流轉(zhu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