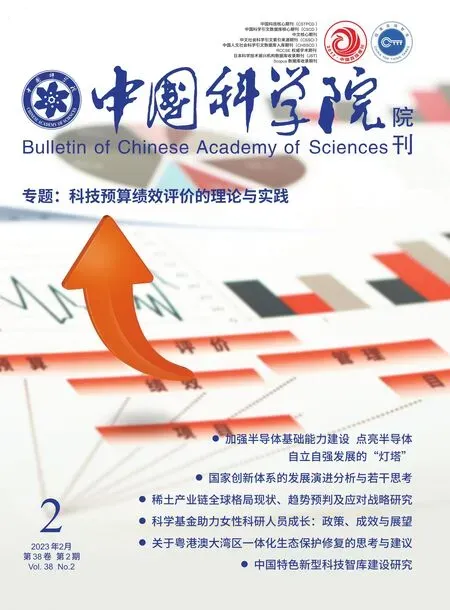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的發展演變與啟示
吳 叢 韓 青 阿儒涵,3*
1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2 中國科學院大學 北京 100049 3 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 北京 100049
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歷經 100 余年發展歷程,是目前相對先進和完善的財政科技投入績效問責機制。由于美國聯邦政府沒有設立專門的科技事務管理機構,其科技領域資助和管理分散在各職能部門中,各部門則是依照機構使命定位來開展科技管理與評價工作,因而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也在政府績效評價的大框架下運行。作為科技強國和引領政府績效評價變革的代表性國家之一,美國聯邦政府預算績效評價有何獨特的實踐經驗?能夠為我國開展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價提供哪些啟示?基于此,本文以美國為研究對象,將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的歷史演進分為探索期、形成期與發展期 3 個階段,首先梳理分析了各階段的特點與方法,進而綜合 3 個階段進行整體性的經驗總結,最后得出對我國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價有借鑒意義的結論與啟示。
1 探索期:為提升預算科學性,啟動基于績效的預算編制方法
美國政府績效評價最早開始于 20世紀初,距今有 100 余年的歷史。1906年,紐約市政研究局首次探索以效率為核心的政府績效評估方法,通過計算政府活動投入、產出和社會條件來衡量政府工作績效。但是績效評價工作并沒有大規模實際推進。直到 20世紀30年代,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和美國農業部開始采用基于績效的預算方式(以下簡稱“績效預算”)來提高部門運作效率。1949年,美國政府行政部門組織委員會(又稱“胡佛委員會”)建議在政府部門中采用績效預算進行預算編制,即“基于政府職能、活動和項目情況來設計聯邦政府預算”[1]。
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政府進一步開發了“計劃-規劃-預算系統”。該系統于 1961年在美國國防部(DOD)首次實施,1965年擴展到所有聯邦機構,旨在通過預算編制手段來加強項目規劃和資源配置之間的關聯性。20世紀70年代末,卡特政府引入了“零基預算法”,強調在績效評價過程中績效數據使用的重要性,旨在加強計劃、預算和支出審查之間的聯系,以提高聯邦政府效益成本比[2]。同期,美國科技資助機構對于聯邦機構研發投入績效評價也開展了相關探索。例如,DOD 的“后見之明”(Hindsight)事后評估項目、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追溯項目”(TRACES)研究、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技術經濟研究等,嘗試將成本效益法運用在科技投入績效評價中[3]。
20世紀初—7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績效評價經歷了一系列方法和實踐層面的初步探索。這一階段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提升效益;美國聯邦政府績效評價方式主要借鑒了企業管理經驗,旨在通過績效信息來約束預算制定,開展對于“錢”的評價。這一時期的探索總體上是出于提升預算科學性的目的而引入績效預算概念,但沒有形成明確的績效評價方法體系保障。美國聯邦政府在這一時期開展的績效預算評價實踐探索為后來其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提供了基礎。
2 形成期:出臺《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形成完整的績效評價方法與組織體系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績效評價的法律地位獲得確認,而科技預算績效評價也在政府績效評價的框架下開始運行。
2.1 基于《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和計劃評級工具的聯邦政府績效評價體系
1992年,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明確提出了要實施以績效為導向的政府管理,并提出了國家績效評估倡議,該倡議的核心是創立一個“運作更好、成本更低”的政府。為了達成這一愿景,1993年 9月,克林頓在白宮發布了《創建一個運作更好、成本更低的政府》報告,該報告中列出了 1 250 項具體行動項目。這些項目約 1/3 涉及美國聯邦政府所有機構,其中由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牽頭負責的預算制度改革項目形成了《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GPRA),其為新型政府績效評價模式奠定了法律基礎;另外 2/3 項目的目標各具有機構特色,由各機構自行貫徹落實[4]。
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 GPRA,并于 1997年開始正式實施。GPRA 要求聯邦各機構制定戰略計劃,開展機構績效評價并上報結果[5]。法律規定,聯邦各機構需要根據機構使命定位,與國會在內的多方利益相關者進行磋商,以制定年度和長期戰略目標。此外,各機構還需制定詳細的年度績效計劃,并在年底提交績效報告[6]。這是美國績效預算改革的一項里程碑式進展,為聯邦政府的績效預算管理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同時也是首次在法律層面上對于聯邦政府機構設立績效目標提出要求。
2001年,喬治·沃克·布什(小布什)總統上臺后,OMB 隨即發布了《總統管理議程》(PMA)。PMA 有 3 項指導原則:① 政府要以公民而非以官僚機構為中心;② 以結果為導向;③ 以市場為基礎,通過競爭機制來促進創新[7]。在這 3 項原則的指導下,PMA提出了 5 項全面管理倡議,即人力資本戰略管理、競爭性采購、改善財務管理、擴大電子政務、預算和績效整合倡議[7,8]。其中,預算和績效整合倡議的出臺和實施難度較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GPRA 的背書。預算和績效整合倡議強調績效評價結果和績效信息的重要性,要求自 2003年起美國聯邦部門實施基于績效的項目預算。在此過程中,PMA 要求各機構同 OMB 合作,為選定的項目選擇目標,評價項目的實施過程、成本和效率等[7]。在 GPRA 與 PMA 的框架要求下,各聯邦機構開始設立自己機構的戰略目標、目標達成計劃并按年度提交進度績效報告,這標志著美國聯邦政府開始明確以目標為導向的績效評價體系。
為了保證 GPRA 和 PMA 實施的有效性,OMB 于2004年引入了“計劃評級工具”(PART)。PART 體系用于評估財政支出計劃與項目的實施績效,是一個以“綜合打分制”為核心的支出審查框架[9]。作為美國聯邦政府開展績效預算評價的有力工具,PART 幫助 OMB 實現了對于 5年周期內所有聯邦政府項目績效預算的把控與監管。
2.2 聯邦政府對于科技項目評估的特殊做法
GPRA 的頒布在美國科技界引起層層波瀾。許多科學家和科研資助機構官員認為科學研究具有獨特性,GPRA 框架并不適用科學研究評價,主要有 3 個原因:① 科學研究成果具有不可預測性,年度績效報告會導致科學家過于關注短期成果;② 科學研究資金來源是多渠道的,無法將多元資助的成果歸功于單一資助機構;③ 基礎研究的質量不能完全依賴于定量評價[10]。
法案的實施不允許有例外,美國國會和白宮堅持科研資助機構也必須實行 GPRA,只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以采用靈活處理方式。1996年,美國基礎科學委員會在《評價基礎科學》報告中指出,要制訂適合科學研究特點的評估策略,同時發揮基礎科學在推動國家總體發展目標中的作用。基礎研究的評價可以采用同行評議與定性定量指標、案例分析、亮點表現等方式相結合的模式。并且,在關注近期直接產出之外,還應關注到研究成果的長期綜合影響[11]。
此外,PART 體系中為聯邦研究與試驗發展(R&D)項目設立了專門附加題項(表1),以更好地體現科學研究與行政部門的不同點。基于 PART 工具,OMB 能夠自上而下地開展對于聯邦機構科技項目層面的績效評估。

表1 美國“計劃評級工具”(PART)附加問題中R&D項目的專設題項(2006年版)Table 1 R&D programs related questions in PART of US(2006 version)
以 NSF 為例,作為科研資助機構,NSF 旨在通過撥款、合同和合作協議等形式資助美國大學、科研機構和非盈利組織等開展科學研究。依照 GPRA 法律框架與 PART 系統要求,NSF 需開展年度績效考核并形成公開報告。2006年,NSF 被評項目共有 8 項,評級結果均為“有效”。以環境生物多樣性項目為例,該項目屬于競爭性資助項目,其中“目標”“規劃”和“管理”3 個部分評分均為 100 分,“結果”部分評分為 89 分。OMB 的綜合評定意見指出,環境生物多樣性項目總體有效,但是在績效表現和效率目標達成兩方面仍需繼續努力。此外建議該項目開展持續性監測,而訪客委員會也會對該項目進行有針對性的外部評審。在 NSF 給出針對性的優化措施后,OMB 提出將繼續支持該項目[12]。
GPRA 與 PMA 的通過與實施為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提供了合法性保障。其中,機構戰略目標設計、目標落實方案和目標進展報告是以目標為導向的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初步探索;PART 系統的落實也為政府績效評價提供了工具支撐。這一階段的探索標志著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逐步從探索期中“錢”的評價轉向了“錢”與“事”的評價。
3 發展期:通過《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修正案》,重點保障高優先級績效目標達成
在績效評價體系形成期內,美國聯邦政府明確了以目標為導向的科技預算績效評價體系,這一模式在后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奧巴馬政府時期推出了機構高優先級績效目標,在聯邦政府機構層面設立了以目標為導向的績效管理辦法;而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時期在沿用機構高優先級績效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目標層級,構建了上下貫通、有機互聯的績效目標系統。
3.1 高優先級績效目標方法的建立
PART 以其績效評價體系的標準化、透明度等特點得到了公眾和管理層的認可。然而,隨著實踐的深入,PART 自身“指標化”“打分制”的理念也受到眾多質疑。例如,評價標準“一刀切”、評價結果主觀性強,缺乏信譽、人財物成本消耗過高、評估工作細節繁雜等[9]。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全面叫停了 PART 系統,并采用“機構優先級績效目標”方法來推動各聯邦機構開展工作。機構優先級績效目標是指機構層面的、需要優先關注的、數量有限的 2年期績效目標(通常為 2—8 個),是推動聯邦機構取得長期成效的關鍵。高優先級績效目標由機構領導層設立,反映了領導層希望機構在 24 個月內達成的成果。奧巴馬任命齊恩茨(Jeffrey Zients)擔任首席績效官和 OMB 副主任;在齊恩茨與若干選定機構共同商議之下,各聯邦機構確定了 18—24 個月之內的機構優先級績效目標,并且通過績效門戶網站和季度審查會議實施過程監督。機構優先級績效目標的實施扭轉了小布什政府自上而下的項目績效評估方法,通過將績效目標自主權下放給各機構的方式,以機構自身為動力,以優先級績效目標為抓手,推動具體工作實施。
為了確保政府改革順利實施,2011年,奧巴馬總統簽署通過了《政府績效與結果修正案》(GPRAMA),從法律層面確立了績效目標在聯邦政府機構績效評價中的作用,這是以績效目標為核心的政府績效評價的進一步探索。作為 GPRA 的修正條款,GPRAMA 就 8 項條款進行了重點修訂,突出了績效目標在績效評價與管理中的作用,明確要求機構需設立跨領域的聯邦優先級目標和機構層面優先級目標。其中,跨領域的聯邦優先級目標旨在促進多機構之間的合作,每 4年更新 1 次;其設立需要 OMB 主任和各相關機構共同商議,要求目標設立以結果為導向、數量不能過多,且要保證可實現性;這些目標最終由總統批準確定。機構層面優先級目標的時間需持續 2年,要求各機構負責人在眾多績效目標中選出優先目標,由 OMB 主任決定全國和各機構績效目標總數(全國總數不得超過 100 項,每個機構不得超過 5 項),并撰寫季度報告以匯報進展情況。
在 GPRAMA 的框架要求下,各聯邦機構提出了符合自身發展愿景的機構優先級績效目標,并采用績效目標達成評價法開展機構層面的績效評價。績效目標達成評價法以合理的績效目標設立為核心,以績效信息為依據來判斷績效目標達成情況,即“基于證據的績效評價”。這一方式要求各聯邦機構首先針對各自使命定位和戰略規劃制定出一段時間內的可衡量的績效目標,然后被評機構需自行提供目標達成情況的證據集來說明目標完成度,再以績效目標為核心、證據集為依據將證據集交由專家進行研判,最終由評審組給出“是否達成目標”的判斷結果(圖1)。

圖1 美國優先級績效目標評價流程Figure 1 Evaluation procedure of agency priority goals
科技領域績效評價也在此模式下運行。以 NSF 為例,2011年設立的機構優先級績效目標為“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的勞動力發展”。該目標要求:截至 2011年底,STEM 領域中至少 6 項有關研究生、職業和早期職業的項目要設立配套的績效評價系統,且評價結果需能為項目重新規劃或整合所用,以提供更多的戰略影響。該目標由 NSF 時任教育和人力資源理事會助理主任 Ferrini-Mundy 負責。2011年 NSF 在年度績效報告中提交了相關的證據集內容。為確保績效評價結果可衡量,NSF 為評價活動設立了一套指標體系,評價指標和證據來源等如表 2 所示[13]。

表2 2011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優先級績效目標評價指標體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NSF agency priority goals in 2011
基于該指標體系,優先級績效目標評價采用了 5 分制評分法,從低至高依次賦 1—5 分。參與評審的項目材料由 NSF 提供,評審專家對于 STEM 領域中參評的 25 個項目分別進行評價,并形成最終打分表。經過專家組研判,“研究生教育和教授聯盟”和“教師早期職業發展計劃”等 12 個項目能夠滿足優先級績效目標描述中的要求。因此,專家組將優先級目標的整體績效結果判定為“達成”[14]。
隨后,NSF 在優先級績效報告也總結了相關經驗與問題。NSF 指出,優先級目標完成度評分最高的幾個項目有共性經驗,如有美國國會指導參與、受資金資助期更長、評價體系更為成熟等。而對于未達成目標的幾個項目,其中共性問題也存在一定的客觀性,如項目設立時間較短、證據收集不夠等,后期也將會進一步整改完善[15]。
3.2 形成系統化的聯邦機構績效目標管理體系
奧巴馬政府時期推出的以機構優先級目標為主導的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模式進一步明確了績效目標在評價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而這一模式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時期獲得了進一步的完善與改進,形成了由自上而下的績效目標設定和自下而上的績效結果評估組成的一整套目標管理體系(圖2)。該體系上下貫通、縱橫到底,服務于美國聯邦機構的總體愿景。

圖2 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績效目標系統關系圖Figure 2 Structure of US feder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goals
3.2.1自上而下,設立聯邦機構的績效目標體系
對于聯邦機構而言,機構戰略性目標、機構優先級目標及其子目標的組合形成了有機關聯的績效目標系統。第一層為戰略目標層,包括總戰略目標和子戰略目標。戰略目標層是宏觀的、能夠反映機構長期戰略方向的目標,根據機構的戰略規劃期每 4年修訂和更新 1 次,實施過程中領導層要開展年度審查。例如,2022年 3月NSF 公布了最新一期的《2022—2026年戰略規劃》,重點關注 STEM 領域人才、知識創造、知識轉化和 NSF 管理提升 4 個部分。第二層為多年績效目標層,包括多年期績效目標和優先級績效目標。該目標層的設立是為了落實和保障戰略性目標的實施。多年期績效目標通常持續時間較長,一般會覆蓋機構的戰略規劃期。例如,NSF 在 2018年設立的 7 項多年期績效目標,其中 6 項覆蓋了 2018—2022年戰略規劃期。優先級績效目標延續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特點,目標持續 2年。機構內部要設立績效目標負責官員,領導層要開展季度績效審查,保證能夠及時發現問題并調整修改。第三層是年度績效目標層。該類型的目標設立是為了保障戰略目標層和多年績效目標層的落實與實施。
以 2021年 NSF 績效目標系統設立為例。NSF 戰略目標層的設立依照 2018—2022年戰略規劃期要求,共設 3 項總戰略目標,每項總目標下各設有 2 項子戰略目標。多年績效目標層共設置8項目標,其中 1 項為 2年期機構優先級目標,分別服務于不同的戰略目標。年度績效目標層共設立 11 項目標,是多年績效目標層的進一步延伸與細化,與各項多年期績效目標分別對應。
3.2.2 自下而上,開展針對聯邦機構各層級績效目標的評估
績效評價結果判定遵循了自下而上的方式,即基于年度績效目標達成結果來判定多年期績效目標層的達成情況。2021年 NSF 的機構績效評價也依照了“年度績效目標層-多年績效目標層”的思路展開。年度績效目標層中,經過機構證據收集和評審專家研判等流程,11 項年度績效目標有 8 項被判達成,3 項被判未達成。基于該評價結果,NSF 的 8 項多年績效目標中,5 項被判達成,2 項被判部分達成,1 項被判未達成。對于部分達成和未達成的績效目標,NSF 在 2021年績效結果報告中也做出了特別分析。例如,NSF 指出,機構達成了中等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年度目標要求,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導致 3 個項目的建設進度有所推遲,故未能達成對應的年度目標,因此多年績效目標二被判定為“部分達成”。同樣出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NSF 領導層決定將工作重點轉移至疫情相關研究的規劃和資助等內容,故未能達成評審速度方面的年度目標要求,因此多年績效目標五被判定為“未達成”。在對于信息技術系統的要求上,2021年 NSF 領導層將投資重點改為提升外部客戶體驗感,如為研究人員提供展示和培訓環境、改善信息收集等;投資決策的轉變影響了 NSF 門戶網站的優化進程,導致 1 項年度目標無法達成,因此多年績效目標八也被判定為“部分達成”[16](圖3)。

圖3 2021年NSF績效目標系統設立與績效評價情況Figure 3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of NSF performance goals in FY2021綠色為目標達成,黃色為部分達成,紅色為未達成Green marks performance goals achieved, yellow marks partially achieved and red marks unachieved
4 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發展的演變特征
在對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發展歷程中 3 個階段(探索期、形成期與發展期)的方式方法進行各自分析的基礎上,有必要貫穿百年歷程,揭示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百年演變的底層邏輯。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既包含科學層面的、偏重基礎研究的績效評價,如 NSF 優先級目標與機構績效目標系統評價,也有技術層面的相關實踐,如美國能源部資助的車輛技術、地熱、水能等研究與發展項目評價在 PART 體系中的應用等[12]。總體來看,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發展至今有 4 個演變特征。
(1)美國政府績效評價實踐體現了“變”與“不變”相結合的特征——“變”的是不斷完善的體系與方法,“不變”的是提升政府績效的根本目標。可以看到,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的政策工具在不斷地發展和優化:在目標設立方面,由 GPRA 時期僅關注機構層面目標,到 GPRAMA 時期引入優先級績效目標,既關注跨機構的聯邦優先級目標,也關注機構層面 4年期戰略目標、2年期的優先級績效目標和年度績效目標,從而形成更為系統和全面的績效目標體系。在評價方法方面,由早期方法探索、發展到項目層面的 PART 工具、再演化成為與聯邦機構績效目標體系相配合的目標績效達成評價法。同時應注意到,這些政策工具本身雖然在不斷發展,但其宗旨從未脫離政府管理的根本性目標,即以漸進優化的政策工具來提升美國聯邦政府的績效表現和公信力。
(2)美國聯邦政府績效預算評價在發展中逐步完善評價體系與政策工具。美國聯邦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國聯邦政府從重點關注“錢”的配置來開展績效預算實踐,到逐步關注到“錢”與“事”相結合的項目績效評價,再到近 10年來凸顯機構層面和跨機構層面優先級績效目標的全流程績效目標系統評價,每一步都在基于前期的探索與努力做邊際“加法”,不斷豐富和完善,以更加科學理性的方式保證預算有效性。
(3)嚴格的預算審核聽證,為美國政府績效預算評價提供了機制保障。一方面,美國聯邦預算編制流程復雜、聽證環節眾多,編制過程充分考慮績效評價結果。在預算編制過程中,各聯邦機構的預算計劃需交由 OMB 進行審查,預算計劃中需要報告各機構上一財年的績效評價結果。在幾輪磋商與修改后,OMB 會基于機構上財年的績效表現決定是否繼續提供資助,形成聯邦預算后交由總統和參眾兩院進行審批撥款。通常一個完整的科技預算編制和審查周期需要 3年時間[17]。另一方面,以美國科技促進會(AAAS)為代表的科技組織也為美國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提供了智力支持。例如,2020年 7月,時任AAAS 總裁 Parikh 呼吁更新已有 75年歷史的美國聯邦政府科技資助框架,并指出現階段美國研發投入水平遠低于其峰值期,建議進一步增加科技投入。再如,每年 AAAS 會對下一財年聯邦政府科技預算配置進行統計分析和建議并發布相關研究報告,參與針對聯邦科技預算的聽證會,在國會會議結束時發布報告來總結、分析美國政府科技資助的效果與影響等[18,19]。此外,AAAS 主辦的期刊Science發表大量政策研究成果,為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提供理論與方法支撐。例如,20世紀80—90年代,針對科研產出價值難以量化的問題,Science收錄了 Ling 和 Hand[20]、Leopold[21]、Lewison[22]等學者有關各類科技產出評價方法使用與優缺點的文章,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工具層面的新思路。
(4)美國聯邦政府績效評價的發展過程也非一帆風順,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是推動績效改革的動力。① 在 GPRA 推行過程中,科技領域績效評價是否應該采用該法律框架受到了科學界質疑。充分考慮到科學研究的獨特性,美國國會和白宮在強制執行 GPRA 的基礎上,同意在科學研究評價過程中采用靈活處理方式,如制訂特殊評估策略、考慮基礎研究長期影響、采用同行評議與定性定量、案例分析和亮點表現等方式相結合的多元評價模式等。② 在 PART 體系時期,其打分制和指標化方法受到民眾質疑,認為存在評價結果主觀性強、人財物成本消耗過高、評估工作細節繁雜等問題。針對該情況,奧巴馬政府叫停 PART 工具,轉而采用機構優先級目標來推進機構績效評估。③ 進而,在 2010年,政策專家對于奧巴馬政府績效改革進程提出質疑,認為聯邦政府改革目標存在,但是執行力度不足[23]。針對該問題,奧巴馬任命齊恩茨為 OMB 副主任,重點推進機構優先級績效目標,并通過門戶網站與季度會議跟蹤監督政策過程。一系列問題的發現與解決成為了美國聯邦政府完善科技預算績效評價的助推力,為政策的完善提供事實依據。
5 結論與啟示
5.1 結論
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在 3 個時期內有不同的發展,整體來看是一個不斷完善的漸進變化過程。各階段分別體現了各自特點,其評價方法也在逐步完善中:探索期內,聯邦政府為提升預算科學性,啟動績效預算,經過計劃-規劃-預算系統、目標管理法、零基預算法等一系列方法實踐,以預算為約束來提升政府績效。形成期內,GPRA 法案為政府開展績效評價提供了法理基礎。聯邦機構開始以績效目標為核心開展績效管理,PART 工具為機構項目績效評價提供了新工具,形成了完整的績效評價體系。發展期內,GPRAMA 進一步確立了以績效目標為核心的政府績效預算評價體系,重點保障機構優先級目標達成,目標績效達成評價法也為績效評價實踐提供了方法支撐。
5.2 啟示
2018年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意見》標志著我國預算績效管理工作從試點探索階段(2000—2018年)向全面實施階段轉變。經過 20 余年的探索,我國各級政府部門對于預算績效管理的認可度不斷提升,對于“花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原則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然而,在具體的財政科技預算績效評價方法上仍存在較多問題,可借鑒美國經驗進一步改進。
(1)深化認識,恪守以績效評價提升財政科技投入效能的根本目的。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我國財政科技投入提出了明確要求,即“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財政科技經費分配使用機制改革”。從美國來看,其聯邦政府科技預算評價的政策工具歷經百年的發展和完善,在具體方式方法上不斷調整和優化,但是始終圍繞政府效能這一核心目標。我國過去20余年在財政科技績效評價中,以打分制為主的評價方法過多關注細節,在某些時間段上出現了過分強調項目中期結項、忽視項目本身戰略目標等偏離初衷的問題。建議進一步統一觀念、深化認識,在國家層面進一步明確將政府效能提升作為財政科技績效評價的根本目的,以此促進我國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2)加強對宏觀戰略目標等科技投入效果的評價,促進科技投入更好地支撐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美國聯邦政府科技預算績效評價在形成期向發展期的轉變過程中,經歷了從聯邦預算項目完成情況的評價向機構優先級績效目標評價轉變的過程。我國現階段同樣存在以項目產出和管理為績效評價重點,忽略宏觀戰略目標達成等問題。針對這一問題,可以借鑒美國等的經驗,在項目產出和管理的評價基礎之上,開展宏觀層面的戰略目標與效果的評價,從而避免績效評價流于形式。
(3)強化績效評價結果在預算編制中的實質性應用,切實發揮科技投入績效評價的作用。中美兩國在預算編制機制方面各有特色。美國聯邦政府在預算編制階段通過開展廣泛的聽證和質詢,以立法形式頒布預算,保障了預算的合理性。我國預算編制實踐則更多地遵循歷史路徑依賴和主管部門要求,在預算編制有效性和合理性方面仍然有提升空間。預算績效評價提供了“從結果看投入”的新視角,實際上在為預算編制提供糾偏作用。因此,加強預算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有助于切實發揮科技投入績效評價作用,從而提升財政科技投入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