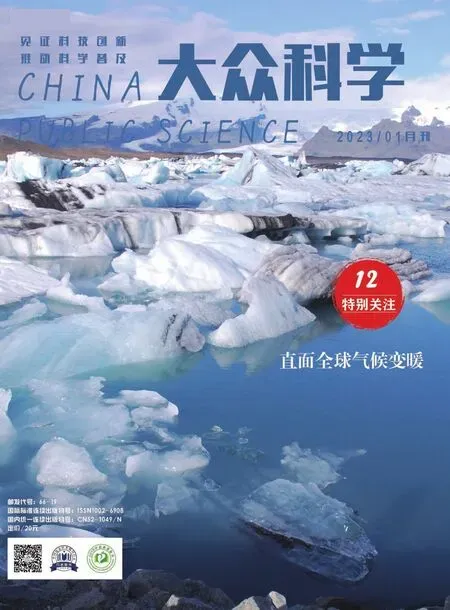人形機器人黑科技解密:后空翻、動手指都靠它

人形機器人能跑能跳的關鍵,藏在機器人的“關節(jié)”里。人體的關節(jié)決定了做各種動作的靈活性,機器人的“關節(jié)”驅動器同樣如此。
已發(fā)展數(shù)十載的驅動器,為何至今仍是連科技巨頭都難啃的“硬骨頭”?波士頓動力和小米、特斯拉的“關節(jié)”到底有什么不同?背后涉及哪些關鍵技術及組件?本文將從技術到產業(yè)鏈,深扒一顆顆小小的驅動器,如何成商用人形仿生機器人的“命門”。
想讓機器人玩雜技?先煉好“人工關節(jié)”
人形機器人有4大核心組件,分別是傳感系統(tǒng)(對應五官)、控制系統(tǒng)(對應大腦)、執(zhí)行機構(對應四肢)和驅動系統(tǒng)(對應關節(jié)組織)。
走路、下蹲、舉手、抓握、搬重物、爬樓梯……機器人的每個動作都離不開驅動系統(tǒng)的支持,驅動器則是撐起機器人運動能力的關鍵組件,技術門檻、成本都很高。
這是一個“小而精”的技術要地。人體有名有姓的關節(jié)共78個,其中使用頻率高、承受重量大的關節(jié)更易出現(xiàn)磨損和病變。老年人不如年輕人動作麻利,往往是因為關節(jié)的靈活性、韌性損壞了。
類似的,人形機器人能否高效精準做各種動作,非常依賴控制肩、肘、腕、指、髖、膝、踝、腰椎等關節(jié)部位驅動器的質量。這要求驅動器既要數(shù)量多、占空間少、重量輕,又要耐摔扛撞。畢竟一旦“關節(jié)”出問題,機器人就“癱瘓”了。
因此,一臺行動精準敏捷的人形機器人,其“關節(jié)”至少應具備這些特征:
數(shù)量上,自由度越多,能做的動作越復雜。自由度可以簡單理解成能讓一個物體獨立運動的數(shù)量。小米人形機器人“鐵大”全身有21個自由度,特斯拉“擎天柱”的更多,全身自由度共28個。
形態(tài)上,體積越小,機器人外形越精巧。深圳安普斯的伺服系統(tǒng)專業(yè)研發(fā)人員透露,伺服驅動器在工業(yè)領域已經(jīng)很成熟,但放到人形機器人中需做到更小,突破這一點后,精度、控制性能、柔性化等就都不是大問題了。
功能上,輸出扭矩越大,承載能力越強。波士頓舊版Atlas的膝關節(jié)扭矩已高達890Nm,髖關節(jié)扭矩達840Nm。小米“鐵大”的髖關節(jié)主要電機瞬時峰值扭矩可達到300Nm。
人在運動過程中,腳底接觸地面瞬間的沖擊力是人體體重的數(shù)倍。因此人形機器人要想像人類一樣瞬時起跑、彈跳,很考驗驅動系統(tǒng)的快速響應和能量效率。
要讓機器人動作速度快,驅動器在提供很大輸出功率的同時,需確保不會因為發(fā)熱量太大而被燒壞。驅動系統(tǒng)還要具備出色的緩沖沖擊能力,來保護驅動器不會因為猛烈撞擊而損毀。
掌握抓握的力度也很重要。舉個例子,如果讓機器人去拿雞蛋,握力過大,可能把雞蛋捏碎;握力過小,雞蛋就摔地上了。因此驅動系統(tǒng)需與控制系統(tǒng)協(xié)作,精細控制每一個動作的輕重。
總體來說,人形機器人的驅動器必須做到體積小、重量輕、軸向尺寸短、高功率密度、高能量利用效率、精度可控、耐沖擊性等特性,結合機器人整機結構和控制系統(tǒng)設計優(yōu)化,才能保證其關節(jié)動作的高效執(zhí)行。這不僅是制約人形機器人更靈活、自由的關鍵,同時也是讓其實現(xiàn)規(guī)模化量產、應用的重要門檻之一。

波士頓動力VS特斯拉小米,驅動器差別有多大?
為什么集聚了強大工程師團隊的小米“鐵大”、特斯拉“擎天柱”,沒能做到像波士頓動力Atlas那樣高燃跑酷?
優(yōu)必選科技人形機器人創(chuàng)新中心負責人表示,從時間維度看,特斯拉、小米機器人剛開發(fā)一年多,在軟件運控層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從技術方案看,特斯拉和小米機器人采用的電機驅動方案,Atlas采用的液壓傳動方案,驅動器集中性和功率密度不在同一層次。
而技術路線的差異,歸根究底是特斯拉、小米研發(fā)人形機器人的用途定位和預期功能,與波士頓動力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導致成本亦相差很大。
波士頓動力Atlas主打挑戰(zhàn)極限的炫技動作,因此選用功率大的液壓驅動。其核心原理是通過液體壓縮泵產生高壓液體,高壓強作用于缸體產生巨大推力,帶動機器人關節(jié)運動。這也是Atlas能做出高難度絕技的秘訣。
波士頓動力在液壓驅動方向一家獨大,積累了大量專利。Atlas有一個非常緊湊的液壓驅動裝置,重5kg、功率5kW,里面有電動泵儲液罐、電池、過濾器、電子設備和一個冷卻系統(tǒng),憑借28個液壓驅動器完成各種爆發(fā)力強的雜技動作。
液壓驅動方案的缺點是噪音大、易漏液、對污染敏感、對液壓元件的精度質量要求高、對維護團隊要求高等,導致制造成本居高不下,難以走出實驗室、走向商業(yè)化。
因此,優(yōu)必選科技Walker、小米“鐵大”、特斯拉“擎天柱”等人形機器人,都選用了穩(wěn)定性、性價比更高的電機驅動方案,更加注重實用性。
在電機驅動方案中,伺服驅動器將位置、速度、扭矩告訴伺服電機,伺服電機將接收到的電壓信號轉換為扭矩、轉速,減速器可以增加扭矩,優(yōu)化低速運動的平穩(wěn)性。
雖然扭矩密度遠低于液壓驅動,但電機驅動可以通過搭配減速器來加以補足,其現(xiàn)有技術已能滿足機器人的多數(shù)運動需求,同時擁有能量轉化效率、易維護、低成本、零件規(guī)整等優(yōu)勢。
據(jù)一位機器人行業(yè)的資深產品經(jīng)理透露,這一驅動方式通過位置、速度、力矩來實現(xiàn)對機器人的閉環(huán)控制,使精度更高。在機器人系統(tǒng)中,伺服電機能做到“說停就停、說走就走”,讓執(zhí)行系統(tǒng)能夠“絕對服從”控制系統(tǒng)的命令。
因用途不同,用在不同機器人“關節(jié)”位置的驅動器,在物理指標、執(zhí)行任務強度和功率方面均不相同。為了找出最優(yōu)的驅動器方案,科技公司多選擇定制驅動器的路線。
例如,小米“鐵大”全身有5種關節(jié)驅動器,行走時速能夠達到3.6km/h。其上肢關節(jié)能夠靈活運動,得益于小米為其研發(fā)的一個重量為500克、額定輸出扭矩高達30N·m的高效電機。
特斯拉研究人員利用算法為“擎天柱”定制出6款最優(yōu)的驅動器,包含3種線性驅動器(采用永磁電機)和3種旋轉驅動器(采用諧波減速器),以滿足不同關節(jié)的效率需求并兼顧成本。
其中,線性驅動器用于推拉,比如讓機器人手臂向前或向后伸展;旋轉驅動器用于轉動動作,有直流電機、伺服電機、步進電機等常見類型。這些驅動器能驅動完成不同角度的動作。基于這些設計,“擎天柱”的手腕、腳掌都能靈活轉動。
從精簡成6 款驅動器可以看出,特斯拉奔向“大規(guī)模量產”、2萬美元成本目標的設計思路非常明確,通過實現(xiàn)更多硬件重復可替代,壓低總體成本,并讓所有的驅動器都能高效工作。

在設計過程中,特斯拉結合收集到的真實世界數(shù)據(jù),在虛擬空間中做機器人走路、轉身模擬,用人工智能算法反復測算扭矩、速度等數(shù)據(jù),分析出能夠更好兼顧質量、效率、能耗、成本平衡的最佳驅動器設計。
在承重能力上,特斯拉研發(fā)的腿部線性驅動器,通過集成伺服電機、減速器、絲杠、傳感器、一體化運動單元等零部件,做到了精準的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力控制,在極限測試中能提起一架500kg重的鋼琴。
除此之外,特斯拉“擎天柱”還有一大看點——設計出與人手非常相似的機械手。
“擎天柱”的每只手擁有11個精細的自由度,結合控制軟件,能完成像人手般復雜靈巧的操作,并能承擔大約9公斤的負重。驅動器通過齒輪驅動一根金屬線來控制手指彎曲,并集成了感應器和鎖定裝置,以更加節(jié)省能耗。
相比之下,很多人形機器人的手部設計都較為簡單,例如Atlas的手像個浴霸,“鐵大”的手沒有手指。它們能開門、能抓握,但碰到像“穿針”這樣的精細活兒,就會一籌莫展。
為了保護包括驅動器在內的核心組件避免因碰撞等突發(fā)情況造成損壞,特斯拉工程師借鑒了以往在車輛安全測試上獲得的技術跟經(jīng)驗,用軟件模擬機器人摔倒等狀況,通過調整機體,把傷害控制在表面。
在供電上,波士頓動力Atlas與特斯拉“擎天柱”的差別也很顯著。Atlas的3.7kWh電池組只能撐起大約1小時的活動,特斯拉則聲稱“擎天柱”的2.3kWh電池能供應其一整天工作所需的電量。
50 年演進3大路線,人工肌肉或成未來主要研究
回溯發(fā)展歷程,人形機器人驅動器的技術演進經(jīng)歷了3個階段:傳統(tǒng)剛性驅動器、彈性驅動器、準直驅驅動器。
早先從1983年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發(fā)出WL-10R機器人起,傳統(tǒng)剛性驅動器被廣泛用到人形機器人中。這種驅動器的最大輸出功率密度只能達到200~300W/kg,與生物肌肉500W/kg的功能密度相差較遠,因此在人形機器人上的應用受限。
彈性驅動器、準直驅驅動器均由麻省理工學院提出。彈性驅動器SEA最早提出于1995年,通過模擬具有彈性的肌肉系統(tǒng),讓關節(jié)的動作變得更加流暢。但因其彈性體的控制難度較高,該驅動器難以做到精準控制機器人的動作。
近年趨熱的準直驅驅動器是在2016年提出。準直驅驅動器依靠驅動器電機開環(huán)力控,不依賴于附加力或力矩傳感器,就可以本體感知機器人腳部和外界的交互力,也被稱為本體驅動器。

從具體構成來看,傳統(tǒng)剛性驅動器由電機、高傳動比減速器、剛性力矩傳感器、輸出端組成,其中剛性力矩傳感器是可選擇項;彈性驅動器則在高傳動比減速器與輸出端之間加了彈性體,用位置傳感器檢測彈性體的形變,可以推斷出力矩的大小;而準直驅驅動器改成了高力矩密度電機+低傳動比減速器的組合,通過電機的電流大小間接推斷出輸出力矩的大小。
更理想的方案是電機直接驅動,但由于現(xiàn)有電機技術的限制,電機直接驅動的扭矩密度達不到機器人關節(jié)應用的需求,因此,輔以減速器是一個折中方案。
同時,要求負載質量和轉動慣量盡可能的小,可以實現(xiàn)高帶寬力控和良好的抗沖擊能力,滿足人形機器人對小尺寸關節(jié)的需求。
未來,結合5G、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驅動器還有望在云上實現(xiàn)相互通信,檢測和監(jiān)控驅動器的實時狀態(tài)。
“人形機器人驅動器經(jīng)歷了由剛性驅動器向彈性驅動器和準直驅驅動器的技術演進。彈性驅動器和機器人整體優(yōu)化,甚至人工肌肉研究都是未來發(fā)展方向。”專家表示,仿生機構都遠沒有達到人類骨骼肌肉系統(tǒng)的能力,機構的主動件驅動器也沒有達到人類肌肉的水準,因此這一方向未來還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
在科技巨頭帶動下,驅動器的發(fā)展前景,正讓相關國產廠商受到更多資本的關注。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人形機器人研究中,驅動器等核心軟硬件一直在迭代進化,但迄今距離完全類人的運動性能仍然遙遠。人形機器人對于關節(jié)自由度和靈活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規(guī)模化商用的目標又對硬件成本提出更苛刻的限制。
邁入2023年,我們期待看到更多“化繁為簡”的設計理念,進一步優(yōu)化驅動器等核心組件的性能與成本,打開人形機器人進入家庭的想象力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