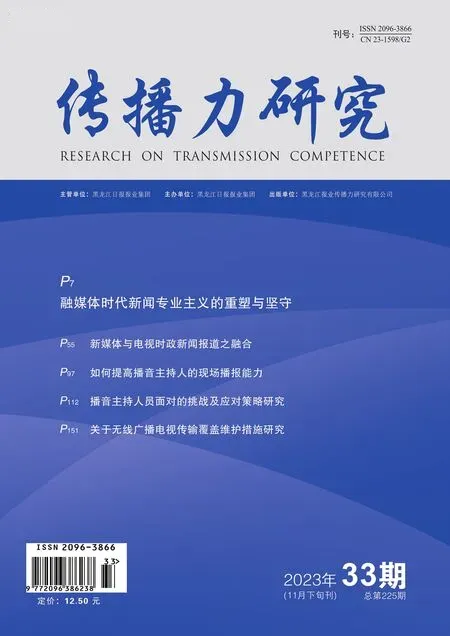網絡短視頻中青年亞文化傳播機制和規制研究
◎王紫語
(成都錦城學院,四川 成都 610097)
短視頻是信息技術蓬勃發展的產物,以文娛體育、學習生活、教育為拍攝內容拍攝的具有文化和實踐特征的視頻。當前,短視頻生產與傳播已成為典型文化現象,以片段化方式展現不同特征與風格的青年亞文化[1]。青年文化因網絡獲得了廣闊的成長空間,年輕群體也借助虛擬技術優勢打造符合自身個性特征與興趣愛好的文化價值觀。對此,應通過客觀審視與深入探究,尋找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間的契合點,推動短視頻以及新興網絡快速穩定發展。
一、青年亞文化語境下網絡短視頻發展特征
(一)大眾化
網絡在新媒體背景下為亞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展示特征的平臺,也為社會普及青年亞文化奠定了良好基礎。近年來,受眾對青年亞文化的關注度日益提升,其附帶價值也逐漸提高。例如,在熱播綜藝《奇葩說》中,主持人運用“廢話就像頭皮屑,海飛絲幫你消滅它。”這一俏皮語播報節目贊助商廣告,將商業產品宣傳與當下熱議亞文化相結合,再以商業形式收編亞文化。隨著資本轉換以及對亞文化關注度的提升,基于新媒體傳播下的亞文化有了更多展示空間,甚至能與主流文化共同出現在大眾視野范,加速青年亞文化轉型。上述情況說明,無論商業收編亞文化或與主流文化共同展現,亞文化在新媒體時代都以符合大眾化傳播與發展的形式持續發展,與以往社會群體對青年亞文化存在偏見有著顯著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新媒體在促進青年亞文化大眾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此外,青年亞文化在當前媒介傳播和文化大交融背景下,對傳統文化與主流的解構與挑戰在無形中加速了青年亞文化在新媒介下的轉型,轉變了部分受眾對青年亞文化的偏見。網絡短視頻運用已有物品體系中的符號系統并加以轉換和利用向經典發起對話,再運用非常規方式對社會權威進行質疑,達到荒唐、怪誕、幽默與詼諧效果,在此過程中表達自身想法和發表言論以及傳遞目的,展現對主流話語權與文化的解構[3]。
(二)自發性
青年亞文化的形成一般是由年齡相近的青年群體通過相似的心理特征、社會觀察能力、價值判斷和選擇而構成的新時代青年價值文化[4]。這種文化不是社會階級壓迫或者刺激產生的,不存在外力施壓的情況,同時也不屬于社會文化的必要組成,它是新時代青年群體通過個人判斷和群體現象發酵而自發產生的,屬于青年群體在社會發展中獨到的話語現象。以“80 后”“90 后”青年為代表,并呈現不斷擴張的趨勢,青年群體既是青年亞文化的創造者,同時也是文化的先行傳播者,但是傳播者的范圍并不局限于青年,隨著互聯網新媒體的不斷發展和普及,更多的人加入到了青年亞文化的傳播者中,但其主體仍然是青年,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例如,“80 后”“90 后”以快樂男聲、快樂女聲等歌唱比賽和韓劇、韓星為代表的追星文化;以獨特風格服飾奪人眼球的殺馬特風格的非主流文化;以戲謔諷刺口吻、表情包等手段對社會特點和現象進行評論的表情包娛樂文化。
(三)包容性
亞文化受廣泛普及的互聯網和蓬勃發展自媒體影響,其與主流文化已不如以往般涇渭分明,而是展現出共通交融的形態。尤其在部分領域,主流文化被亞文化中的部分創新性觀點所影響,也在改變自身的發展方向。縱觀當前社會生活,很多方面都有了青年亞文化的身影,例如,涂鴉文化就受到各大品牌的歡迎,相繼推出涂鴉聯名吸引用戶關注。事實上,在大眾的認知中,以傳統為引領的主流文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亞文化則是創新文化的典型,雖然創新不是亞文化才具有的屬性,然而部分主流文化確實可以借鑒與學習亞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展現的創新性。但需要認識到處于多元文化社會環境的新一代青年人要求更多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去接受出現的亞文化,增強青年亞文化的包容力,對于其積極方面予以關注,對于其消極方面予以引導,為更好地引導青年群體樹立正確的主流價值觀而做準備。我們也要認識到青年亞文化并不是消極的代名詞,要在社會的不斷變革中對青年亞文化的存在給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要辯證地看待青年亞文化的存在,既要看到其與主文化之間的對抗性,也要看到其對社會文化體系積極的一面。在某些情況下,亞文化也是對主流文化的補充,可以與主流文化和諧共存。它不僅是網絡時代中青年人文字語言與肢體語言的替代品,也是一種日常文化實踐。因此,我們在評析青年亞文化時應該辯證客觀,避免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青年亞文化的產生和發展[5]。
二、網絡短視頻青年亞文化傳播機制
青年亞文化在互聯網背景下不斷生長,對青年群體而言,亞文化具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力。若科學利用青年亞文化的強大力量,必然會形成較強的凝聚力,推動青年群體快速成長。虛擬網絡打造的空間場景可覆蓋所有層面,每個置身于其中的網民均能成為各種情緒傳播的重要節點,再通過復雜群體結構作用形成一定范圍內的相似認同與認知,并在技術加持與人際傳播中形成多維互動的傳播循環鏈,這也是網絡短視頻中青年亞文化傳播邏輯。其具體傳播機制如下。
(一)依附于技術開放傳播環境
新媒體與受時空限制的傳統媒體相比,通過技術方式形成與眾不同的傳播機制,其傳播渠道與方式也更趨于開放化以及支持信息傳播主客體實現雙向度與多維度交互。主流文化傳播渠道在此背景下得到拓展,為引領青少年亞文化朝健康方向發展提供強大支撐平臺。眾所周知,主流文化傳播主要平臺為主流媒體,學習強國、央視新聞、《人民日報》等媒體平臺在傳遞主流文化中發揮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力,若合理利用新興媒體,必然可推動主流文化傳播。青年亞文化傳播內容新穎、傳播個體獨特,以及傳播方式的顛覆性等一系列價值訴求,與網絡短視頻平臺的用戶訂閱、算法推薦、碎片傳播等傳播環境形成內在邏輯共振,并在相互交織中實現共同發展。
(二)可模仿性的疊加傳播
新媒體的出現使很多興趣相投的群體找到歸宿,青少年更不例外,通過新媒體不僅可以獲取身份認同,精神需求也能夠得到極大滿足。現代青少年可根據自身興趣愛好選擇群體并自主決定行為方式,可以說青少年因主體性釋放激發挖掘小眾文化興趣,即使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文化,也能在虛擬時空中構建精神棲息地。青年網絡短視頻行為背后的意義即直接的情感宣泄方式、多元價值訴求與獨特表達機制。其他受眾經模仿行為可優化表達與自我替換中心人物,內心多元情感需求可在此過程中得到滿足,更能有效宣泄情緒情感,推動青年亞文化短視頻疊加傳播。現代年輕群體尋求認可和表達自我的主要方式。例如,抖音有很多美妝創作者制作仿妝視頻,很多青年會相繼模仿或創新視頻內容,甚至部分創作者的創作和傳播效果超越原版。青年網民因短視頻引起群體模仿行為,并在短時間內產生情感共鳴,被認同和被關注的心理訴求得到有效滿足,進一步推動了青年亞文化快速穩定發展[6]。
三、網絡短視頻中青年亞文化傳播規制策略
(一)采取規制收編,實現強制性約束
如果青年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充分尊重與理解,以及在主流文化活動中尋找到自身的位置,展現自身價值,那么就會逐漸降低不良文化對其的吸引力。針對青年亞文化的傳播需要善于引導其朝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主流文化方向發展,并在此基礎上挖掘亞文化中健康和積極的元素。雖然青年亞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叛逆特征,但是其并不反對主流文化體系與主流意識形態,尤其在重大事件發生后,此文化圈層積極融入主流文化與意識形態引導的宣傳討論中,由此說明,青年亞文化有被當前主流文化影響及引導的可能性。事實上,部分青年彰顯個性和力量,展現出亞文化及相關群體“圈層化”現象,這些青年群體往往在政治、經濟、文化、聲望、社會地位等層面缺少影響力與話語權,然而其表達欲望和自我意識又極為強烈,因此通過共同的興趣和愛好集結成一個個新族群。傳統社會中的族群往往以家庭、社區、學校和單位為紐帶,而很多青年群體則以興趣愛好來聚合、以價值認同為連接。新族群的形成正是亞文化“圈層化”的結果,他們試圖規劃自己的勢力范圍,并通過各種亞文化符號來刷新主流社會對自己的認知[7]。針對青年亞文化發展,除了要采取選擇性認可與商業性收編兩種“軟性”策略,還需采取強制性規制收編,打造健康和諧和積極向上的發展環境與秩序。官方層面的強制收編僅針對個別青年亞文化內容與行為,也是對選擇性認可與商業化收編的補充,最大限度地保障青年亞文化在網絡短視頻中健康和諧發展。基于新媒體環境下不斷發展的主流文化與二次元文化,并非與傳統亞文化有著極大的不同,其主要特征為抵抗意義消減與反叛并在潛移默化中對主流文化進行擴編以及融合。例如“中國制造日”主題曲《天行健》的演唱者為虛擬偶像洛天依,以古風形式表達歌曲內容,尤其“工匠精神”與“中國歷史”相結合使“中國制造日”的知曉度得到擴大,縱觀短視頻觀眾留言發現,多數二次元用戶高度認同和贊賞這一表現形式。
(二)重視科學引導,實現商業化收編
相關研究者指出[8],如果想要整合亞文化表達方式,可采取不同方式,商業化收編就是其中之一。蓬勃發展的移動短視頻驅動資本市場對其展開商業化經營。換言之,就是挖掘移動短視頻中亞文化風格中的商業價值并將其包裝為商業產品后再推向市場。例如,爵士樂與搖滾樂在某個年代極具代表性,與商業市場相結合后漸漸弱化其自身附帶的反叛性風格并成為西方音樂的主導文化之一。現代移動短視頻中具有強烈的青年亞文化風格,此類視頻形式被作為現代時尚商品后,即使與其他視頻文化形式相比新奇性十足,但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眾多商品中的一類,以內容生成為主的文化語境因商業化收編發生變化,亞文化風格中不符合主流文化的元素也相繼被改造或去除,逐漸弱化具有反抗意識的亞文化風格,并在此基礎上轉為消費風格。但不可否認的是,消費風格具有典型的階級性與普遍性特征,此特征不同于青年亞文化中的顛覆性與反抗性,所以最后僅剩具有消費影響力的青年性。如果移動短視頻中青年亞文化風格被商業化收編并成為符合大眾消費意向的廣泛商品,必然會弱化對主流文化的反抗意識,自然而然會減弱或消退與主流文化間的沖突。此外,在此過程中還要打破圈層壁壘,除了需要亞文化圈層內核心人物發揮引導作用,更要借助如相關政策、部門、網絡平臺和網絡技術等多方力量的指引與支持,如此一來才能聚集不同空間力量,打破不同領域青年群體間的封閉狀態,促進青年群體的溝通交流,集結青年群體的力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青年亞文化破圈。
(三)重新明確定義,實施選擇性認可
事實上,官方意識形態收編另一層內涵即選擇性與有限性認可亞文化,最為重要的是篩選青年亞文化中契合主流文化的相關內容,再重新界定其定義以及通過主流文化價值符號闡述其內涵與存在的意義。如此一來,青年亞文化不僅收獲預期的經濟效益,更在某種層面上獲得社會與文化資本的認可。換言之,青年亞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與主流文化達成合作意向。例如,B 站是深受當前年輕群體喜愛的視頻網站,該網站主打二次元。2020 年五四青年節,B 站推出《后浪》視頻引發熱議,甚至在年末舉辦的跨年晚會上邀請著名琵琶演奏家與虛擬歌手《洛天依》聯合演繹《茉莉花》,觀眾對這一跨界合作感到驚喜。近年來,央視新聞、共青團中央、眾多高等院校等都在B 站開設賬號,大眾日常生活也開始被“萌寵”或“萌萌噠”等二次元流行語充斥;二次元網絡社區UP 主制作《鋼鐵洪流進行曲》播放量達到近600 萬,B站也購買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播放版權,很多網友都紛紛被傳統文化所吸引,實現了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高效融合。近年來,青少年在新媒體語境下運用二次元元素將民族轉至世界,學術轉至大眾,經典轉至流行,不斷擴展二次元受眾范圍,并在此過程中尋求與主流文化、人生觀、價值觀等的相通點,受眾也開始重新審視和欣喜地接受青年亞文化,實現文化交融。
四、結語
總之,短視頻生產者在現代網絡傳播背景下有意營造娛樂氛圍或制造淚點與笑點,促使受眾適應網絡傳播中因短視頻形成的青年亞文化。在隨處是中心、無處是邊緣的網絡社會中,窺探新媒介發展中的新文化以及探索新時期的精神需求與面貌。主流文化在面對全新發展語境與傳播機制中需樹立正確態度,基于包容、客觀、開放態度對青年亞文化進行審視,再采取強制性約束、商業化收編或選擇性認可等方式引導對話,最大限度地保證青年亞文化健康向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主流文化與短視頻行業相融并釋放出無窮潛力,在帶動社會和諧與進步的同時,營造更高層次的網絡娛樂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