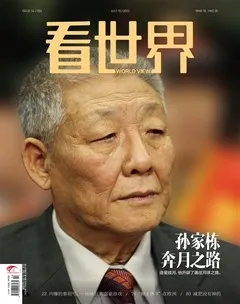日本核廢水,到底還是來了
費雪

5月26日,日本福島縣,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廢水儲罐
“海納百氚”,正在變成現實。
6月6日,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以下簡稱“東電”)已在基本完工的排海隧道內,注入約6000噸海水,開始持續兩周的設備試運行。
這意味著,日本正式排放福島核廢水的準備工作已接近尾聲。而根據日本官方給出的時間表,“排污入海”工程一旦開啟,將持續30年左右。從2021年4月日本政府計劃將經過處理但仍略帶放射性的核廢水稀釋后逐步排放入海以來,輿論場一直沸議不斷。而處于“風暴眼”的核心議題則在于,對受波及的各國來說,負面影響究竟會有多大?

5月26日,福島第一核電站,建設中的輸水管道
生態災難難以預估
日本政府方面稱,排海的核廢水對人體安全無害,少量的氚并不影響健康。東電在論及該水中的核素輻射劑量時,更曾形容,成人可以“每天喝兩升,持續喝一年”。
然而6月11日,面對太平洋島國專家建議日本在基建使用混凝土的過程中消耗核污水時,該國卻以“核污水或導致放射性物質氚蒸發,對人體有害”為理由,駁回了這一提議。
自相矛盾的表態,又一次引發外界的憂心忡忡。畢竟,在核廢水安全管理問題上,東電歷來存在令人難以放心的“信任赤字”。
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記錄,2011年,日本核事故發生后的第二個月,東電就曾向太平洋中排放了上萬噸核廢水,其中“放射性碘131超標100倍”。其后,東電還至少涉嫌導致了5起核廢水外泄事故。
在此情形下,科學界對東電“核廢水質檢合格的結論”提出了公開質疑。據《韓民族日報》報道,在“福島核廢水排放海外專家邀請討論會”上,太平洋島嶼國家論壇(PIF)科學家小組指出,東電只關注了64種放射性元素中的鍶-90、銫-137等9種物質,而對其余55種元素置之不理、未加測定。
更糟的是,早在2018年的一次檢查中,外界就發現,即使是被列為重點的鍶-90等放射性同位素,也在“處理水”中檢出殘留,某些監測樣本的輻射水平甚至高過安全標準2萬倍。
在海洋排放外,地層注入、蒸汽排放、氫氣排放和地下掩埋,都是可行選項。
此外,專家還批判,東電只提取了30升“處理水”樣本進行一次性測量,實際上無法充分代表待排廢水的實際構成和濃度,因此就已有數據不足影響“安全”的可能—更不必言,在東電的測量數據中還存在多個異常的可疑測量值,使數據本身的可信度也打上了問號。
那么,放射性物質入海,到底后果將會怎樣?日本排污地點的特殊性,決定了核廢水隨洋流擴散的速度會比較快,數年后就將蔓延至全球范圍。德國海洋研究機構也有研究表明,核廢水經汽化后進入大氣循環,還將隨云化雨,灑遍地球每個角落。
用日本環境經濟學專家、龍谷大學教授大島堅一的話做總結,那就是“一旦入海,未來的生態災難難以預估”。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日本選擇廢水入海的理由,官方說法是儲蓄罐不夠用了。
因為核反應堆堆芯熔化,造成殼體裂縫和滲液,導致需要存儲的污水遠高于預期—東電稱,按每天產生大約100噸核廢水的速度,到2022年10月,1000個儲罐容量飽和。而為了確保廢爐作業的空間,現在已無場地建設更多儲罐。
乍一看,核廢水排海屬于不得已的無奈之舉。但細究之下卻會發現,其實存在其他善法。首先就核廢水的整體消納來說,日本經濟產業省組織的專家組提出過5種方案。據了解,在海洋排放外,地層注入、蒸汽排放、氫氣排放和地下掩埋,都是可行選項。
日本科學界和民間團體也曾先后向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提出多種比排海更為合理的方案,譬如日本化學工程師、日本原子力市民委員會委員川井康郎的“砂漿固化”法,但可惜都未被采納。
其次,就核廢水的過濾來說,除氚作為氫的同位素難以處理外,其他62種放射性元素在技術上,都是可以被清除至達標的。即使是最難分解的氚,市場上也有一家名為Kurion的公司已開發出除氚系統。
但日本經產省卻在2016年得出如下結論:在福島廠址上,沒有可用的去除氚的方法。并且,選擇了效果不甚理想的“多核素除污設備”(ALPS)過濾其他放射性核素。
據悉,東電執行的,是僅將核廢水中所含1000多種放射性物質里的30種作為檢測對象的極寬松清除標準—即只要這30種放射物的含量總和低于某個限度,就視為“達標”。可2020年8月的數據顯示,處理后73%的核廢水中,放射性元素仍然“超標”,留待進行二次過濾。
而截至今年5月18日,東電官網數據顯示,133.31萬立方米核污水中,ALPS污水只占30%,多達70%連第一次過濾都未實現。在核污水排海已進入倒計時的當口,外界不得不疑竇叢生—倒進大海的廢水,究竟能有幾分“干凈”?
在這背后,“成本”,則是一切不合格的原因。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估計,核災難的清理費用可能最終達到6600億美元,約合日本GDP的13%。在過去10年中,僅儲存核廢水這一項,每年便至少花去9億美元。

1月31日,福島第一核電站,用處理過的核廢水養殖的比目魚

日本排放核污水,將讓全球漁業蒙上陰影。圖為日本漁民捕捉鮭魚
所以,安裝成本約10億美元、運行費用每年需數億美元的除氚設備,不可能出現在日方考慮之列。最終決定將核污水排放入海,也并非因為這是最利于環境保護和人類安全的做法,而是它“所需時間最短,花費也最少”。
自食苦果
東電曾承認,今年5月在福島第一核電站港灣內捕獲的海魚許氏平鲉,體內放射性元素超標,銫的含量達到每千克1.8萬貝克勒爾(放射性活度的國際單位),超過日本《食品衛生法》所規定的標準值(每千克100貝克勒爾)180倍。
如果日本正式按下核污水排海的啟動鍵,太平洋海洋生態環境的污染幾乎板上釘釘,全球漁業由此也將蒙上陰影。
為此,今年太平洋諸島國曾敦促日本推遲釋放福島核廢水,避免對這些國家賴以生存的漁場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在6月12日下午,數千名韓國漁民舉行“先不打漁了,去首爾”的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強烈抗議日本政府將福島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受害的將是太平洋里的所有生命,和依靠大海生活的所有漁民。”來自釜山、全羅南道等地的漁民代表如此說道。
反對的疾呼聲音,同樣從日本國內傳出。2021年日本政府宣布將核污水排海的計劃后,其國內民眾就不曾間斷抗議集會的舉行。
日媒4月發布的問卷調查顯示,51名福島核事故相關地方市町村行政負責人中,有25人對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計劃表示“不接受”和“比較不接受”。其主要理由中,就包括了“很多漁業人士反對”。
到6月7日,即日本排海設備試運行的第二天,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在地區的當地漁業組織,向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又一次提出反對,對日本政府的措施傷害了漁民利益表達不滿。
“排污會再次打擊福島漁業,停滯甚至消失都是有可能的。”福島漁民的擔憂不是杞人之思,當地漁業銳減的出口數據,業已證明核污水對經濟帶來的致命影響—福島三大漁業協會2022年捕撈量只有5500余噸,僅剩福島核事故發生前的兩成。
畢竟眾所周知,核素入海會通過生物富集效應影響海洋生物,一旦人類食用了受污染的魚類,就有可能造成健康損害。這一事實,不是日本政府通過在東京奧運會和G7廣島峰會上提供福島農產品和水產品,就可以輕松進行國際公關來“洗白”的。
根據東京大學對亞洲和歐美10個國家的3000名居民展開的調查,各國民眾普遍對福島食品的安全性表示憂慮。日本之外的民眾中,回答“很危險”和“有點危險”的受訪者超過六成,其中韓國達93%、中國為87%。
現在,因擔心核廢水污染,韓國消費者正大量搶購囤積鹽和海產品。韓國民意調查機構Research View5月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85%的韓國民眾反對日本排核污染水,70%的人計劃在核污染水排海后,減少食用海鮮。

5月31日,韓國釜山,在野黨成員在海邊示威,反對日本核廢水排海
福島漁業“雪上加霜”,整個日本漁業也受名聲所累,面臨嚴重危機。
出于保護民眾食品安全和身體健康的要旨,據統計,已有12個國家和地區對福島食品采取進口限制。
韓國海洋水產部副部長宋相根聲明,即使福島排海核污水的安全性在科學上得到證明,但只要福島水產品的安全性未得到驗證,禁止進口措施就不會解除。
福島漁業“雪上加霜”,整個日本漁業也受名聲所累,面臨嚴重危機。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布的2022年漁業及養殖業生產統計數據顯示,包括養殖在內的捕撈量較上年減少7.5%,捕撈量連續2年減少,創下有可比數據的1956年以來的新低記錄。
而一旦核污水排海,可以預見,其負面影響還將如“多米諾效應”般,逐漸延伸至其他產業。不僅所有涉及海洋食品類的產業,如漁業、海鮮類產業、海鹽產業出現坍塌,食品行業、藥品保健品行業也會受到波及。
6月14日,話題詞#SK-II神仙水生產地涉嫌核污染#沖上微博熱搜。有消息稱,日本鴨川與琵琶湖匯合的岸邊,有區域堆放了大量產自福島核事故中受輻射樹木的木屑,其中含放射性物質銫。公眾由此質疑,水質來源和全球生產線均位于琵琶湖的護膚產品“神仙水”,是否也遭到核污染。
對此,寶潔公司不得不進行緊急公關,就產品安全性做出無輻射承諾。可以想見,面對消費者的疑慮,未來此類事件將逐漸增多,并影響日本企業的全球形象。
無法充分知情,是產生猜疑的根源。為節約成本而我行我素的日本,是放任這種不信任潛滋暗長的第一責任人。現在看來,在國家經濟上受傷最深的,也將是它自己。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