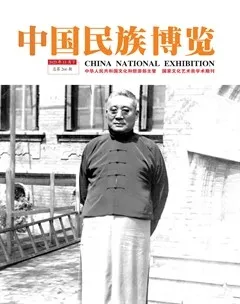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
【摘 要】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特征在孔子對于律法、政治等方面的理解上都有所體現。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即在推行立法與司法期間將儒家“德、利”思想作為中心。儒家思想出自春秋時期,但這一時期的儒家并沒有受到當時統治者的認可,甚至是處在備受壓制的境地。古時候戰爭頻繁、思想動蕩,將儒家提倡的“文質”論作為當時社會的運行內核,為統治者提供獲得豐功偉績的思想武器,是極為不符合實際的。而法家思想則在春秋時期中逐漸嶄露頭角,諸侯統治者也更喜歡法家思想,受此影響儒家提倡的“文質”論進一步陷入困境。
【關鍵詞】春秋戰國;儒家思想;“文質”論
【中圖分類號】K01;K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22—018—03
春秋戰國時期,將“緣法而治”視作中心思想的法家主張逐漸成為當時的指導思想,威震一時。
但春秋戰國諸侯勢力的逐漸增強、社會復蘇后,“緣法而治”便無法與當時的社會統治、民眾需求相契合,急需一套全新的意識形態來應對社會一些客觀存在的難題,緩解各種社會問題。
以此制定一套與統一制封建國家相契合的理想政治體系成為了重中之重。儒家“文質”論思想便在這時出現于春秋戰國的歷史之上,由此開啟了長達兩千年的思想統治[1]。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所提倡的儒學“文質”論思想是受到時局影響變革后的新儒學理念。
其在原有的哲學理論基礎上結合了道、法與其他家學說,將家庭倫理與社會形態統統歸入思想統治的范疇,充分結合政權、夫權與族權,將封建倫理道德與封建統治相聯結,進而順應春秋戰國時期的發展進程,滿足各方諸侯的政治所需。
一、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戰國時期的“文質”論思想核心要義
(一)“文質”以禮為基
“禮”是儒家規定的人生信條與國家治理標準之一,在仁義禮智信中,“禮”具有極為關鍵的地位,其也極大程度上體現出了早期儒家思想的治國理念。在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體系中,利益等級與名分是其基本的兩大特征,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則是寄期借助“禮”來對社會關系進行調節,從而實現相處和諧之目的[2]。這也使得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體系中一直彰顯著等級有序的儒家信條。
君臣關系方面要重點加強“忠君”思想在,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中也提出要嚴格避免出現損傷帝王尊嚴的行為,這種行為存在就會被判定是犯罪,并且對于此類罪名的懲罰會遠重于同等級的罪名。在親子關系方面,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倡導:兒女要對父母懷有感恩之心、孝順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倡導:夫為妻綱,妻子要盡到相夫教子的職責,同時男性在家中具備決定財產分配與婚姻的權利。上述規定所展現的事實上都是戰國時期儒家“文質”論思想中“三從四德”的基礎思想特質。
(二)“禮”“法”兼顧并施
除等級有序、以禮待人之外,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還指明了“禮”“法”兼顧并施的思想特點。孔子在戰國時期所倡導的儒家“文質”論思想認為:“治國者若只重視社會律法便會出現很多問題[3]。”其思想體現在如下兩方面:一方面,法律不足以全面地對社會上各項事務的細節管制到位,部分管制不到的地方則要取決于百姓的道德與禮儀展開判斷。另一方面,“依法治國”的思想觀念也無法控制所有的行為,因此就需要禮來教導世人,提升百姓的道德意識進而有效避免犯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禮”“法”兼顧并施的思想特點不僅是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指導思想,也是“文質”論對于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的集中詮釋,“法”時刻表現“禮”的仁治,而“禮”也時刻維護“法”的尊嚴。
(三)慎重行法
“慎重行法”是戰國時期儒家“文質”論的又一種思想形式,這也奠定了早期儒家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中的“施仁政”觀念。“不獨親其親,獨子其子”,這一哲學觀念就充分表明在嚴苛的統治與法律約束下,還需要加強對社會大眾的區別關注。“律法森嚴最終只會導致百姓揭竿而起,同心協力推翻君主暴政。”因此,在戰國時期儒家的“文質”論思想中,孔子也深刻吸取了前朝的慘痛教訓,認為治國者要在量刑方面極為注意:
第一點,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認為:拷問時要謹慎,同時也要對囚犯拷問進行限制,但若出現“失禮”行徑,拷問者便要承擔法律責任。并且拷問還應當受到很多規矩的限制,要依靠嚴謹的證據為基礎,不然將會以“故失”論罪。第二點,對于老弱病殘孕之犯罪應慎重行法。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認為:針對這類群體其若是犯罪,可以適當減輕懲罰或是免除。若是囚犯已經定刑,同樣要謹慎對待,若是囚犯存在質疑,判官要在其他人證在場的情況下重新審理,同時確保提供囚犯所需的生存保障,行法時要慎重使用笞刑和杖刑,而死刑更加需要慎重,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執行完成,否則國家要追究相關責任。量刑時也必須要慎重確定,根據違法程度進行使用[4]。
二、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戰國時期的“文質”論治國思想
在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中,“文質”論治國思想進一步發展。雖然其思路體系發展時期較短,但在倫理道德觀念的影響下,“依禮制律,引禮入律”的“文質”論思想卻也逐漸成為了儒家思想后續的哲學精髓之一。后世編撰的《開皇律》《唐律疏議》等封建法典都是以“文質”論治國思想作為藍本的。
“依禮制律,引禮入律”的“文質”論治國思想也漸漸發展成后世歷朝歷代模仿的基礎。戰國時期的“文質”論治國思想其最大特征便是:統治者一定要堅守“以利為剛”的指導準則。在此思想基礎上制定的治國思想應“一切皆準乎禮”,即:“禮與律相互融合。禮借助律表達觀點,律以禮為核心[5]。”在戰國時期的“文質”論治國思想中,孔子所堅守的“禮法合一”也為“引經斷獄、以禮入法”的哲學觀念提供了發展基礎,從這一角度來看,戰國時期的“文質”論治國思想也標志著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終形態。
三、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戰國時期的“文質”論律法思想
(一)立法“文質”論思想
在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體系中,孔子所提出的“文質”論認為:思想上混亂一定會造成政治混亂,因而,為實現中央集權制度,必須將統一思想的工作進行完善。由此推崇的思想體系通過禮法約束百姓,與當時的治國方略相統一,預防暴政出現。因此,在戰國時期的“文質”論律法思想體系中,孔子在“律、令、科、法、章、句、經、義”等立法形式上,都在強調“禮”“法”兼顧并施這一基本思想原則。雖然孔子所提出的“文質”論并不被各諸侯所推崇,但春秋戰國時期的儒生卻十分崇尚立法“文質”論思想,普遍采取儒家經典對法典內容進行注釋[6]。
(二)司法“文質”論思想
在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發展進程中,春秋戰國時期的司法制度也逐漸與儒家“文質”論形成對立格局。孔子所提出的“文質”論認為:若是在審判時缺少清晰的規定,就可以直接借助儒家經義當做司法定罪量刑的評定準則。這樣的司法“文質”論思想在《春秋》——“引經”部分也有所體現,這樣的司法“文質”論思想也被稱之為“春秋決獄”。自此之后,孔子所提出的“文質”論思想便逐漸開始滲透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司法領域中,這也使得司法“文質”論思想進一步打破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對于立法、司法觀念的控制格局。雖然“春秋決獄”的儒家經義看似合理,但因時代背景所限,導致其權威性依舊不能夠高于法家思想之上,從而直接變成國家律法的根源[7]。
四、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戰國時期“文質”論思想的后世影響
(一)戰國時期“文質”論思想的后世影響——刑法
《唐律疏議》和《唐六典》是唐代法律法規中的集中代表法典,從《唐律疏議》和《唐六典》中都能夠看出立法與禮法的融合互通,唐太宗李世民與其父親李淵的統治思想不同之處則在于,李世民通過傳統儒家理論與國家刑法之間的辯證性結合,逐漸衍生出一套以“三綱五常”為基礎的唐朝法典,這樣禮法并重指導思想,在現代的法律制度中,卻早已不復存在。
刑法方面的儒家化表現在新刑法的制定、增設罪名與形式原則層面。為了使中央集權穩定,漢朝不斷對新律法進行完善。除此之外,漢朝統治者為了加強皇權,加大力度鞏固了權威,同時還編寫了《左官律》、阿黨附益之法等類似的律令。針對罪名,漢朝還設置了一定數量的嚴重罪責。如:漢朝法律列舉出了欺騙、誣陷與誹謗等一些類罪責,根據上述罪名能夠發現,統治者不光規定一般百姓不可威脅皇權,還要在內心深處絕對服從皇權統治。
《唐律疏議》云“德禮為政教本,刑罰為教用”,明唐法之大要,德刑重而禮法合也。唐太宗用大體寬仁,詔納違經諸典,著之刑書。愿導之以經義,導諸刑罰。唐實治刑獄,嚴如唐律以量罪,守法者絕威強。其在政治文化,唐皆世道隆盛,此時國家非徒富民強市如潮,所以固本也。唐太宗在位,亦漸修唐法于空前之高,是時法非乃國之政刑民法,備極詳矣。
今每聞成言十惡不赦,惡正古之十大罪也。唐十兇之制,起于魏、晉、北齊,唐因而完之以為詳法者,皆當危立階級之利,犯儒術者也,故十罪皆入于《唐律疏議》,而以重擊其罪。唐刑法十惡之制,其雛形宜追魏晉南北通行《北齊律法》。《齊律》之本,唐刑者,惡刑之意也[8]。
唐代刑法典中的“十惡”制度,其雛形最早可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通行的北齊律。以北齊律為基礎,對唐朝刑法中惡行方面的內容進行了更細致、更完善的法律制度優化。但《北齊律》中的“十惡不赦”,卻把制度性規定直接指向了當時社會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由此引出儒家傳統思想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與傳統宗法相抵觸,或與國家政法相抵觸的現象。
然《齊律》十惡不赦,則直指其制度之封建以統治之,亦引得當時之儒術、宗法與國家之政法相亂者也。《唐律疏議》乃唐六典集中為典,自《其疏論》及《典》皆見立法與禮相通,太宗與其父淵異道則在,世民因傳儒理與刑法之辨合,稍衍以為“三綱五常”基本唐法,如是而重指導之,當今法制之中,久不復存。
(二)戰國時期“文質”論思想的后世影響——刑罰
漢朝初期,文帝、景帝充分吸取秦王朝快速滅亡的慘痛教訓,多次致力于減輕刑事處罰,在漢文帝時期,提出將三種肉刑廢除,同時這些建議統統被漢文帝接受,由此可知當時統治者急于減輕刑罰并且漢朝法律和儒家思想相結合。漢景帝傳承了文帝改進刑罰的意識并且不斷深化,兩度削弱笞刑,并將宮刑廢除。唐五刑謂律令之科,杖、徒、流及死刑五罰也,五者相連,保刑者致于法,然而罪不及十惡,則可因贖而免之,不過贖罪而可用之上階也。唐法制得儒家傳思之意,刑罰輕于它世,唐之“輕刑慎罰”之法也。唐法尚有保辜之制,其法謂兩爭傷者,所加害者救之,而其制蓋甚廣,唐民外國友人,至有家畜。保辜之制不徒安人身心,亦降其所受刑罰,儒者仁慎之法也。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的儒家“文質”論思想始終都是封建社會影響下所形成的思想觀念與哲學體系,其無法避免自身存在的特有時代特征,就現代啟示而言,如何分析理性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觀念,并在其中攝取營養才是完善現代法律理念的必備之舉。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可以為現代法治建設進程提供一些借鑒,雖然我國現代社會的律法條件、律法環境都相對健全,但如何實現“善治”與“良治”格局則依舊是一種需要解決的現實因素。
參考文獻:
[1]秦鵬飛.儒家“公私”思想的人倫關系維度——兼論“差序格局”的社會倫理含義[J].廣東社會科學,2023(3).
[2]郭萍.儒家自由主義與自由儒學——論儒西文明對話的兩種思想形態[J].文史哲,2023(3).
[3]李雙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儒家思想源泉[J].西藏發展論壇,2023(2).
[4]余治平.董仲舒賦予漢制“更高的文化理想”——“2022中國·衡水董仲舒與儒家思想國際研討會暨中華孔子學會董仲舒研究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開幕致辭[J].衡水學院學報,2023(2).
[5]蔡方鹿,張靜遠.儒家經典詮釋的有益嘗試——評《“樊遲學稼”詮釋史》[J].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3(1).
[6]陳立勝.儒家思想中的“內”與“外”——“內圣外王”何以成為儒學之道的一個“關鍵詞”?[J].現代哲學,2023(2).
[7]楊美玉.明王道 重五常:儒家思想下的金代中期教育研究[D].通遼:內蒙古民族大學,2022.
[8]保羅·那比爾.“公子友如陳”:《公羊傳》與“親親”“尊尊”儒家思想[J].衡水學院學報,2022(3).
作者簡介:秦穎(1995—),女,漢族,山西運城人,碩士,長治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助教,研究方向為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