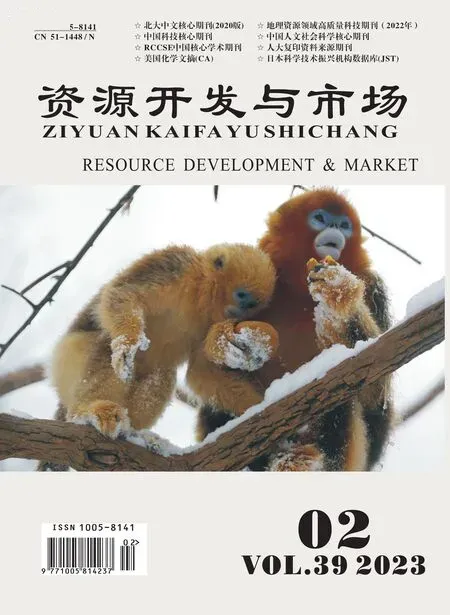川西北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質量評價與優化研究
席 歡,朱艷婷
(四川省自然資源科學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0 引言
鄉村生態人居環境,是以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為基本原則,運用生態系統的生物共生和物質多級傳遞循環、再生原理,根據當地環境和資源稟賦,以鄉村綠化規劃為引領,結合系統工程方法構建形成的自我凈化、零污染、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豐富的人居環境[1]。20世紀50年代,薩迪亞斯提出了“人類聚居學”的研究構想,認為人類聚居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是人類與環境最密切、最具體的物質交換與情感交流的地理空間,并按照性質的不同,將聚居分為鄉村型聚居和城市型聚居兩大類[2]。20世紀以前,國外學術界聚焦于城市人居環境研究,對鄉村人居環境研究則較為忽視。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農村人居環境研究日益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視角轉向農村。Farokh Afsha提出應該關注小型人居(小城市、集鎮、村莊)和農村地域的研究[3]。
近年來,特別是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大背景下,國內眾多學者從經濟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多學科、不同研究視角及不同地理單元對中國鄉村人居環境進行了研究。胡偉等在對村鎮人居環境內涵、優化原則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運用系統優化的思想,以縣或鄉鎮為地域單元,提出了一套農村人居環境優化系統[4]。郜彗等基于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建立了一套由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居住條件和經濟發展5個亞目標層組成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的評價指標體系,對中國省域農村人居環境建設情況進行了評價,并提出了發展對策[5]。于法穩在闡述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時代價值,剖析當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所面臨的形勢與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對策建議[6]。然而,截至目前,針對我國重點生態功能限制區的研究相對偏少[7,8]。本文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限制區——川西北地區為研究地理單元,通過實地調研、問卷調查等方法,運用層次分析法(AHP)對該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進行初步探索研究,在分析該地區鄉村人居環境生態保護形勢與問題的基礎上,提出優化策略和建議,以期為我國重點生態功能限制區 川西北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
1 研究區域概況
川西北地區位于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接壤處,平均海拔在3000—4000m,有平原、峽谷、高原、濕地等多種地形地貌,區域內自然資源豐富,生態環境地位特殊,毗鄰“三江源”國家級森林公園,是長江、黃河上游的重要組成部分。金川縣是川西北地區一個以農業為主的高原山區縣,全縣氣候得天獨厚,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年均日照2435h,土地肥沃,光熱充沛,具有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的良好生態環境[9]。甲咱村位于金川縣西南部,距縣城12km左右,整個村莊依山而建、臨水而居,全村土地總面積8.2km2,耕地面積61.86hm2。下轄2個村民小組,2019年末全村常住戶數323戶,常住人口825人。甲咱村有藏、羌、回等14個民族聚居,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占75%左右。甲咱村農業農村基礎差、底子薄、發展滯后,主導產業支撐不強,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較低,農村基礎設施提升難度較大,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鄉村產業發展、生態保護等方面的人才短缺問題突出[10]。因此,以甲咱村為例探討重點生態功能限制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建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 生態人居環境指標體系構建及評價
2.1 指標體系的構建
對生態人居環境質量進行評估,首先要建立指標體系。本文根據吳良鏞人居環境科學導論的研究成果[11],遵循科學性、代表性、可量化、方便獲取等原則,結合研究區域特色和實際情況,運用理論分析和專家咨詢相結合的方法,構建川西北聚落生態人居環境指標體系。在總的體系下設自然環境、社會生態、經濟支撐等3個子系統,每個子系統下設次級子系統。
在調研過程中,課題組對金川縣甲咱村進行實地調查走訪和問卷調查,結合研究區域實際情況,根據2017—2020年《阿壩州統計年鑒》等數據來源,篩選出48個能夠體現鄉村生態人居環境狀況的初選指標。咨詢人居環境方面的專家[12],對初選指標進行進一步的調整和優化,最終建立一套包括16個指標的川西北鄉村生態人居環境質量評價體系(表1)[13]。

表1 川西北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指標體系Table 1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Northwest Sichuan
2.2 評價過程
無量綱化處理。本文在分析金川縣甲咱村2016—2019年生態人居環境發展的3個子系統及其包含的次級子系統時發現,由于每個指標性質、形式、單位均不一致,且有些指標是相對來說正向的(比如收入、養殖量、用地面積等),有的指標相對來說是負向的(比如自然災害發生頻度),在進行特征選擇之前,應先對研究使用的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以使表征不同屬性(單位不同)的各指標之間具有可比性。計算公式如下:


表2 無量綱化后的川西北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指標體系Table 2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human settlements in Northwest Sichuan after dimensionless
指標權重設置。指標權重確定的方法通常有層次分析法(AHP)、網絡分析法(ANP)、德爾菲法(Delphi)、熵值法、二項系數法、環比評分法等,本文選擇層次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是由美國運籌學家T L saaty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該方法將主觀比較和判斷用數量形式進行表達和處理,具有高度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廣泛的適用性,是一種簡便、靈活實用的多準則決策方法。本文在建立遞階層次結構模型(構建了包含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的評價體系框架)的基礎上,構造各層次中的所有判斷矩陣并進行一致性檢驗。
構造判斷矩陣。構造判斷矩陣是層次分析法中最關鍵的一步。針對直接賦予指標權重沒有統一標準且比較困難的問題,采用1—9標度法對矩陣中兩個因素進行比較并標出分值(表3),再邀請專家進行打分評比,對兩兩指標之間進行賦值比較,通過矩陣計算,A、B1、B2和B3得出第一層和第二層的判斷矩陣(表4)。

表3 判斷矩陣中指標分值確定標準Table 3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index scores in the judgment matrix

表4 A、B1、B2、B3判斷矩陣Table 4 Judgment matrix of A,B1,B2and B3
一致性檢驗。層次分析法中判斷矩陣有時候會有不一致的范圍,需要通過一致性檢驗來校驗。一致性檢驗步驟和方法如下:

式中:CIi為一致性指標;i為A、B1、B2、B3判斷矩陣;λmax是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值;n為矩陣階數。

式中:CRi為一致性比例;RI為隨機一致性指標值。當CRi<0.10時,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是可接受的,λmax所對應的特征向量即為權重;當CRi>0.10時,應考慮修正判斷矩陣。
從表5可見,CIA、CIB1、CIB2、CIB3的一致性比例分別為0、0.047、0.014、0.057,均小于0.10,說明表4中A、B1、B2、B34個判斷矩陣均通過了一致性檢驗,λmax所對應的特征向量經歸一化后(使向量中各元素之和等于1)即為排序權重(表6)。

表5 隨機一致性指標值Table 5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value

表6 評價指標體系各指標權重值Table 6 Weight values of each index i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2.3 綜合得分
將數據標準化并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后,根據評價對象的特點計算甲咱村生態人居環境綜合得分。計算公式如下:

甲咱村生態人居環境質量指數及準則層一級指標得分結果如圖1、圖2所示。從圖1、圖2可見,2016—2019年,目標層A(生態人居環境質量)綜合得分是0.89、0.90、1.06、1.17;準則層B1(自然環境)得分為0.33、0.30、0.34、0.39;B2(社會生態)得分為0.28、0.30、0.37、0.38;B3(經濟支撐)得分為0.28、0.29、0.36、0.40。對以上數據分析發現,甲咱村2016—2019年生態人居環境質量的綜合得分呈現持續上升態勢,從2016年的0.89增長到2019年的1.17,生態人居環境質量不斷提高,可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城鎮化進程加快,甲咱村生態人居環境質量總體持續向好發展。

圖1 2016—2019年甲咱村生態人居環境質量評價結果Figure 1 Evaluation results of ecologic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in Jiazan Village,2016-2019

圖2 2016—2019年甲咱村生態人居環境準則層評價結果Figure 2 Evaluation results of Jiazan Village's ecological habitat environment criteria,2016-2019
3 評價結果及分析
3.1 自然環境子系統
自然環境準則層包含大氣質量優良率、自然災害發生頻率、人均公共用地面積、地表水質達標率、垃圾收集率5個指標(圖3)。由圖3可知,除自然災害發生頻率這一指標外,其余指標均顯示持續增長,而自然災害發生頻率指標是負指標,由于研究區域整體處于青藏高原東麓,川西北干旱河谷地帶,地質不穩定,地災活動具有不確定性,屬于自然原因。人均公共用地面積由2016年的0.83增長到2019年的1.02,年均增長率為23%;大氣質量優良率保持在99%左右;地表水質達標率由2016年的0.99增長到2019年的1.04,年均增長率為5%;垃圾收集率由2016年的0.78增長到2019年的1.32,年均增長率為69%。綜合來看,自然環境質量總體上得到一定的改善,生態環境及農村面源污染等趨勢得到了一定的緩解,村民環保意識逐年增強。

圖3 2016—2019年甲咱村自然環境指標層評價結果Figur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index layer of Jiazan Village,2016-2019
3.2 社會生態子系統
社會生態準則層包括人均居住面積、人口數量、燃氣普及率、人均娛樂活動參與次數、每百人擁有醫護人員數量、學校數量、人均用電量等7個指標(圖4)。由圖4可知,人均居住面積由2016年的0.9增長到2019年的1.08,家用燃氣普及率由2016年的0.67增長到2019年的1.33,人均用電量由2016年的0.91增長到2019年的1.05,學校包括幼兒園、中心小學校、傳統文化傳習所等3所,每百人擁有醫護人員數量由2016年的0.9增長到2019年的1.1。綜合來看,無論是人居生活環境、基礎設施配置、教育醫療發展、隨著社保保障體系不斷發展完善,整體水平逐年提高,特別是近年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進一步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

圖4 2016—2019年甲咱村社會生態指標層評價結果Figure 4 Evaluation results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indicators of Jiazan Village,2016-2019
3.3 經濟支撐子系統
經濟支撐準則層主要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鄉村旅游收入比例、戶均養殖畜禽數量、農作物畝均產量4個指標(圖5)。由圖5可知,隨著近年來經濟社會整體不斷發展,鄉村產業發展不斷壯大,經濟穩步向上發展,但是由于2018—2019年金川縣參與南水北調后期工程,修山開路,整條汶馬公路在建,造成交通不變,加上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災害的影響,對旅游收入造成一定的影響,有所波動。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6年的0.81增長到2019年的1.24,年均增長率為53%;戶均家庭畜禽養殖數由2016年的0.82增長到2019年的1.18,農作物畝均產量由2016年的0.67增長到2019年的1.31。鄉村經濟持續發展,但沒有支柱產業,第三產業發展有待加強。

圖5 2016—2019年甲咱村經濟支撐指標層評價結果Figure 5 Evaluation results of economic support indicators of Jiazan Village,2016-2019
4 鄉村生態人居環境面臨的問題
川西北地區氣候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城鎮化建設的推進促使川西北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面臨一系列新舊問題和嚴峻挑戰。具體表現在:①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安全形勢依然嚴峻。川西北地區是國家重點生態功能限制區,近年來當地既要發展農、林、牧業等第一產業,又要興建礦業、水利和交通等項目,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環境問題。長期以來,對森林資源的不合理采伐,致使森林覆蓋率下降,資源面臨枯竭。由于草場沙化、退化嚴重,進一步加劇了該地區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②新的環境問題逐步顯現。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區域內基礎設施建設、礦山開發開采、農業農村設施設備改擴建等日益加強,在改善區域內鄉村生產生活條件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環境問題,對鄉村生態人居環境和村民身體健康帶來潛在的危險;大量的固體廢棄物和生活污水造成的面源污染呈逐漸增加態勢;受全球氣候變暖影響,川西北地區氣溫呈現持續上升態勢,降水的年際變化逐漸增大,導致冰川融化、濕地退化、草原沙化等問題日益嚴重,干旱化加劇了河谷區的植被退化,地區生態環境脆弱性日益增強,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威脅日益增大。③農村面源污染問題日趨凸顯。目前,農業面源污染的危害日益凸顯,導致耕地退化、農村和農業內部環境惡化,嚴重影響了鄉村臨近河流水質、村民飲水安全、農產品質量與食品安全等,農業面源污染已成為影響鄉村生態人居環境質量的重要污染源。④基礎設施建設有待提高,公共服務保障能力有待提升。該區域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經濟相對落后,導致村鎮生活污水集中處理難度大。對鄉村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的政策傾斜力度不夠。
5 優化策略及建議
川西北地區作為我國重點生態功能限制區,二三產業發展受到政策約束,并影響了部分垃圾處理企業的建設和產業發展。一方面,生態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污染治理工作主要依賴于政府的主體作用及財政資金支持,經濟成本高,可持續性差;另一方面,群眾的主體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群眾環保參與意識有待繼續提高,試點示范推廣宣傳效果有待提升。總體來看,川西北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建設面臨的形勢越來越嚴峻,經濟壓力越來越大,可持續性發展能力亟待加強。川西北地區鄉村生態人居環境建設需要加強規劃引領,以人工濕地建設引導垃圾處理向無害化、零污染方向轉變,推動鄉村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發展,充分發揮群眾的主體作用,提高群眾環保參與意識。
5.1 加強鄉村生態人居環境規劃
川西北地區鄉村大多依山而建、臨水而居,房屋修建布局較為散亂,缺乏科學布局規劃。房屋廁所改造、生活垃圾和畜禽糞便處理、生活污水處理、村容村貌整治等雖然取得了不錯的進展和效果,但仍需持續推進,并迫切需要規劃引領。加強鄉村生態人居環境規劃,應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核心,科學布局房屋及鄉村基礎設施,暢通鄉村內外生態廊道聯系,著重構建鄉村污染物生態自然處理凈化系統。
5.2 加強垃圾無害化處理和人工濕地建設
在城鎮近郊及周邊的村落,采用“戶分類村收集鄉鎮轉運縣處理”的垃圾處理方式;在地理單元相對獨立的村落,采用“村收集鄉鎮轉運中心鎮處理”的垃圾無害化處理方式;在邊遠地區、高半山區等交通不便的村落,以中心村為單元,采用“統一收集就地分類綜合處理”的垃圾無害化處理方式;加大鄉鎮垃圾填埋場建設。
構建鄉村污染物生態自然處理凈化系統,可將建設小微類型人工濕地作為川西北地區聚落加強生態人居環境保護和環境污染治理的核心項目。相對于垃圾處理廠或其他垃圾集中處理點而言,人工濕地對生活垃圾、畜禽糞便和生活污水的處理具有能耗低、投運成本低、便于管理和維護、能夠產生一定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收益等優點。但目前在高海撥地區建設人工濕地仍舊存在一些問題制約,例如建設周期較長、設計難度大、核心技術仍不完善、關鍵植物泥炭蘚自然繁育困難等問題,需要著重加強核心技術攻關,組織科研力量和技術團隊提供長期科技服務支撐。
5.3 推動產業生態化發展
發展“農業+旅游”“農業+康養”“農業+文創”等產業融合發展、生態化發展,扶持培育一批觀光度假、休閑避暑、農牧體驗、民俗風情、生態康養、研學旅游等特色產業和業態,促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立足獨特的生態文化旅游優勢,按照全域旅游全域景區化定位,堅持生態優先、尊重自然的理念,加快全領域建設、完善全產業鏈條、強化全方位營銷,加快鄉村旅游發展步伐,培育鄉村發展新動能,增強鄉村產業支撐能力。深入推進“交通+旅游”融合發展,加強旅游通道建設。加強旅游主動脈交通道路建設,切實推進客源地與旅游目的地之間的交通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