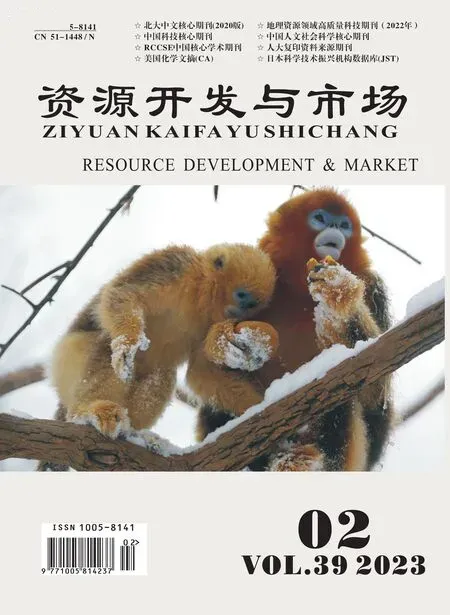旅游援疆政策量化評價與多元路徑分析
路 雯,白 洋,譚李娜
(1.新疆大學 新疆歷史文化旅游可持續發展重點實驗室,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2.新疆大學 旅游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
0 引言
對口援疆是黨中央扶持新疆社會發展的重要政策舉措,2010年的全國對口援疆工作會議拉開了新一輪援疆序幕,產業援疆成為新疆跨越式發展的關鍵著力點。2015年的全國旅游援疆工作會議確定了旅游援疆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工作目標等,國家開始探索富有旅游特色的援疆工作模式。隨著旅游興疆戰略的持續推進,旅游業逐漸增強了新疆經濟的內生動力和發展韌性。2021年全國文化旅游援疆工作會議召開,旅游援疆已成為對口援疆的重要領域。自2004年廣東省政府發布《關于加強廣東省援藏援疆交流合作工作的總體方案的通知》起,援助方與受援方層面結合自身優勢與地方實際,通過動態激勵與靜態管理,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旅游援疆政策。旅游業是新疆特色優勢產業,在“產業援疆,旅游先行”共識下,國家部委、援助省市持續深化拓展旅游援疆方式,實現新疆旅游業提質增效。面對區域旅游協調發展和旅游援疆精準化幫扶的雙重政策契機,亟需實現旅游援疆工作的重心轉移與結構轉型,厘清旅游援疆政策的內在邏輯,探究旅游援疆的政策力度、沖擊程度和實現路徑,對于新時期新疆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援助理念源于發達國家(地區)對欠發達國家(地區)的幫扶措施,通過援助保障受援地發展[1]。國外援助研究多指某個國家對本國內經濟欠發達地區實施經濟援助等措施[2-4],而國內研究同時涵蓋了對外[5,6]和對內[7]援助。區別于西方援助性質,中國援助具有經濟合作與對口支援的雙軌制屬性[8],雙方政府地位平等、互惠互利。對口援疆工作發軔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環境,在實施過程中不斷改善革新[9],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援疆的實踐探索和效果評估,研究內容多為醫療援疆[10]、教育援疆[11]、文 化 援 疆[12]、科 技 援 疆[13]等,研 究 方 法包括定性描述、實地調研[14,15]等,也有學者通過計量模型[16]探究援疆政策的實施效果。綜上所述,以往研究多從單一視角分析對口支援的實踐效果,多集中在對策、經驗和展望等理論認知,缺乏理論與實證結合的系統分析,政策量化評估體系構建鮮有涉及。政府是旅游援疆政策實施的主導力量,為政策實施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根據DSR模型歸納旅游援疆政策的作用機理,分析在外部環境驅動下的政策演變和自我調節,運用PMC指數模型、VAR模型、fsQCA軟件分析旅游援疆政策的驅動力、狀態和響應間的復雜關系。
1 研究設計
1.1 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解釋變量:政策力度計量是政策效果評價的難點,已有研究多用專家主觀評價賦值政策力度[17,18]。近年來,較為客觀的PMC指數模型得到了廣泛應用。因此,本文采用PMC指數模型測算政策力度,表征旅游援疆政策的作用強度。考慮到旅游援疆政策的滯后效應,故以6月30日為界,在該日期前計為當年實施;否則視為次年實施,根據時效期限更新政策樣本。政策樣本源于中國政府網、國家文旅部官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網、新疆文旅廳官網、19個援疆省市與新疆14個地州市政府官網和文旅廳官網,以“旅游+援疆or援助or支援”為關鍵詞,通過八爪魚軟件搜集2231條旅游援疆政策樣本,刪除總結、宣傳、新聞等無效文本,最終獲得2004—2021年65條有效政策文本。考慮到2010年以前僅有1份旅游援疆政策文本,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旅游業沖擊較大,確定實證研究期限為2010—2019年。
被解釋變量:將旅游投入(Tourism input,TI)和旅游產出(Tourism output,TO)作為評價旅游援疆政策有效性的被解釋變量,旅游投入和旅游產出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19],通過熵權法測算其綜合值。數據源于2011—2020年《新疆統計年鑒》及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旅游投入指標體系包含A級景區數量、旅行社數量、星級飯店數量、博物館數量及公共圖書館數量,旅游產出指標體系包括國內與入境旅游收入、國內與入境旅游人次。

表1 影響因素指標體系構建Table 1 Construc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 index system
控制變量:為增加模型的解釋力度,清晰反映旅游援疆政策組合對旅游投入和產出的影響效應,根據前 期 研 究 成 果[20,21],選 擇 交 通 保 障 因 子(Traffic management support,TS)、轉型升級因子(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TU)、經濟支撐因子(Economic support,ECS)、環境可持續因子(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ENS)、對外開放因子(Opening up,OU)作為控制變量,控制變量數據來自2011—2020年《新疆統計年鑒》。
1.2 研究方法與模型構建
PMC指數模型及量化步驟:依據PMC指數模型的建模原則,結合政策實際特征與文本挖掘結果,設定指標參數為一級變量(5個)、二級變量(10個)和三級變量(40個),建立旅游援疆政策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表2)。對三級變量賦值,根據賦值原則各變量地位一致,通過標準為1,未通過則為0(其中,X3-1因為各指標互斥,根據前人研究賦權)。通過二進制法構建多投入產出表,量化政策文本。計算公式為:

表2 旅游援疆政策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 m of TPDAX


式中:t為二級變量;j為三級變量。
將旅游援疆政策PMC指數代入政策力度評估模型,計算旅游援疆政策力度值,政策效力時長由其有效期限決定并動態更新。計算公式為:

式中:TAPi為第i年旅游援疆政策力度累積值。
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利用VAR模型分析無約束條件下聯合內生變量間的動態關系,解釋隨機擾動對被解釋變量的沖擊,探索政策變動與旅游投入和產出間互相傳導的動態路徑。
QCA組態分析:結合集合思想、布爾運算和隸屬類別,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精確計算并區分處理統計分析中的各子集間關系[29],將變量轉化為[0,1]連續數值,運用fsQCA軟件確定旅游投入和產出的充分或必要條件。考慮案例類別和程度差異,設置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非隸屬的關鍵閾值,將各變量的校準點分別設定為樣本描述的上下四分位數值和均值,確定變量錨點,其中1為完全隸屬,0為完全非隸屬。
2 結果及分析
2.1 旅游援疆政策文本分析
政策文本包含政策主體、結構、類型、數量等內容[30],是量化評價的數據基礎。整體來看,政策主體分為國家、援助方和受援方,三方互動解決旅游援疆的核心問題和主要障礙,以國家牽頭、多層級多部門協同發展的形式推進旅游援疆政策落地落實;政策結構包括目標政策、戰略政策和具體政策,以把新疆旅游業建成國民經濟重要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和改善民生的富民產業為目標,實施“引流入疆、人才援疆、規劃援疆、游客送疆”等戰略措施,著力增強新疆旅游業自身“造血”能力;政策類型分為公告、計劃、意見和方案等,國家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旅游援疆工作的指導意見》《關于赴援疆省市開展旅游援疆工作的方案》為相關省市和旅游部門開展后續援疆工作指明方向。
DSR(Driving Force-State-Response)模型涵蓋驅動力、狀態和響應3個子系統,是評價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模型[31]。基于DSR模型,借助NVivo軟件進行詞頻分析,抓取TOP100高頻關鍵詞,利用反向查詢功能查看高頻詞所在政策原文,解讀政策內涵并解構內部聯系,結合政策現狀及未來趨勢構建旅游援疆政策的作用機理(圖1)。

圖1 旅游援疆政策的作用機理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TPDAX
驅動力是旅游援疆的行動指南,包含影響政策制定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等因素,具體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科技創新引領支撐、旅游興疆發展趨勢、旅游生態環境脆弱、區域經濟發展滯后、消費市場多元化需求和經貿交流合作。驅動力是新疆旅游業跨越式發展的決策依據,是援助省市和受援地州市的行動指南,為新疆旅游品牌建設開辟新領域。狀態是旅游援疆的關鍵著力點,指政策措施在驅動力背景下演化發展、自我調節達到的基本狀態。社會層面包含政府調控市場引導、深化改革加強管理、因地制宜統籌兼顧;環境層面要維護旅游業發展和生態環境改善相統一;經濟層面通過財政補貼和設施建設、旅游業轉型升級和加強對外開放拓寬旅游發展渠道。援助方和受援方通過制定行動原則,深入貫徹保護和發展理念,完善旅游公共服務體系,準確把握旅游援疆的階段特征,提高政策有效性和可靠性。響應是旅游援疆的時代答卷,指政策持續發展重點及其產生效應,包括旅游投入保障效應、引導效應、外部效應和旅游產出集成效應、源泉效應、轉移效應,通過多元路徑組合推進新疆旅游發展速度、規模、質量相統一,探索具有新疆特色、時代特點的旅游援疆新模式。
綜上所述,驅動力系統通過外部環境推動旅游援疆政策動態調整,促使社會、環境和經濟效益的均衡統一,同時激發政策做出積極響應,通過多元路徑為旅游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狀態系統通過自我調節逐漸適應外部環境,打破旅游援疆固有模式,實現響應路徑的完善革新,助推新疆旅游業螺旋式上升發展;響應系統既直接作用于政策階段狀態,積極探索合作模式,又通過新疆旅游業發展間接推進政策實施,實現驅動力的加強與優化,刺激狀態的調整與響應。系統間通過相互關聯和內在邏輯形成有機循環反饋模型,持續加大旅游援疆的政策力度,為政策實施提供持續引擎動力,構建優化和創新并存的發展格局。
2.2 驅動因素及力度分析
選取高頻詞解讀旅游援疆政策的驅動因素,詞頻越高則說明占據地位越重要。①社會驅動力。社會資本參與旅游資源開發和產業發展,對新疆旅游高質量發展有著更高要求。民生(149)保障(327)、科技(156)創新(296)、技術(238)改革(418)、扶持(243)和振興(104)等高頻詞說明社會發展進步是旅游援疆主要目標,需要結合新疆實際,推進重點文旅功能區建設,鞏固新疆旅游業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地位作用。②環境驅動力。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消耗資源,政策制定過程中需對旅游環境由被動維護變為主動保護。改善生態(423)環境(432)是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路徑,通過加快清潔能源(102)產業鏈建設,找準環境與旅游連接點,處理好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③經濟驅動力。作為政策制定主要因素,高效發展新疆整體經濟成為主要目標。由于區域(417)經濟(503)發展的外在推動、消費(183)市場(355)的內在需求及對外開放(109)的整體要求,需著力解決基礎(798)設施(609)不健全、景區(486)配套(121)服務(1157)不完善等關鍵問題,不斷提高目的地的吸引力。隨著旅游援疆政策持續實施,驅動力不斷適應狀態的調整變化,持續優化旅游援疆的新路徑。
通過PMC指數測算歷年旅游援疆政策力度值TAP,探究驅動力作用下的政策演進水平和階段特征,將其劃分為萌芽成長期、蓄力發展期和穩中有進期(圖2)。整體來看,旅游援疆政策力度呈上升趨勢,但仍存在部分短板,尚需修訂和完善。政策方式力度明顯低于其他維度,說明旅游援疆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缺乏多重激勵保障措施,忽視資金項目和人才支持的有機結合,單一措施不利于保持政策完整性,指向性不夠明確。①萌芽成長期(2010—2014年)。2010年起中央及各省市實施新一輪援疆工作,作為關聯作用強勁的綜合性產業,旅游業充分發揮富民興疆的帶動作用,十二五時期是建設旅游強國的關鍵時期,旅游援疆逐漸受到重視。②蓄力發展期(2015—2017年)。2015年原國家旅游局首次針對旅游援疆提出專項政策《關于進一步推進旅游援疆工作的指導意見》,對工作內容提出具體要求,推動援疆省市資金、人才、信息與新疆優質旅游資源相結合,打造新疆旅游形象品牌,促進區域旅游聯動發展。十三五時期奠定全國文旅行業提質增效的總基調,旅游援疆政策數量大幅增加。③穩中有進期(2018—2021年)。2018年中央出臺《關于赴援疆省市開展旅游援疆工作的方案》,搭建平臺、創新形式,不斷提高旅游援疆的綜合效益,推動具體舉措落地實施。2018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全域旅游發展的指導意見》,促進區域旅游協調發展。2021年國家文旅部發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國家旅游援疆力度突飛猛進,開啟了旅游援疆的新格局。

圖2 旅游援疆政策力度及階段劃分Figure 2 The strength and phases of TPDAX
2.3 動態效應分析
為厘清驅動力推動下的旅游援疆政策的狀態調節與作用效果,基于2010—2019年時間序列數據,采用VAR模型驗證旅游援疆政策與旅游投入(產出)間的動態均衡和沖擊程度。
為消除異方差影響,對旅游投入、產出和旅游援疆政策力度均取自然對數處理。為避免“偽回歸”,運用Eviews11軟件進行單位根檢驗(表3)。從表3可見,ln TI、lnTO和lnTAP至少在5%水平通過檢驗,說明變量數據平穩。分別建立ln TI與ln TAP、lnTO與lnTAP的VAR模型,采用LR、FPE、AIC、SC與HQ的統計量檢驗模型最優滯后期,選擇最優滯后階數為2。運用Eviews11軟件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各變量因果關系的作用方向,結果在5%水平顯著:TI和TAP為單向因果關系,即政策力度加大可以顯著促進旅游投入增加;TO和TAP為雙向因果關系,旅游援疆政策實施會提高旅游產出水平,同時旅游產出提質增效則會加大政策力度。通過AR特征根檢驗,確定構建的兩個VAR模型均穩定,探究政策力度沖擊對被解釋變量造成的影響軌跡及響應程度(圖3),反映TAP和TI、TO的交互關系,其中橫軸表示沖擊后的滯后期數,縱軸表示變量對自身和對方沖擊的方向和大小。

圖3 脈沖響應函數結果Figure 3 The results of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

表3 ADF單位根平穩性檢驗Table 3 ADF unit root stationarity test
旅游投入(TI)發揮了旅游援疆的新優勢,響應程度具有“擴散→收斂”趨勢。TI對來自TAP沖擊首期未立即做出響應,隨后迅速上升并在第二期達到峰值后下降,最后逐漸平緩,表明從短期看政策力度對旅游投入起到顯著促進作用,從長期看雖始終正向影響但效果逐漸減弱。旅游援疆政策出臺初期,各援助省市迅速反應,全面推進旅游投入,宏觀政策指導作用較強,伴隨發展入軌并呈現全局演變態勢,旅游投入呈現穩步提升、長期向好的新趨勢;而TI對自身沖擊迅速正向反應,但隨之陡然下降,從第四期開始響應效果始終為負,表明旅游投入從短期看對自身會產生積極影響,從長期看則不利于自身健康發展。旅游投入過多更會造成“投入冗余”,打破投入產出平衡,影響旅游投入質量和旅游效率的動態均衡。
TO瞄準旅游援疆的新布局,沖擊波動呈現“劇烈→平緩”趨勢。TO首期未對TAP的沖擊做出響應,且短暫出現負向效應,之后波動回調,于末期趨于收斂狀態,表明政策力度加大對旅游產出整體收益增長起到強化支撐作用,波動趨勢逐漸較小。從旅游援疆政策實施到旅游產出效果凸顯的過程中存在滯后效應,政策扶持推動新疆旅游業轉型升級,促進“資源優勢→經濟優勢→品牌優勢”的有效轉化,實現旅游產出效益穩步向好;而TO對自身正向沖擊,并在第4期達到最大,隨后出現下降趨勢,表明新疆旅游產出對自身沖擊較為顯著,隨時間推移有所減弱。旅游產出增加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唱響“新疆是個好地方”文旅品牌,以求實務實、提質增效之勢創造旅游興疆戰略實施的新成果。
TI和TO發展變化的方差分解結果如圖4所示。從TI方差分解可知,旅游援疆政策力度對旅游投入的解釋力在第一到第二期內迅速上漲,增長率達47%,之后持續增長趨于平緩,解釋率于末期達到66%,而旅游投入對自身解釋率則由首期的100%逐漸減緩至34%,從第三期后政策力度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成為主要考量因素;從TO方差分解可知,政策力度在短期內對旅游產出的解釋力度有所提高,第四期峰值達到13%,最終保持10%左右,表明政策力度并非旅游產出效益提升的主要原因。旅游產出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和前期建設,發展周期長、市場韌性強,旅游援疆政策實施往往受到一系列風險因素的不確定性影響導致其政策效應不明顯,需在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中開啟旅游援疆的新征程。

圖4 方差分解結果Figure 4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2.4 多元路徑分析
運用fsQCA3.0軟件構建旅游投入和產出的組合構型,探究自變量與結果變量間的必要關系。結果顯示,自變量TAP、TU、ECS一致性均大于0.9,而其他變量均不構成必要性條件,旅游援疆政策明確要求加大旅游投入,轉型升級和經濟活力在發展過程中通過多種途徑影響旅游投入的增加;自變量TU、ECS一致性水平大于0.9,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和國民經濟向好,新疆旅游業發展優勢逐漸凸顯,旅游產出效益實現新突破。分析各因素差異組合對旅游投入和產出的響應路徑并優化路徑,產生“殊途同歸不同效”的效應差異。
使用fsQCA3.0軟件識別不同前因條件組合(表4),設定案例一致性閾值為0.8,PRI一致性閾值為0.75[32]。旅游投入(產出)路徑組合整體一致性為0.9872(0.9847),均達到0.75閾值要求,各組態具有充分的解釋能力。根據Lepp?nen等的做法[33],將一致性閾值水平由0.8調至0.85,兩類構型組態數量、結構、一致性和唯一覆蓋度參數均未改變,驗證結果穩健可靠。總體來看,TU和ECS在TI(TO)構型中均為核心條件存在,說明高品質建設和經濟增長對旅游投入(產出)均產生良性互動,如烏魯木齊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旅游集散中心”,整體呈現繁榮向好的穩健發展步伐。而TAP是TI的核心條件和TO的邊緣條件,政策實施初期支持政府牽頭整合旅游產品,充分發揮旅游景區的主體作用,最大程度獲得旅游動力、釋放旅游活力、挖掘旅游潛力,通過政策傾斜推進旅游興疆戰略實施,培育多元特色旅游景區,如南疆建設“絲綢之路文化和民俗風情旅游目的地”。

表4 前因條件組合Table 4 Antecedent condition combination
組態A1和B1為環境依托型旅游路徑,旅游投入產出釋放活力,實現了新疆旅游效益均衡發展。A1和B1一致性和唯一覆蓋度分別為0.9932、1和0.6328、0.5876。兩種構型均以TU和ECS為基點,雖然對外開放程度較低,但其環境優勢可有效彌補缺陷,驅使旅游業依托良好生態基底與和諧社會環境加大投入。借助環境優勢,為旅游業可持續發展注入活力,切實發揮旅游投入保障效應,如天山世界自然遺產帶、阿爾泰山千里畫廊等。通過環境治理約束旅游非期望產出,同時貫徹新理念、采用新技術,將發展與保護納入統一框架,實現集約化發展,如賽里木湖景區建設3A級旅游廁所污染物集中處理項目,實現污染物達標排放。
組態A2和B2為雙驅動型旅游路徑,聚焦旅游市場,構建多元投入產出體系。A2和B2一致性和唯一覆蓋度分別為0.9927、1和0.5896、0.5478。兩種構型包含條件個數最多,無核心和邊緣條件缺失。在TAP、TU和ECS存在基礎上,TS和ENS為TI和TO發揮輔助作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旅游業發展密不可分,借助蘭新高鐵、城際列車和普速鐵路互聯組網優勢,構建“交通+旅游”協調聯動新格局,實現新疆“快旅慢游”新舉措;環境規制倒逼旅游業建立智能化與綠色化的管理鏈條,實現新疆旅游可持續發展。交通設施提升旅游資源的利用率,引導旅游投入增加,通過源泉效應不斷提升旅游產出的效益與效率。
組態A3和B3為開放加持型旅游路徑,發揮特色優勢,提升良性投入產出效益水平。A3和B3一致性和唯一覆蓋度分別為0.9688、0.9625和0.3348、0.3068,均為組態最低值。相較于東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存在投入產出效益較低、對外開放滯后等問題,需要貫徹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建立和完善對外開放體系,加快推進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和統一大市場的新發展格局,如簽署“中俄哈蒙”旅游合作協議,推動邊境購物旅游、養生醫療旅游的合作發展。通過對外開放調節旅游產業的內部關聯和外部效應,助力旅游投入滿足市場需求。通過對外開放把握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求,引入和吸收旅游前沿理論與先進技術。
為辨析不同情境中路徑組合方式的結果差異,根據均衡理論對旅游投入和產出分別設置減少和增加5%、10%和50%情境模擬,旅游投入構型均為TAP×~TS×~TU×~ECS×~ENS和TAP×~TU×~ECS×~ENS×OU,旅游產出構型均為TAP×~TS×~TU×~ECS×~OU和TAP×TS×~TU×~ECS×~ENS×OU,且TAP均為核心條件存在。對比表4分析可見,當其余條件缺失狀態下,TAP對TI和TO顯著正向影響,說明旅游援疆政策對旅游投入產出的比例結構更合理、區域發展更平衡的作用愈發重要。需要加大政策力度,搭建平臺、創新形式,堅持突出重點精準發力,不斷提高旅游援疆的綜合效益,如浙江省幫扶建設托木爾峰自然保護區到G3012連接線,打通旅游交通微循環。援助方和受援方協同合作,以新疆旅游跨越式發展為戰略目標,啟動實施疆內外旅游企業“雙百結對”提升行動計劃,借助內地旅游企業的融資、管理、人才等優勢,扶持建立新疆骨干旅游企業。優化旅游投入要素結構,避免“木桶效應”造成資源浪費和路徑依賴,實現以更少投入獲得更多產出,如加大高速公路沿線旅游廁所、標識標牌、信號基站建設力度,縮短旅途時間,提高服務質量。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根據DSR模型歸納旅游援疆政策的作用機理,梳理旅游援疆政策文本,運用PMC指數模型、VAR模型、fsQCA軟件分析旅游援疆政策的驅動力、狀態和響應。主要結論如下:①驅動力、狀態和響應形成協調聯動的復雜系統,共同構建旅游援疆政策的作用機理。驅動力是旅游援疆的行動指南,通過外部環境推動政策動態調整,同時激發政策做出積極響應;狀態是關鍵著力點,通過自我調節逐漸適應外部環境,進一步實現響應路徑的完善革新;響應是時代答卷,直接作用于政策發展狀態,實現驅動力的強化與優化。②社會、經濟和環境驅動力互動作用形成有機循環系統,為政策實施提供持續的引擎動力。在驅動力作用下,旅游援疆政策呈現階段特征:萌芽成長期(2010—2014年)旅游援疆逐漸受到重視;蓄力發展期(2015—2017年)旅游援疆政策出臺數量大幅增加;穩中有進期(2018—2021年)旅游援疆關注度突飛猛進,開啟旅游援疆的新格局。③旅游援疆政策狀態有效性有利于推動新疆旅游業整體發展進程。旅游援疆政策力度與旅游投入(產出)為單向(雙向)因果關系,旅游投入(產出)對政策力度的沖擊響應分別具有“擴散→收斂”和“劇烈→平緩”的變化趨勢。政策力度在旅游投入中占據主導地位,成為主要考量因素,而非旅游產出效益提升的主要原因。④殊途同歸不同效,政策響應存在環境依托型、交通環境雙驅動型和開放加持型的多元組合路徑。轉型升級和經濟支撐均為旅游投入和產出的必要條件,旅游援疆政策是旅游投入的必要條件。根據均衡理論進行多種情景模擬,旅游援疆政策均為核心條件存在并優化路徑。
3.2 建議
旅游援疆是新時代新疆旅游業發展的強勁動力,政府推動成為引導市場驅動行為的有效依據。基于政策實施效果與新疆旅游實際,提出“援疆+旅游”的發展建議:①針對驅動力,推進激勵體系建設,維護援助雙方主體利益。相較于其他維度演變趨勢,政策方式力度始終處于低水平狀態,需要完善旅游援疆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多重激勵保障措施,為新疆旅游發展提供積極的外部環境,有機結合資金項目和人才支持,引導旅游企業提供有效供給支撐。通過實施人才支持工作者專項計劃、鄉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項目和“訂單式”人才援助項目等,重點支持旅游公共服務保障設施建設,夯實旅游業發展基礎。②針對互動狀態,旅游援疆政策持續發力,助力旅游產出落地見效。旅游援疆政策對初期旅游投入影響較大,導致政策力度并非旅游產出效益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要求政策直接作用于旅游產出,通過引客入疆等途徑豐富旅游創收形式,引導行業協會、中介組織、社會單位發揮自身優勢共同參與旅游援疆工作;另一方面通過間接渠道促進旅游產出增長,支持政府開拓多元化融資渠道,為新疆旅游業發展提供具體化、科學化的政策扶持。③針對響應路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進新疆旅游業整體有序協調發展。根據情境模擬結果,政策力度有效促進新疆旅游業提質增效,要從援疆戰略的高度出發,考慮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逐漸適應“輸血→造血→活血”的漸進變化。強化受援地州市與援疆省市的交流交往交融,加強旅游宣傳促銷工作,制定切實可行方案,及時出臺優惠政策,鼓勵文旅企業涵蓋兩地經營、連鎖經營和品牌輸出,不斷豐富旅游援疆的新業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