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上學”的孩子走進心理科診室
李文

“18歲以下的抑郁癥患者占總人數的30%,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已達15%至20%”,前不久新發布的《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公布了上述數據。
抑郁的孩子為什么會有這么多?走進心理科診室求助的孩子是什么狀態?珠江醫院心理科“青少年情緒障礙門診”負責人趙久波教授向南都記者介紹,青少年的抑郁、雙相障礙、焦慮等情緒問題,的確已不是個別現象,這些孩子的情緒問題,也并不是“不開心”“不想上學”這么簡單。
不想上學的孩子
來看心理科的孩子有多少?趙久波算了算,自己最近的一個半天門診接診了20多個病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如果加上另外幾個20出頭的大學生,可以說,年輕人占了門診病人的一半”,這個情況,也基本是平日里的平均狀態。
15歲女孩小余(化名)2022年9月剛升上高一,但沒讀幾天就要求回家,之后就不愿再去學校。小余爸爸為此帶她來看心理門診。
趙久波記得,這個女孩文靜、沉默,醫生的提問大部分由父親代答,但也看得出,孩子的精神狀況并沒有達到抑郁癥的診斷標準,更有可能是新學校、新環境帶來的適應問題。
和小余爸爸一樣,孩子的情緒問題影響到上學,這是大部分家長帶孩子來看心理科的最初動因,“抑郁、雙相(雙相情感障礙,抑郁與躁狂交替出現)、焦慮是青少年中比較多見的情緒障礙,出現這些問題時,孩子不光是心情不好,還會變得思維遲鈍,注意力、記憶力下降,睡眠不好,體力、精力也不好,影響到學習生活,有的干脆不去學校了,這種情況在門診里是比較常見的”。
在趙久波看來,小余的問題還不算嚴重,其實,大部分來到心理科的孩子比她要嚴重,“我們普通公眾的觀念還沒有達到‘發現輕微的情緒問題就意識到來醫院看病的程度,很多掛號來看門診的都是比較嚴重的”。
“不想上學”的背后,這些孩子遭受了多重困境:有孩子感覺抑郁到“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感覺自己“與地球脫節”;睡眠出現問題,早上很早醒、容易被驚醒、睡眠淺,或者躺下睡不著;注意力、記憶力下降,對什么都不感興趣,覺得自己很沒用;精力不足,不想出門,不想見人,什么都不想干;吃東西沒有胃口;嚴重的,會出現頭疼、頭暈、胸悶、心慌、出汗、發抖等軀體癥狀……
孩子因“不想上學”被家長發現問題、帶來看心理科,但家長們更傾向于把這些問題歸結于適應問題或學習、人際關系等外界壓力導致,但卻不知道或不愿承認,自己有可能就是孩子的壓力來源。
是父母的錯嗎?
對于青少年來說,情緒問題的產生與家庭環境、親子關系的關聯度更高,“一個問題孩子的背后,常常存在一個有問題的家長,或者有問題的家庭環境。”趙久波說,親子關系問題導致的孩子情緒問題,占青少年情緒心理問題的一多半。
小林(化名)的情況讓趙久波印象深刻。小林20歲左右,已出現抑郁狀態,還伴有幻聽、手抖等軀體癥狀,她的情緒問題從初中即出現,她能清楚表述,自己的問題源自幼時父親的打罵。
趙久波向陪診的小林媽媽求證,但小林媽媽一開口就講自己的苦衷,說小林總是說謊,才引得父母不滿意,母女倆差點在診室爭執起來。
這種情況,除了下醫囑,趙久波盡力勸解大人和孩子一起調整,他特別希望孩子家長能理解“孩子現在的狀態,不是她不努力不上進,而是她生病了,人抑郁了以后就對什么都不感興趣”。
類似的情況,趙久波遇到過很多,“親子關系的問題關鍵是,雙方都只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到了青春期,孩子過度夸大了自己作為成人的一面,父母夸大了孩子作為孩子的一面,實際上,家長要尊重孩子作為獨立個體的情感需要、心理需要,孩子也都希望爸爸媽媽理解自己,正視不同時代的人思想觀念的巨大差別”。
多年經驗,讓趙久波對孩子們的“槽點”了如指掌:孩子最討厭父母拿自己小時候的經歷跟孩子現在類比,討厭父母太嘮叨;孩子很在意生活中的細節,比如玩手機的時間是一小時還是兩小時,比如答應的事為什么不算數,比如為什么你看手機可以、我看手機就不行;父母給孩子報的興趣班是父母感興趣的,孩子小時候沒能力反抗,上了中學就會用各種辦法逃避……
家庭環境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還有一部分孩子,親子關系不差,外部環境問題不大,但也發生抑郁問題,已有研究發現與遺傳因素有關。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不論是家庭因素還是遺傳因素,還是外部環境壓力,情緒問題的產生通常都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趙久波強調,切忌把原因單一化、簡單化,有時候,是此前積累了太多不利因素,而某個誘因的產生導致孩子“最后一根弦”崩掉了。
“18歲以下的抑郁癥患者占總人數的30%,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已達15% 至20%”,前不久新發布的《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公布了上述數據。
內心困境并非不可逾越
崩掉的弦其實可以慢慢修好。
趙久波有個“老病號”,是個初中男孩,在激動時難以控制情緒,此前有把別人一拳打倒在地的經歷,但通過系統的藥物、心理治療及規律復診,孩子已經能夠做到在感覺情緒要失控時,先控制住自己的行為,之后再發泄情緒。
這個孩子在診室的表現非常懂事,和媽媽的溝通也順暢,孩子媽媽對治療也非常配合,孩子的好轉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目前他事后發泄情緒的辦法仍有點危險,就是拿拳砸墻,之后會指導他慢慢尋找一些不會傷害自己的疏解情緒的辦法”。
“到了初高中階段,青少年的獨立意識是很強的,我們要做的是鼓勵他們,讓他們有信心去面對內心困境和現實中的困難,這是很核心的一點。”趙久波說,同時,家長也需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孩子的學業、未來都是需要自己承擔的,家長最核心的幫助是讓孩子感覺有陪伴、有理解、有支持,內心有力量,是孩子有困難時的“兜底”力量。
趙久波曾遇到一名中學生,是成績特別好的名校尖子生,但特別追求完美,給自己很大壓力,出現了情緒問題,他的老師發現了端倪,提醒他來看心理門診。
經過治療調整后,孩子的情緒穩定了,狀態好轉了,但一直不愿回到學校繼續學業,“他的想法比較極端,因為休學一段時間,他可能無法一下子在學業上重回巔峰,達不到完美狀態,他就干脆逃避,不回去”。
這種情況,其實是沒有接納現實,無法清晰評估自身的身心狀態,也就談不上之后的康復和回歸。實際上,在心境障礙問題解決之后,孩子能否順利回歸生活正軌,還需要在價值觀、適應能力、性格、思維方式等方面進行疏導和重塑。
有的時候,無法接受現實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長。趙久波遇到過一個讀初中的男孩,為治療雙相障礙已經休學很久,但此前治療不規范、不系統。不過,家長關心的不是怎樣改進治療,而是他什么時候能夠回到學校上學,一味地希望他積極適應學校,還要給他輔導功課。
實際上,對于這個雙相障礙患者來說,待在課堂上是一種煎熬,長久的情緒問題消磨了他的思維能力、體力、精力,讓他不再具備課堂學習的能力,“其實,家長心里不愿意接受他的孩子已經抑郁了、雙相了,而寧可相信是孩子上學不夠努力,在學校不適應,或者學習壓力太大”。
不接受、不直面問題的后果,有時候是嚴重的,孩子會以自傷、自殘的形式發泄情緒和壓力,用肉體的痛苦來緩解內心的痛苦,甚至有更嚴重的想法和行為。在心理科診室,胳膊、腿上布滿劃痕的病人并不少見。

醫生眼中的孩子:可愛又無助
有情緒問題的孩子,表面不一定有明顯的異常。有的孩子狀態低迷、不愿說話,也有的孩子坐姿松弛,有問必答,表達清晰,講話時會習慣性地笑。
在趙久波的眼里,這些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有孩子氣的單純、可愛,同時,有了情緒問題之后,他們也是非常無助的,“情緒問題嚴重到一定程度時,單靠跑步、打球、聽音樂這些辦法來自我調節,是搞不定的,而孩子的社會關系簡單,生活中一般只有父母、老師、同學,如果在父母那里得不到支持,同學、老師關系不好,那就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了,非常無助”。
有些孩子的處境,讓趙久波覺得,如果換作自己,也會非常難:父母分開,或者父母不在身邊、不怎么管他,帶他的老人只有精力管個溫飽,孩子身邊沒有特別親近的人可以依靠,“他的世界是非常孤單的,如果生活中還有人欺負他,有人瞧不上他,他自己性格也比較內斂、沒什么朋友,情緒問題又導致他精力體力差、腦子不好使,這種情況換作是我,我也會覺得特別痛苦、無助”,而這種處境的孩子,即使醫生、老師調動起社會資源來幫助他,往往也難以擺脫這種無力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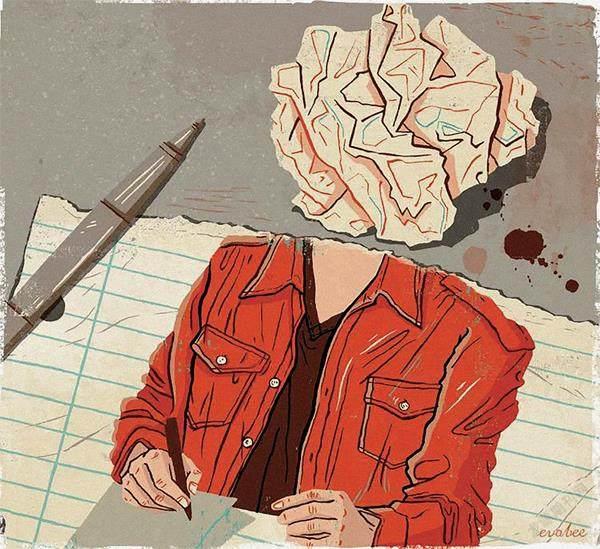
不過,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現在的孩子也越來越有辦法,能夠來到醫院心理科求助,就是他們找到的自救辦法。
未成年人看診一般都會有家長陪著,趙久波也遇到過一個人來看診的初中生,他趁孩子做心理量表的時候聯系了孩子媽媽過來,發現,孩子和父母關系不好,父母覺得孩子還很正常,只是不夠堅強和努力,但孩子覺得自己狀況很不好了,就自己來看醫生,之后的診斷發現,孩子的確已經是抑郁狀態,開始了系統的治療。
有數據顯示,抑郁癥患者中,得到規范治療的只占總人數的10%左右,而治療的第一步是對情緒問題的正視和接受,趙久波發現,在這方面,很多孩子的觀念比父母更開放、更科學,但這不代表后續的治療是容易的。
社會對心理疾病患者的“標簽化”歧視、國人對長期藥物治療的心理抵觸,甚至總是要靠“搶”的心理科號源、有限的看診時間,都是后續治療的阻力,“即使通過藥物、心理治療解決了醫學可以解決的那一部分,青少年健康成長所必需的家庭、社會支持體系,并不是醫生能夠提供的”。
政策已經在行動。2021年10月,教育部在對《關于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郁癥防治措施的提案》的答復中明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心理健康服務相關的文件也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給予了高度關注。這些“不開心”“不想上學”的孩子,有望更早地被發現、被幫助。
◎ 來源|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