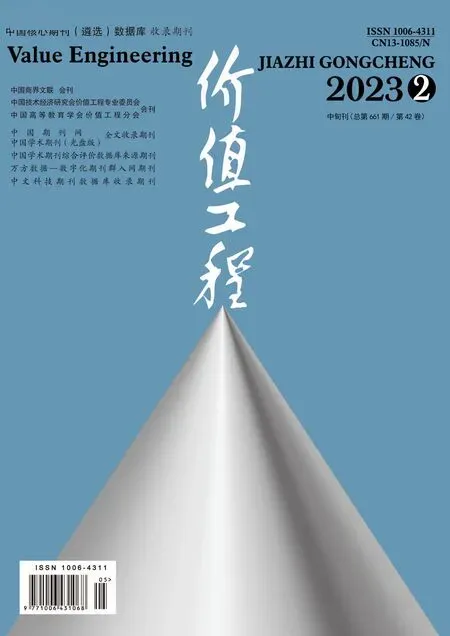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與企業創新質量
——基于高耗能行業數據分析
冷湘韻 LENG Xiang-yun
(鄭州大學,鄭州 450001)
0 引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粗放式經濟增長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其也導致了不可忽視的環境問題。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污染防治是政府工作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我國更是提出了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雙碳”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近年來政府出臺了各種環境規制政策,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促進企業創新,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雙目標。根據趙玉民等(2009)的分類,環境規制可分為顯性環境規制和隱性環境規制,其中,顯性環境規制又分為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以市場為基礎的激勵性環境規制和自愿性環境規制。由于隱性環境規制的度量方式及數據難以獲得,現有研究較多從顯性環境規制出發研究其經濟后果。不同的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具有不同的影響路徑。
本文以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實施這一事實構造準自然實驗,利用該試點作為識別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資源消耗型企業創新質量影響的外生沖擊,構造雙重差分法來驗證碳排放權交易機制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因果推斷。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本文從微觀企業視角提供了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微觀企業影響的增量文獻。現有文獻大多從省份層面分析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的宏觀影響,而忽略了其對微觀個體的經濟后果;第二,本文從企業創新質量的角度,分析了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實質性創新的影響,對波特假說進行了再驗證;第三,選取高耗能行業這一資源消耗型子樣本進行研究,為政府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政策實施提供微觀實證參考。
1 文獻綜述
政府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的實施會對企業生產運營決策產生影響。企業會通過降低產量減少排污量、直接購買更新綠色工藝設備減少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排放或自主研發創新等活動來應對環境污染問題、響應政府號召。有學者認為,一方面由于企業研發過程通常具有高風險、高投入、耗時長等特點,無論是降低產量、購買設備還是自主研發,都會占據企業正常生產運營資金,影響企業現金流,降低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企業創新行為的目的不僅包括推動技術進步、保持競爭優勢還有一種是策略行為。企業會通過增加創新申請數量來向社會展示經營良好、環保負責的企業形象,而且由于信息不對稱性,政府難以辨別企業申請專利的質量,只能通過企業創新專利申請來給予企業創新補助、稅收優惠等政策,這也為企業的投機活動提供了可能。
以波特為代表的學者對此提出了相反觀點,根據波特假說,嚴格且適宜的環境管制能夠激勵企業發展新的技術和組織方式,這反而可能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和市場競爭力。從企業內部來看,雖然企業研發創新短期內會占用企業生產資源,但是從長期來看,企業創新專利帶來的經濟利益流入會抵消研發支出,并形成企業的無形資產,通過技術領先戰略提高企業競爭力。從外部環境來看,隨著2014年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實施,到2018年排污費改稅,再到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雙碳目標”。我國環境規制強度不斷增強、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不斷完善。根據企業競爭力理論,企業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可能克服企業惰性,促進企業做出改變、積極開展綠色技術創新。
為探究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是否能促進企業實質性創新,提高企業創新質量,本文提出如下競爭性假設:
H1a: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能提高企業創新質量;
H1b: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不能提高企業創新質量。
2 研究設計
為了獲取可信的因果推斷,本文以2014年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實施為準自然實驗,以此來分析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是否能提高企業創新質量。因此,本文將雙重差分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Apply是指企業創新質量,本文使用企業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并參考張杰等(2018)的做法,以實用新型專利的IPC分類號為基礎,根據赫芬達爾指數計算方法統計出每一個實用新型專利的質量,然后用平均數的方法加總到每一個企業。Time表示時間,2014年及以后取值為1,2014年以前取值為0;Treat表示是否為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重點排放企業,是則取值為1,反之為0;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δ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γi,t表示省份虛擬變量,ρi,t表示行業虛擬變量,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Xi,t為控制變量。參考胡珺等(2020),本文分別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資產凈利潤率(Roa)、產權性質(Soe)、成長能力(Grow)、經營凈現金流(Ocf)等變量。
為獲得一個相對平衡的面板數據,本文選擇2009-2020年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六大高能耗行業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并對樣本進行了如下處理:①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這些公司的財務數據結構和監管制度與其他行業存在很大差異;②剔除當年被ST的樣本,此類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都經過了一定處理;③剔除財務數據存在缺失的公司年度樣本。經過上述處理后,共得到1791個樣本。本文公司層面的財務數據和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重點排放企業信息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實用新型專利IPC分類號數據來源于CNRDS數據庫。為避免數據極端值對研究結論產生干擾,本文對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處分別做了縮尾處理。
表1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創新質量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8148,表明高耗能企業間創新質量水平差距較大;Treat均值為0.1167,表明樣本企業中有210個企業為對照組,1580個企業為實驗組;Soe均值為0.5366,表明樣本中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分部較均勻。其余控制變量與現有文獻基本一致。

表1 描述性統計
3 實證結果與安慰劑檢驗
圖1表示動態效應檢驗結果,平行趨勢假定是實證論文中使用DID的前提,即在沒有政策干預的情況下,結果變量在處理組和對照組的發展趨勢一致才能使用DID。本文發現在2009-2014年間β均不顯著,說明處理組和對照組在試點政策實施前不存在明顯的差異,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此外,試點后估計系數β從第四年(2018年)開始顯著,說明2014年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對創新質量的影響滯后四到五年。

圖1 平行趨勢檢驗
根據前文設計的待檢驗模型1,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創新質量影響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括號內為P值)。其中第(1)列,本文僅加入了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并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這一列中Time×Treat的估計系數為0.0552,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在第(2)列中,本文加入了控制變量,Time×Treat的估計系數為0.0502,在10%水平上顯著;在第(3)列中,進一步控制了省份和行業的固定效應影響,發現Time×Treat的估計系數仍然為正,并且在10%水平上顯著。表2的回歸結果說明,碳排放權交易機制能夠顯著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質量,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H1a。

表2 基準回歸及安慰劑檢驗
本文進一步采用安慰劑檢驗來檢驗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根據安慰劑檢驗,政府2014年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的實施能促進企業創新行為,提高企業創新質量,而在2014年之前并沒有實施該交易試點政策,所以在2014年之前碳排放權交易政策試點的實施與企業創新質量的回歸結果應該不顯著。根據這個思路,本文重新定義了Treat變量,假設2012年為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年份,2012年及以后期間Treat變量取值為1,2012年以前Treat變量取值為0,然后將重新定義的Treat變量放入模型1中重新回歸,結果如列(4)所示。Time×Treat的估計系數為0.0592,但并不顯著,通過了安慰劑檢驗,本文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在梳理現有文獻、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以2014年碳排放權交易試點這一外部政策沖擊,使用微觀企業層面數據,構造雙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高耗能行業企業創新質量的影響。根據本文的研究成果,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創新質量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通過碳排放權交易政策,低污染排放企業有排放配額盈余,其能將這一盈余配額在排放權交易市場上出售獲取收入。而對于高污染型企業,政府分配的免費排放額不足以覆蓋其在生產過程中排放量,這就導致了這類企業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從排放權市場上購買其他企業的排放額度,進而激發了企業創新意愿,提高了企業創新質量。如何在不同行業類型企業間分配排放權額度及對排放權配額交易價格進行定價就顯得非常重要。當高污染型企業在排放權交易市場上購買排放配額的費用低于企業創新研發支出時,可能并不能很好地激勵企業進行創新;相反,當購買排放權費用較高時,更能激勵企業進行創新,因為從長遠來看,通過研發出環境友好型生產工藝不僅能避免繳納環保稅,還能在社會公眾樹立環境友好的負責任企業形象有利于營銷,在競爭對手間形成技術領先優勢搶占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