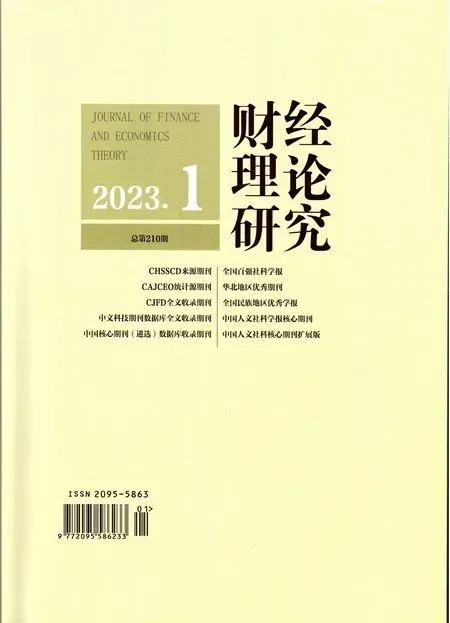工作重塑如何促進員工職業呼喚的實現:建設性責任知覺與親社會動機的作用
李亞慧,郭 曈,鄭文麗
(內蒙古財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一、引言
胡小武對90后群體的言語和行為進行了全面分析,發現他們能感受到國家號召和社會需要,主動參與到奉獻他人和社會的工作之中,并在此期間對自己的職業使命有了清晰認識,在工作中展現出他們的職業使命感[1]。職業使命感在國內研究又被翻譯為職業呼喚[2-3]。所謂職業呼喚,是個體對工作的主觀感受,指個體渴望在工作中尋求和實現個人的價值感和意義感[4]。也就是說,職業的使命不在于物質利益和地位的提高,而在于工作所帶來的成果、意義和目的[5]。有調查證實,職業呼喚對員工的工作投入、工作幸福感、工作滿意度、創新行為、建言行為、職業承諾等有顯著的正向影響[6-12]。由此看來,職業呼喚能夠為激勵效應、職場效應等帶來極大的促進作用,但是怎樣引導員工形成職業呼喚呢?近期有研究從組織心理安全氛圍、差序氛圍、精神型領導、領導-成員交換的角度探討了對員工職業呼喚實現的作用[13-16],但是以上的研究結果不足以形成系統性的結論,因此有必要對職業呼喚的形成機制進行深入探討。
職業呼喚是人們重新建構工作的內在價值,這意味著人們需要重新理解工作以適應當前情境,這種理解又來源于如何進行工作重塑。工作重塑是一種調整工作情形、特質與認知的方式,是提升工作意義的關鍵形式[17]。Akkermans證明工作重塑可以提高個體對其工作的認同感、幸福感和意義感等[18]。這與職業呼喚的積極影響不謀而合,因此工作重塑很可能與員工職業呼喚顯著相關。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則為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之間關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基礎要求得到滿足之后,人們就會對精神文化和價值成就有所渴望,向自我實現努力。也就是說,進行工作重塑的員工不再滿足于一成不變的工作內容,而是尋求挑戰性和突破性,邁向更高的成就。同時,也意味著員工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優勢,感受到自己在組織中是有價值的,此時員工易于體會到工作意義感從而實現職業呼喚[19]。在此基礎上,本文從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角度出發,探索工作重塑與員工職業呼喚之間的關系及影響機制。
員工內在動機與職業呼喚的實現有著密切的聯系[20]。所謂內在動機,是指個體出于對工作的熱愛或者對工作的興趣等,而產生工作的欲望[21]。如果在工作重塑影響職業呼喚的過程中,增強員工的內在動機,是否可以增強職業呼喚的實現程度呢?建設性責任知覺是能夠促進組織建設性變革的內在動機[22],與本研究息息相關。建設性責任知覺體現的主動性責任意識,可以幫助員工建立職業呼喚的價值取向。從自我決定理論的視角,員工通過滿足工作重塑的三個需求,可以提高建設性責任知覺,進而員工會得到積極而滿意的工作結果。由此可知,工作重塑有助于員工形成積極樂觀的工作行為,獲得較強烈的建設性責任知覺,從而驅使員工建立對他人和組織的責任意識、追求工作的內在意義,實現職業呼喚。為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建設性責任知覺在工作重塑和職業呼喚之間的中介作用。
職業呼喚的一個重要特質為親社會性[3],因此,親社會動機可能在職業呼喚的實現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親社會動機強調了個體愿意將自己的精力奉獻給他人的意愿[23],親社會動機強烈的員工不僅對組織發展有責任感[24],而且親社會動機促進了同事之間的合作、互助、支持等行為[25]。也就是說,當員工在通過建設性責任知覺來影響工作重塑激發職業呼喚的過程中,親社會動機可能會成為促進員工實現職業呼喚的主要因素。據此,本研究引入親社會動機,試圖探索員工親社會動機在建設性責任知覺和職業呼喚關系間的調節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基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梳理工作重塑對職業呼喚的作用機制,探究建設性責任知覺的中介作用和親社會動機的調節作用,逐步豐富新時代職業呼喚的理論研究,并從企業如何引導員工實現職業呼喚的角度提供有益的對策與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職業呼喚
Bellah等把職業呼喚概念運用于實際工作場景中,并將其與謀生取向、職業取向并稱為工作價值的三種取向[5]。每一種取向都代表人們所希望在他們的實際工作中尋求到的不同意義。對于謀生取向的人而言,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外在報酬;對于職業取向的人來說,工作目的在于獲得權力或威名;而具有職業呼喚取向的員工則將自己與工作視為一體,表現出愿意幫助他人和服務社會的意愿,是個人價值的實現[5]。本文將參考Duffy和Autin對職業呼喚的研究定義——職業呼喚是個體對職業的一種主觀感受,指個體期望通過工作尋找人生的內在意義,并最終實現自我價值[4]。
對于每個員工來說,工作不僅是一種物質補償的手段,也是實現個人成就感的途徑[12]。而職業呼喚正是回應內心追求、激勵自我的重要過程,使個體能體會到真實自我與個人使命感[26]。這也是學者們呼吁加強對職業呼喚形成機制研究的原因[3,27]。近期,已有部分學者把關注度轉向對職業呼喚的形成機制研究。例如,朱曉妹等認為企業中良好的心理安全氛圍對員工找尋工作成就感與使命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也能夠對職業呼喚的形成產生正面的影響[13];黃攸立等證明了差序氛圍可以成為職業呼喚的前因變量之一,差序氛圍通過削弱員工的心理授權,從而削弱員工對職業呼喚的塑造力[14];史珈銘等將自我決定理論與職業呼喚相結合,在此視角下精神型領導將提升員工的工作意義感和親社會感知,從而促進員工職業呼喚的實現程度[15];章雷鋼等證實在員工職業呼喚提升的過程中,高質量的領導-成員交換在中間扮演著重要作用[16];田紅彬和田啟濤也證實了不同的領導風格對員工實現職業呼喚的效果不同,他們認為在工作中服務型領導有助于員工實現自我成長與自我價值,更有益于追求自己的職業呼喚[28]。還有學者認為契合可能是職業呼喚的來源因素之一[20]。O’Neal指出個體在工作中會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和探索,對工作內容等有把握之后,會逐漸建立與工作的契合感[29]。與工作的契合感實際上是一種對工作的自我調整,只有當工作中的任務和關系等與個體能力相配時,才能達到與工作的默契度和契合度。工作重塑不僅反映了與工作的契合感,也反映了個人對工作意義的理解。而能夠在工作中體會到意義感,也是個體追求職業呼喚的典型表現[28]。
對組織而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使員工擁有工作動力,職業呼喚的內在激勵效用是員工保持工作動力的重要因素。綜上,對職業呼喚前因與形成機制進行深入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
員工主動通過對工作的重新認識與實踐、幫助他人救助社會來獲取不一樣的工作意義與體驗,在此期間,他們會逐漸建構對國家和社會的職業使命感。綜合田喜洲等的研究,將與職業呼喚相聯系并為適應當前情況重新調整工作,從而產生工作意義感的行為稱為工作重塑[30]。Wrzesniewski和Dutton界定工作重塑為:員工在自我驅動下,根據個人優勢、動機和激情,相應地調整工作內容、重構工作關系、改變角色認知等,并與當前的工作相匹配的積極行為[31]。
魏新等分析總結有關工作重塑的研究文獻,整理出與工作重塑研究密切聯系的高頻詞:工作績效與工作投入等[32]。以此看出,以往針對工作重塑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工作結果,鮮有學者把工作重塑與工作內在價值聯系在一起。但在社會多元化背景下逐漸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員工,對實現自身人生價值的呼聲愈來愈高,此時職業生涯與工作價值緊密相關的話題,也引起了大量研究者的重視,由此凸顯了對生活與工作有指導和實踐意義的工作重塑。職業呼喚作為一種體現個體內在工作價值的主觀感受,必然也會受到工作重塑的影響。
田喜洲等認為個體可以通過重新塑造工作任務的方式幫助員工獲得工作意義,也可以理解為個體改變對工作的認識,對回應職業呼喚有重要促進作用[30]。倪旭東和楊露琳提出員工可以通過工作重塑主動地擴展工作范圍、改變角色認知,從而提升工作中的意義感,增加實現職業呼喚的可能性[20]。總而言之,通過工作重塑,員工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需要和愛好,有針對性地結合自己的工作任務、方法和認知,重新詮釋工作內容、構建意義,這是通過需求的滿足來實現職業呼喚的一種途徑[33]。
結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基礎的要求達到滿足之后,人們會對精神和成就上的追求有所期盼,進而達到自我實現[34]。員工自我實現的需求主要體現在渴望創造自身價值、積極主動地投入到工作中,這也是企業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對于工作重塑的員工來說,他們的工作已不再局限于企業日常程序化的事務,他們期望突破自我,這或許就是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因為重塑工作的再設計過程,為員工搭建了表達自己的平臺,讓他們在滿足期望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而職業呼喚也是員工的一種工作追求,員工在追求呼喚的過程中能感受到為自己發聲的滿足感,從而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需求。基于此,以工作重塑作為自我實現的出發點,將展現自己與工作相結合,尋求更高層次的工作滿足,努力邁向自我實現,即實現職業呼喚。在工作重塑的影響下,員工能夠滿足職業需要,實現自我價值,因而容易形成職業呼喚。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工作重塑對職業呼喚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建設性責任知覺的中介作用
擁有職業呼喚價值取向的員工,能夠認識到對改善組織福祉的責任[35]。換言之,員工的責任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職業呼喚的實現,但是責任感不能準確地表達員工對組織的職守,反而是建設性責任知覺可以更為準確地解釋員工對組織的義務與責任。具體來說,建設性責任知覺是個體能夠意識到自己對工作有責任與義務并有意愿為組織發展而提出建設性意見[36],這是員工積極革新的主要驅動力[37]。根據趙海霞和鄭曉明的研究,員工的職業呼喚越強,他的內在動機同樣越強[2]。而員工主動承擔起對工作的責任,正是建設性責任知覺是一種主動性內在動機的體現[22]。因此,職業呼喚作為一種積極的心理信念,與建設性責任知覺這一內在動機可能存在較強相關性。從以往的文獻也可以看出,職業呼喚與建設性責任知覺存在密切的聯系。例如顏愛民等研究證實高職業呼喚取向的員工,更有可能產生強烈的建設性責任知覺[38]。不僅如此,自我決定理論也為建設性責任知覺在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之間的中介作用提供了理論聯系。
自我決定理論認為社會環境可以通過滿足個體自主、勝任、關系三種基本心理需求,增強個人的內在動機,促進外在動機的轉化,從而獲得積極的工作成果[39]。可知,自主需要是個體擁有自主工作的動力,是心理上的自由感和行動上的選擇感,能夠幫助員工做出正面的工作行為。這種自主性也為員工的工作重塑行為奠定了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員工具備了調整和改變自己的能力,同時也獲得了改變工作方式的機會,在工作中沒有相應的壓力和束縛,才能進一步地產生工作重塑行為。為此,可通過自我決定理論的角度理解員工進行工作重塑的需求。具體而言,工作重塑中的任務重塑要求員工對工作動態有一定的掌控感,能夠主動并及時做出調整,通過任務重塑滿足自主需要。工作重塑中的關系重塑會影響員工的人際關系,包括與他人的交往程度、與同事互相學習和溝通。在任務重塑和關系重塑的基礎之上,員工通過自發地改進工作效率與質量、與團隊成員溝通交流,提升他們對工作的感知,此時員工進行了認知層面的重塑,通過對工作的重新理解,員工更易形成對工作的勝任力,進而滿足個人的勝任需要。基于以上分析,工作重塑能夠滿足自我決定理論中的三種基本心理需要,進而增強充當著內在動機的建設性責任知覺,從而實現職業呼喚。
總的來說,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建設性責任知覺作為一種主動性內在動機,會在員工工作重塑的影響下逐漸增強,同時隨著建設性責任知覺的增強,員工會得到滿意的工作體驗與結果,從而激發職業呼喚的實現。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設:
假設2:建設性責任知覺在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之間起中介作用。
(四)親社會動機的調節作用
以職業呼喚為導向的員工會為他人提供幫助,認為組織利益先于個人利益,甚至愿意為整個社會做出貢獻[12]。親社會動機是一種關注他人的心理變化過程,在意愿上傾向于幫助他人和社會,或為他人付出[23]。因此,員工實現職業呼喚的過程中,親社會動機或許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組織中,高親社會動機的個體能夠發揮責任意識,為組織目標與發展做出貢獻[24]。并且具有較強的親社會動機的員工傾向于從事諸如同事合作和同事支持之類的行為[25],具體如組織公民行為、團隊任務反思和建言行為等[40-42]。以上文獻傳遞出同一思想,即當員工具有親社會動機時,更愿意采取無私的行為,提高自身的奉獻精神和使命感,進而得到積極的工作結果,這些都很可能進一步激發員工的職業呼喚。
由此,在工作重塑通過建設性責任知覺影響員工職業呼喚的過程中,當員工的親社會動機占據主導地位時,其自身就更傾向于換位思考、幫助他人,更易培養對工作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但在員工實現職業呼喚的過程中,其親社會動機傾向較低時,他們考慮問題更可能以自我為中心,或者說他們行為處事可能更自私,這樣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無責任感,更不會體會到個人價值,因此本研究認為親社會動機會影響到建設性責任知覺對職業呼喚的作用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3:親社會動機在建設性責任知覺影響員工職業呼喚的過程中起到調節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以工作重塑的視角探索了員工職業呼喚的前因變量。首先,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員工在工作重塑時,他們的基本工作需要都已經得到了滿足,但他們仍然期望突破自我,或許這就是追求職業呼喚的表現。本文預期工作重塑對員工職業呼喚實現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其次,在自我決定理論的視角下,通過滿足員工工作重塑的三種需要,增強建設性責任知覺,進而促使員工的職業呼喚逐漸實現。因此,本文預期建設性責任知覺在員工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之間起到中介作用。此外,因親社會動機會釋放有利于本組織的信號,在工作重塑通過建設性責任知覺影響員工職業呼喚的過程中,高親社會動機可起到促進作用。因此,親社會動機將在建設性責任知覺與職業呼喚之間起到調節作用。綜合以上基礎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構建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了數據資料。問卷樣本主要來自于內蒙古自治區的企事業組織工作人員,問卷的發放形式以網絡訪問為主,結合部分訪談,被調查者可以直接通過鏈接填寫。為了使研究的數據更加嚴謹,本研究分別在三個時間點收集了員工的數據,每個時間點之間相差近一個月。本次調查共回收507份問卷,其中涉及工作重塑、建設性責任知覺、親社會動機和職業呼喚變量。在對數據填寫明顯存在問題的問卷進行刪除后,最終得到有效問卷472份。首先,被調查者中,男性234人,占比49.58%;女性238人,占比50.42%。其次,25歲及以下145人,占比30.72%;26~35歲205人,占比43.43%;36~45歲87人,占比18.43%;46歲及以上35人,占比7.42%。另外,受教育程度中,高中及以下53人,占比11.23%;大專90人,占比19.07%;本科254人,占比53.81%;碩士及以上75人,占比15.89%。最后,從工齡來看,1年及以下的員工85人,占比18.01%;2~5年的員工163人,占比34.53%;6~10年的員工134人,占比28.39%;11年及以上的員工90人,占比19.07%。
(二)變量測量
為了保證量表的信度與效度,本研究均采用國際經典的、被學者廣泛應用的成熟量表。以下量表均以Likert 5點量表的形式計分,由1至5分依次對應“完全不符合”“比較不符合”“不確定”“比較符合”“完全符合”。
1.工作重塑:采用Slemp和Vella-Brodrick(2013)開發的量表[43],共15個題項。該量表中的代表題項有“我會通過主動修改任務的類型或范圍等方式,更好地完成工作”“我會思考工作是如何使我的生活富有目標”“我會積極地組織或參與到與工作相關的社交活動”等。
2.建設性責任知覺:采用的是Liang等(2012)開發的量表[44],共5個題項。該量表中的代表題項有“我應該盡我所能為公司提出想法或解決方案來實現其目標”“我應該盡我所能為公司提出優秀的想法,以確保我們的客戶得到滿意和良好的服務”“如果有必要,我會從我的個人日程中抽出一些時間為公司提出想法或解決方案”等。
3.親社會動機:采用的是Grant(2008)開發的量表[45],共4個題項。該量表中的代表題項有“希望我的工作對他人起到幫襯的作用”“我想通過我的工作對他人產生良好的影響”“通過我的工作為他人做出貢獻對我來說很重要”等。
4.職業呼喚:本研究采用的是Dobrow和Tosti-Kharas(2011)開發的量表[46],共12個題項。該量表的代表題項為“當我向別人描述我是誰時,我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職業”“即使遇到困難我也會繼續選擇追求我的事業”“我的職業能深深打動我的心,給我帶來快樂”等。
5.控制變量:借鑒先前關于職業呼喚的文獻研究,本文選取了人口統計學中的四個因素作為控制變量,依次為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工齡,均在基礎信息部分測量。
四、研究結果
(一)量表信度檢驗
本文采用CR指標和Cronbach’s α系數對量表的信度進行雙重檢驗。如表1所示,CR指標值均高于0.7,其中工作重塑CR值為0.894,建設性責任知覺為0.857,親社會動機為0.845,職業呼喚為0.930。Cronbach’s α系數同樣均大于0.7,其中工作重塑α系數為0.847,建設性責任知覺為0.790,親社會動機為0.754,職業呼喚為0.913。綜上所述,本文所使用量表的信度系數值均滿足要求,樣本通過了內部一致性的信度檢驗。

表1 量表信度檢驗結果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和區分效度檢驗
本研究將數據導入AMOS 26.0中,觀察其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目的是進一步檢驗工作重塑、建設性責任知覺、親社會動機、職業呼喚這四個變量之間的區分效度,結果如表2所示。通過對單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和四因子模型的擬合指標比較得出,四因子模型的擬合程度最佳(χ2=941.752,df=399,χ2/df=2.360;RMSEA=0.054;IFI=0.911;TLI=0.902;CFI=0.910),并且顯著優于其他三個因子模型。因此,本研究的四個變量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

表2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三)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的數據收集方法主要是問卷調查,員工對自變量工作重塑、中介變量建設性責任知覺、調節變量親社會動機、因變量職業呼喚均采取自我評價的形式,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基于研究的嚴謹性與準確性,本文采用Harman單因子檢測方法,將每一項題項的數據全部進行因子分析,通過觀察未旋轉的主成分來判斷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方法提取了4個共同因子后,結果顯示,第一大因子能解釋方差為35.992%,小于40%的臨界值,所以本研究認為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可以進行數據分析。
(四)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在表3中,本研究分析了工作重塑、建設性責任知覺、親社會動機和職業呼喚四個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之間呈現明顯的顯著性(r=0.597,p<0.01);工作重塑與建設性責任知覺之間的相關系數r=0.717(p<0.01),建設性責任知覺與職業呼喚之間的相關系數r=0.567(p<0.01),同樣呈現出明顯的顯著性;建設性責任知覺與親社會動機之間的相關系數r=0.590(p<0.01),親社會動機與職業呼喚之間的相關系數r=0.448(p<0.01),說明上述兩兩變量間也顯著相關。以上數據初步支持了文中假設,接下來將進行回歸模型檢驗。

表3 相關分析結果
(五)假設檢驗結果
本研究基于472份有效樣本數據,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對工作重塑、建設性責任知覺、親社會動機和職業呼喚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如表4所示,本研究將因變量職業呼喚帶入PROCESS中進行回歸,得到了7個模型。其中,模型1是在控制被調查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工齡變量之后,檢驗對職業呼喚的影響。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自變量工作重塑,檢驗其對職業呼喚的直接影響。模型3增加了中介變量建設性責任知覺,旨在檢驗工作重塑影響職業呼喚的過程中建設性責任知覺的中介效應。模型4是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檢驗人口統計學變量對建設性責任知覺的直接影響。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礎上,加入自變量工作重塑,檢驗其對中介變量建設性責任知覺的影響。模型6是在加入中介變量建設性責任知覺時,檢驗親社會動機對職業呼喚的影響作用。模型7是檢驗親社會動機對職業呼喚的調節作用。
根據表4的分析結果可知,模型2的結果顯示工作重塑對職業呼喚的回歸系數β=0.762(p<0.001),因此工作重塑對職業呼喚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假設1得到驗證。

表4 PROCESS回歸結果
根據模型3,在控制變量基礎上,將工作重塑與建設性責任知覺同時對職業呼喚進行回歸時,工作重塑的直接效應顯著(β=0.514,p<0.001),同時建設性責任知覺對職業呼喚有顯著影響(β=0.312,p<0.001)。因此,建設性責任知覺對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的中介效應可得到驗證。同時根據模型5,在控制變量基礎上,工作重塑對建設性責任知覺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β=0.796,p<0.001)。
根據模型6,在控制變量基礎上,以職業呼喚作為因變量,加入中介變量建設性責任知覺和調節變量親社會動機,此時建設性責任知覺對職業呼喚有顯著影響(β=0.522,p<0.001),親社會動機對職業呼喚的作用呈現顯著性(β=0.218,p<0.001)。而模型7在模型6的基礎上,加入建設性責任知覺和親社會動機的交互項后,可知交互項對職業呼喚的作用并不顯著(β=0.046,p>0.05)。因此,假設3未得到驗證。
(六)建設性責任知覺的中介效應檢驗
通過上述回歸分析結果可知,中介變量建設性責任知覺的效應得到初步驗證,因此可以進一步對建設性責任知覺在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之間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本研究在SPSS宏程序PROCESS中,將職業呼喚放入因變量框,通過抽取5000次Bootstrap樣本,進行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如表5。工作重塑通過建設性責任知覺對職業呼喚的總效應是0.762,置信區間為[0.668,0.855];直接效應是0.514,置信區間為[0.384,0.774];間接效應是0.248,置信區間為[0.135,0.351]。可知上述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因此建設性責任知覺的中介效應得到進一步檢驗,假設2得到驗證。

表5 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
綜上,整理得到本研究的結果模型如圖2。

圖2 結果模型圖
五、總結與展望
本研究從激發員工工作熱情的實際問題出發,基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依據472份問卷調查數據,運用AMOS 26.0、SPSS 26.0以及SPSS宏程序PROCESS,實證檢驗了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工作重塑能夠正向促進員工的職業呼喚,建設性責任知覺在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關系之間可以起到中介效應,但親社會動機對職業呼喚的調節作用并不顯著。基于此,本研究為探索影響職業呼喚的潛在因素得出一些結論,并為企業激勵員工工作提供一些啟示。
(一)理論意義
第一,展開了員工職業呼喚的形成機制研究。本文從需求層次的視角拓展了職業呼喚的形成機制研究,驗證了工作重塑對員工職業呼喚的促進作用。這與田喜洲等發現的彌補職業遺憾、回應內心呼喚的邏輯相契合,即個體應該對自我有清晰的認識,重新理解工作與生活的意義進而構建最好的自我,重視個體內心的呼喚[30]。同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與職業呼喚結合應用也為探索影響員工職業呼喚的潛在影響因素提供了新的視角,今后應當重視在職業呼喚研究背景下對該理論的運用。
第二,建設性責任知覺的中介效應。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可以解釋建設性責任知覺在工作重塑與職業呼喚之間如何起到連接作用。一方面,田喜洲等指出,個體響應呼喚易形成較高的工作激情與責任感[3]。據此,學者普遍認為職業呼喚的實現與個體對組織的責任感密不可分[35,47]。本文證實了建設性責任知覺正向影響員工的職業呼喚,這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強調了員工主動性成分更強烈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本文在自我決定層面下得出研究結果:在滿足員工工作重塑的需求后,作為內在動機的建設性責任知覺得到強化,進而得到滿意的工作結果的過程。揭示了員工在工作重塑影響下,從建設性責任知覺轉變為職業呼喚的心理歷程,進一步拓展了自我決定理論。
第三,親社會動機對職業呼喚的調節效應。在以往研究中,學者普遍認為親社會性是職業呼喚的基本屬性[2]。但在本研究中親社會動機的調節效應在職業呼喚中未得到驗證,雖與以往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但也說明了親社會動機對職業呼喚的影響作用需要在一定的背景下完成。結合當前時代背景,出生于20世紀80、90年代的新生代員工與60、70年代員工不同,他們接受的是正規教育,新時代的道德教育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普及性較好。尤其是本研究的問卷樣本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被調查者基本屬于在新時代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員工,文化水平、道德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更易形成親社會動機傾向。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學者全面了解親社會動機的適應條件和職業呼喚的影響因素,未來研究無需考慮親社會動機對職業呼喚的調節作用,可以在其他方面挖掘親社會動機與職業呼喚的相關性。
(二)實踐啟示
員工對工作的責任和使命使員工持續產出積極的工作態度和行為,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不竭源泉,也是企業創造收益的關鍵因素。因此,本文從激勵員工形成職業呼喚的工作價值取向的角度,為管理者實踐提供以下三個方面的啟示:
第一,引導員工進行有效的工作重塑。工作重塑鼓勵員工主動調整工作內容,賦予其一定的工作彈性,使其更加積極地為工作做出貢獻。因此,企業應將員工安排在合適的崗位上,有效協助員工克服工作困難和障礙,建立反饋機制,響應員工訴求。另外,企業應支持員工有效地進行工作重塑,引導他們把一些契機、技能、設施與工作重塑結合,如改進低效能的工作習慣、總結與分享成功的工作經驗等,將所完善的工作模式更好地與自身特征和價值追求相融合,以此激發員工的職業呼喚。
第二,鼓勵員工提升建設性責任知覺。如今依舊有“自我”“脆弱”“垮掉的一代”等負面而消極的詞語形容著80、90后的年輕人[48]。但在特殊事件里,“逆行者”展現出他們對國家和社會情感的認同與責任[1]。因此,要重視培養員工的建設性責任知覺,對他們進行心理教育,調整心態由“逃避擔當”到“勇于擔當”,引導他們形成對工作內容與工作意義的清晰認知;給予員工自由發揮的空間,在工作崗位職責的范圍內,讓員工主動參與到工作設計中;組織要讓員工及時了解其發展目標,表現出期望員工承擔組織發展的責任與擔當,讓員工意識到他們的工作對于組織的發展至關重要,以激發員工的建設性責任知覺。
第三,重新理解親社會動機。親社會動機體現出個體的內在價值,以及在團體中協作互動的需要。以往可以通過培養的方式,幫助員工建立同理心,引導員工的價值立場、價值取向,提升員工的親社會水平。新生代員工已逐漸建立了多元化的價值觀念,他們堅守著自身認為正確的信仰或立場[49]。當危機來臨時,人們被激發出對國家和社會的感情,更多的人愿意換位思考、幫助他人,促使親社會性成為更多人的“標簽”,而不再是影響員工形成職業呼喚的主要因素。但管理者在實際工作情境中,依舊需要引導員工形成正確的價值觀,維持員工的親社會水平,特別是高職業呼喚取向的員工,也不可忽視親社會動機對其職業呼喚實現程度的影響作用。
(三)不足和展望
本文的研究內容存在一定的局限與不足。首先,本研究主要采取線上發放問卷的方式,可能存在樣本分布不均衡的弊端,未來研究可采取與員工面對面訪談的形式收集數據。其次,本研究主要選取員工自評的方式測量各變量,不能完全消除共同方法偏差影響研究結論準確性的可能,未來的研究可采用領導與員工匹配的形式進行。再者,本研究基于橫截面數據進行研究分析,盡管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相對應,但仍然存在變量間的因果關系不準確的可能性,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橫向研究與縱向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全面而準確地驗證研究結論。最后,本研究只針對個體的心理變量進行研究,未來研究需要探索更多影響員工自我價值實現的因素,為積極構建員工的職業呼喚價值取向奠定基礎。
此外,今后的研究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深入思考:一是應該考慮到不同年齡階層的員工,探討不同時代背景下親社會動機影響職業呼喚時的情景條件。二是本文僅探討了親社會動機對職業呼喚的調節作用,因學者普遍認為職業呼喚具有親社會性,因此可以從職業呼喚影響親社會動機的角度展開今后的研究,進而從另一個層面研究職業呼喚與親社會動機之間的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