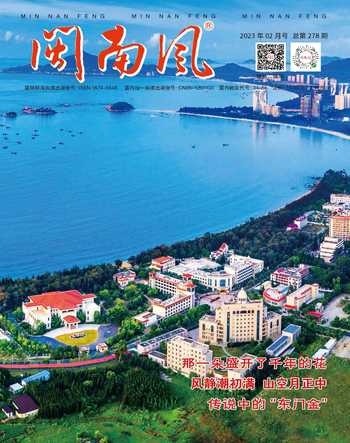幽巷覓書香
翁得祿
石碼鎮依山傍水,精致而安逸,既有繁華都市的靚影,又有山野田園的韻味,更有水運漁趣的風光,其深厚的歷史底蘊為整座古城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偷得浮生半日閑,拂去俗世的喧囂繁華,以一顆詩情畫意的心靈去尋覓一處靜怡的去處,讓好奇的目光去探索這座神秘的古城。
悠閑而又懶散的步伐在石碼古街中敲響,隨處可見風格獨特綿延不絕的紅磚騎樓,相互貫通縱橫交錯,形成老石碼一條條寬窄不一的街巷。沿著解放東路拐進一條幽深的巷子,筆直的巷道僅容得下來往之人擦肩而過,巷道兩旁家家戶戶懸掛著獨具閩南特色的“竹格屏”,令整條小巷充滿古色古香。如今的石碼街頭到處可見高樓聳云,店鋪林立,這條小巷子如同恒河中的一粒沙塵,在石碼鎮中并不起眼,只有附近居民和過往路人才會走進這條小巷深處,可它卻有一個美麗的名字“書巷”。據聞,在清朝康熙年間,石碼錦江書院的校門正是處于這條巷子之中,因此得此雅稱。

書巷中段有一道火焰形西式“隘門”,穿過“隘門”沿著筆直的小巷即到達“訓義埕”。“埕”,在閩南方言中泛指一小片空曠之地,主要形成于房屋之前,為大人閑話家常、小孩嬉戲打鬧,居民晾曬衣被或舉辦紅白喜事活動的場地。訓義埕內有十來座頗具規模的古厝,燕尾翹脊、飛檐斗拱,雖歷經歲月洗禮,中西交織的壁畫裝飾和屋檐窗格的漆金字畫也已斑駁難辯,卻難掩舊時屋主的顯赫家世與古代海絲淵源。
穿過一道窄小的院門跨進訓義埕8號院落,極目環顧,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由四根方形木柱支撐而起的亭榭,亭榭名喚“讀書亭”,為學子們朗朗讀書之所。原來,這座院落舊時喚作“成德書院”,始建于清朝年間,為當時的巡撫楊泰所建,后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賣給張汝湖。清道光年間,張汝湖裔孫將“書院”轉賣給了當地一名武進士陳望三,到了民國十二年(1923),陳望三裔孫又將大厝賣給了黃鳴環,續而輾轉至現在的屋主黃和根。但是,該“書院”并非真正的書院,而是當時屋主比喻“風景如畫,適宜讀書”之意。
讀書亭之前建有蓮花池,池中靜蓮亭亭玉立清香宜人,有的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的已然“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這時,數條鯉魚悠游自得地從荷葉之下嬉戲穿梭而過,留下一層層微波四散而開。繞過蓮花池則是佛堂,堂中一張頗具古早味的紅木桌臺雕刻講究古樸精致,桌上供奉著數尊神佛塑像和一只香爐,香爐中三根清香散發出一絲絲白霧在佛堂中繚繞。
讀書亭銜接之處為院落主宅,主宅兩側各建一間護厝,護厝又與佛堂相連接形成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式古大厝。主宅坐南朝北,面闊三間,進深兩間,屋頂上檐梁相接,紅瓦鋪面,屋脊兩端的“馬背脊”線條彎曲柔和,圓融飽滿。屋檐下一排步步錦圖案的隔扇門窗上,十二條漆金龍紋圖騰抽象美觀。大門兩側的墻壁上各開一扇方形窗戶,窗頂上保存著兩幅凸起的壁畫雕塑。左側壁畫為一本折疊式翻開的書冊,書冊之中陰雕著“作未完問花尋生意,讀將倦聽鳥話天機”字樣;右側壁畫為一卷展開的書卷,書卷中刻有“居然室一斗讀書,甘讀苦讀苦讀到甘,只有這條路”。

步入主宅,正中為廳堂,左右各有一間廂房。廳堂用木屏風作為背景墻隔開前后門,穿過屏風門洞走出廳堂,此處為古厝梳洗晾曬的深井,深井右側是廚房和餐廳,左側則是偏廳和雜物間。穿過偏廳的小門是一座二層閣樓,閣樓下層為茶水間,茶水間側門外是一處后花園。花園不算太大,由三面圍墻構成,西面墻壁上為主宅廂房的窗戶,窗戶呈圓形,窗頂上扇形壁畫書有“解元頤”三字;花園東面的墻壁上遺留有“小院”字樣的殘畫,而北面的小門頂端則書有“幽暢”二字。花園之中擺放著一套青石桌凳,桌凳上的盆景青翠,奇石怪異,相得益彰。但由于年久失修且缺乏整頓,花卉的種植和擺放較為凌亂,使得這座后花園失去了往昔的生機!
閣樓的通道設置在茶水間與雜物間之間,穿過黯淡無光的樓道是一架陡而窄的木梯,不論是上還是下都得小心翼翼。木梯有一處拐角,轉過拐角便可抵達閣樓,樓梯之上設有一塊擋板,如同一扇木門將樓梯與閣樓隔斷。樓上只有一間房間和一個陽臺,通往陽臺的門上罩著一層紗網,為樓外的景色添加一絲朦朧之美。站在陽臺之上,可見門楣之頂書有“拾祿樓”三字,憑欄遠眺,足下的風景一覽無遺。這座“拾祿樓”便是石碼鎮尚存較為完好的“小姐樓”了。
小姐樓又稱為“閨閣”或者“繡樓”,是古代大家閨秀未出嫁前的小天地。封建時期對于女子的規定較為嚴苛,未出嫁的女子不能輕易走下繡樓拋頭露面,只有到了出閣的年紀方可下樓。因此,繡樓的梯道設計較為狹窄陡峭,登梯之時也就舉步維艱。拾祿樓的樓梯共有十四階,這便意味著住在樓上的小姐只有年滿十四歲方可下樓活動。如今,小姐樓依舊,只是不見當初倚欄而坐,用一針一線消磨時光的“窈窕淑女”!
夕陽猶抱琵琶半遮面,訓義埕內的古建筑還有很多,由于時間關系只能粗略地走馬觀花一覽而過,心中雖有不舍,但“成德書院”深厚的文化底蘊卻在心里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