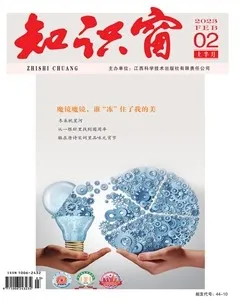阮籍的口哨
馬慶民

“白眼看他世上人”“舉觴白眼望青天”……有關“白眼”的詩句不在少數,而第一個給“白眼”賦予引申意義,并讓無數文人不惜筆墨為之吟詩作賦的人,非“竹林七賢”中最狂放不羈的阮籍莫屬。
阮籍除了愛翻白眼之外,還有一大喜好——吹口哨。
西晉的成公綏對吹口哨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動唇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這大概類似于今天的口哨表演。
不過,在古代,吹口哨更多的是用“嘯”來表示。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寫道:“嘯,吹聲也。”《辭海·詞語分冊》進一步說明“嘯”是指“撮口發出長而清越的聲音”。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有關于“嘯”的記載。這種技藝在漢、魏、晉時很有名,如諸葛亮、曹植等人就很會吹口哨。據說他們閑坐無聊時,常以吹口哨來打發時間,稱之為“坐嘯”。陳子昂在《為資州鄭使君讓官表》中寫道:“坐嘯徒積,主諾空慚。”蘇軾也寫過“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的詩句。
當時,阮籍無法實現抱負,故常用吹口哨來發泄不滿。因為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吹出來的口哨極富音律韻味,十分優美動聽。《世說新語·棲逸》中記載:“阮步兵嘯,聞數百步。”所以一時間大家爭相效仿,連鼎鼎大名的陶潛也常“嘯傲東軒下”。口哨成為當時的一種習俗、一種時尚,進而演變成一種音樂。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春節之后,阮籍從武寧縣家中出發,坐船來到大庾嶺南埜縣(今江西省大余縣),探望遷居南埜縣朱屋棚的大哥阮竺。在這里,阮籍遇到帶兵南下征戰的司馬昭。司馬昭一直想拉攏阮籍,但苦于沒有很好的機會。這一次,謀士蔣濟就給司馬昭出了個主意:與阮籍聯姻。
于是,司馬昭派人到阮籍的家里提親。阮籍很清楚司馬昭的用意,根本就不想結這門親,但又不能得罪司馬昭,他就想出一個絕招——醉酒復長嘯。
阮籍開始足不出戶,每天拼命地喝酒、坐嘯,從早到晚不是酩酊大醉,就是長嘯不止,一連兩個月,天天如此,那個奉命前來提親的人根本沒辦法向他開口。最后,提親的人只好將這個情況如實地回稟司馬昭。司馬昭無可奈何地說:“唉,算了,這個醉鬼,由他去吧!”
在“醉酒復長嘯”的這段時間里,阮籍的口哨技藝得到很大的提高,他自認為已經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天下無人可與之媲美。
這一日,阮籍去拜訪靈隱寺方丈,動情地談天說地。可方丈卻似聽而不聞,一聲不響,連眼珠子都不動一下。阮籍無奈,就干脆對方丈吹起了口哨。這下子,方丈來了興趣,開口說:“可否再來一次。”于是,阮籍再次吹起口哨。然而,方丈又閉上眼睛,一言不發。阮籍覺得很是無趣,便索然寡味地下山了。
誰知剛行走到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蕩起優美的口哨聲。阮籍抬頭望去,原來是方丈在長嘯不已,那口哨聲似鸞鳳之音,幽妙和諧,一時間響徹山谷,禽鳥忘飛。
靈隱寺方丈的哨聲像天籟,又像來自心底的吶喊。頓悟的阮籍回到朱屋棚之后,就奮筆疾書寫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傳》。
在阮籍的影響下,吹口哨還在魏晉士族青年當中逐漸流行起來,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