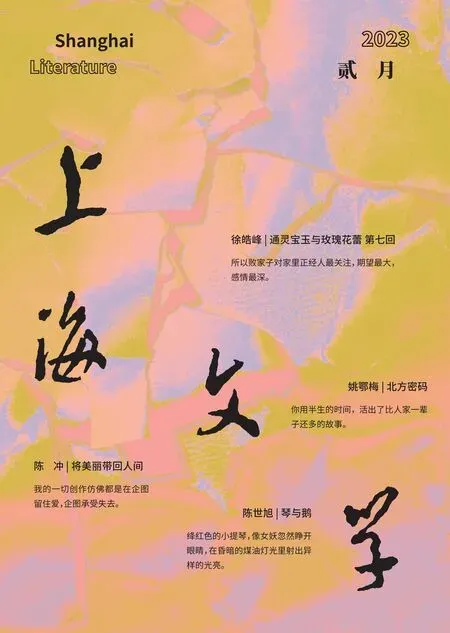詩六首
張新穎
詩:之,止,姿
米沃什《魔山》這首詩寫了三個真實的形象,
布德貝格、陳先生和他自己,
他們是伯克利的同事。
“聽說陳先生是一位有名的詩人,
這我當然確信,因為他寫詩只用中文。”
就像他本人,寫詩只用波蘭語:
“您寫詩使用的語言幾乎沒有人懂。
但是您的詩有人看重。這里有陽光。”
米沃什沒有寫出華人陳先生的名字,
但我們應該知道他,陳世驤。
早年寫作和評論新詩,與哈羅德·阿克頓合作
編譯《中國現代詩選》,一九三六年在
倫敦出版。
那時候他在北平,說“詩人操著一種
另外的語言”。
一九四一年他到了美國,幾年后受聘
伯克利,
逐漸轉向中國古典:
追蹤昏暗歲月掙扎苦痛的文心,
發掘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的創造力量。
陳先生講“詩”字的原始觀念,
說“詩”是這樣難產,
遠紹著ㄓ的語根:ㄓ象足著地,
同時具有“之”和“止”相反二義,
升騰出兩個繁復多面的高級觀念范疇,
限指心意為“志”,特著其言則謂“詩”。
足之往,足之停,自然地踏出節奏,
“之”—“止”—“之”—“止”。
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言之不足,嗟嘆,永歌,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
米沃什說在一所著名大學任教彌足珍貴,
他用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形容他和他的同事:
“甚至在熟睡中,我們也在為建設世界而工作。”
孤寂感能夠成為一種激情,之止合而為一。
陳先生在舊金山灣論述中國“詩”字
得形立義,
用英文講中國的抒情傳統,討論《詩經》《楚辭》,
他打橋牌,也打麻將,死去了將近半個世紀。
“在詩歌走動的年代,有多少代
蜂鳥陪伴它們。穿過這魔山。”——
之止成“姿”:
陳先生從中西文藝批評闡發“姿”字,明其為
活動最富有意義時的把握與表現,紀律與組織。
有 時
有時我坐在冬天的空茫里
空茫的陽光里
這樣的時刻不多 不長
為了抵抗窒息 我抽煙
本能一樣 一支接上一支
我偶爾會想起酷暑的太陽下
曾經奔走了整整一個夏季
多少年了 那種茫然 無措
以及里面的意志 還沒有完全消失
那時候會在樓頂打牌 光著膀子
比賽誰的皮膚被灼傷得更深
與烈日對抗 以及貪婪地吸取
尖利的光線把密密麻麻的疼痛刺進肉體
此時我坐在冬天陰郁間隙的陽光里
年輕的我回來看過我 我微笑
他察覺了愁苦而裝作若無其事
現在他走了 我慶幸他那時的空氣
異于此時
我習慣了但厭惡滿口煙味 我吐出一口
又抽一口 像是完成一次呼吸
破 曉
層疊的疲乏從身體的縫隙
消散 醒來 后半夜
意識中涌起真切的疼痛
我驚喜
如此清晰地感知
它是滯后的
睡眠過濾了白天紛雜的信息
空闊的黑暗中 此時 心地澄明
它才到達 適時而至
我專心聽著吹夜的風聲
而后放松地睡去
等再次轉醒 窗外鳥鳴交響
其中一個聲音連綿 激越 華麗
一浪一浪 沖刷黎明
這是新來的鳥嗎?
我翻找回憶 隨即放棄
改為試著稍微想象了一下 如何
沿著它的韻律滑行 如何
在努力和輕盈之間 持續平衡
平衡器
你必須發明一些小的歡樂
以應付不間斷滋生的瑣碎煩擾
是的 設立對沖基金
在心里造一個平衡器
用很長一段時間 學著調試
至于那個巨大的虛無
最好不要理睬它
因為無論如何 最終
它會把你吞沒
所以 重點是那些小的歡樂
以及平衡系數的設置
你能隨身攜帶 隨時操作
你得忍受住
對生活中某些事物的厭惡
而愛生活
愛生活像一句口號 哦 不
愛是從復雜纏繞中上出的
你要感謝生活也包容了你 縱容
你發明那些孤僻的小歡樂
不能與人分享
畢竟每個人總有獨屬的瑣碎煩擾
無法邀人分擔
你跟我說說
——你跟我說說河邊的事情
那片森林落光了葉子
所以聽不到夏天的喧囂和秋風里的低語
枝干出脫成黑瘦的線條 硬朗地分割
高遠的晴空 密密麻麻的雜草枯死
林間空闊而安靜
傍晚起了變化 樹上叢集大群的鳥
嘈雜地鳴叫 興奮 急切 不管不顧
而那個時候的光線是柔和的
柔和無邊 有些茫然 河水也茫然
那個時候沒有別的聲音
——你跟我說說你的事情
我發現黑暗不是慢慢降臨 是突然
那個時刻 就在鳥鳴突然停住了的瞬間
沒有預兆 整齊地噤聲
樹林里更安靜了 時間停滯
很久之后 有一只鳥粗嘎地叫了兩聲
突兀 短促 沒有回應
——你跟我說說別的事情
那只魯莽的鳥 或許
是冬天黑暗森林的沉默之心
我那么刺痛地感覺了一下
我點了一支煙 猶疑自己
想走出這片森林 還是
再待一小會兒
——你跟我說說沉默之心
仿戴望舒
我是二十一世紀的蝴蝶 所以我思想
幾千年前我的祖先飛進莊子的夢
迷夢如花 醒后困惑如花枝交纏
而花朵輕呼
透過無夢無醒的云霧
來震撼我斑斕的彩翼
但我不能起舞于今世 因為
他們囚禁了時間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