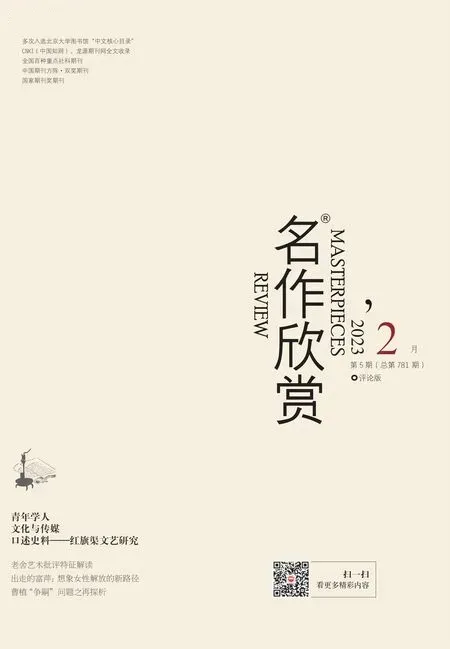中國動畫電影中的傳統文化元素
⊙劉曉妮 [尼山世界儒學中心,濟南 250101]
⊙王凱 [韓國清州大學藝術學院,韓國 清州 28503]
自從1926 年第一部動畫《大鬧畫室》誕生以來,中國動畫電影已經走過了將近一百年,在這近百年的歷程中,中國動畫電影的發展并非順風順水,而是在曲折中前進著。尤其是在1995 年到2015 年這二十年期間,國家為了扶持國產動畫,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黃金時間只能播放國產動畫,對國產動畫也按照制作時長進行補貼,在這種粗放型的扶持政策之下,一些制作方為了謀取政府更多的資金補貼,直接對國外動畫的內容生抄硬搬,制作出了大量粗制濫造的“山寨品”,如《高鐵俠》《馬拉松王子》《寵物小精靈傳奇》等,雖然這段時間也有零星的優秀作品,但很多人已經不看好中國動畫的發展。
2015 年,騰訊視頻播出了《中國驚奇先生》 《狐妖小紅娘》等一系列高質量的漫改動畫,標志著網絡動畫的興起,重燃漫迷對中國動畫的希望。在同一年,田曉鵬導演的《大圣歸來》 橫空出世,迅速超過了好萊塢動畫《功夫熊貓》的票房,成了動畫票房史上的第一。因此《大圣歸來》也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一致認為這是吹響中國動畫電影“歸來”的號角,此后的《大魚海棠》 《白蛇:緣起》 《哪吒之魔童降世》 《雄獅少年》 等動畫你方唱罷我登場,通過科技與藝術相結合的手段,對傳統文化元素進行創新,開創了中國動畫電影市場的新局面。
一、中國動畫電影對傳統文化元素的繼承運用
動畫是科技與藝術相結合的產物,隨著二維動畫技術向三維動畫建模的發展,動畫電影的表現形式也產生了巨大的變革,給觀眾帶來無與倫比的視聽體驗,然而動畫的內在意蘊仍是由其核心思想以及表現內容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動畫電影的思想內容是其藝術性質的根本所在。從這方面來說,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已經具備了博古通今的藝術性質,動畫電影在對傳統文化元素內容的創新運用方面,有著天時地利的優勢。
(一)取材于傳統文學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學不但作品的數量非常突出,而且取得的成就十分輝煌,其生動地體現出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傳統文化當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動畫不斷開拓創新的今天,豐富多彩、包羅萬象的傳統文學成了國產動畫電影源源不斷獲取創作題材的源泉,事實上,國產動畫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就和傳統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如取材于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記》的動畫有《大鬧天宮》《天上掉下個豬八戒》《鐵扇公主》,取材于《史記》的《東郭先生》,取材于神魔小說《平妖傳》的《天書奇談》等,題材的來源不拘,神話、史實、小說、戲曲等都可以,將其經過改編加工之后,用一種全新的藝術方式呈現出來。事實證明,動畫產業發達的國家,其優秀的動畫作品,無一不是根據經典文學改編而成的,例如在美國迪士尼動畫所制作的作品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改編自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那些經典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必定是經歷過歷史和人民的考驗,成了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那么,動畫的內容以此為基礎進行創作,無疑是走上了創作的捷徑,在保證其觀眾具有廣泛性的基礎上,再充分發揮動畫創作的藝術性。
從傳統文學中汲取營養,并不意味著生抄硬搬,而是要辯證地對經典文學進行改編創新,形成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動畫電影。縱觀近年來在票房和口碑皆取得不錯成績的幾部中國動畫電影,無一不是把傳統文學作為創作題材,將故事情節內容進行改革創新之后再制成電影。如《大圣歸來》雖然取材于文學巨作《西游記》,然而不拘泥于原著中孫悟空與唐僧的師徒關系,而是安排了因大鬧天宮被如來佛壓在五行山下過了五百年的孫悟空與年幼時期的唐僧相遇,并且在其相伴之下完成了一段冒險之旅,最終實現了自我救贖,找回了初心。而《大魚海棠》的題材內容則綜合了莊子的《逍遙游》和“上古三大奇書之一”的《山海經》,講述了少女椿為報恩而努力復活人類男孩“鯤”的靈魂,在天神湫的幫助下與彼此糾纏的命運斗爭的故事。《白蛇:緣起》取材于“白蛇傳”民間傳說,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講述的是白素貞在刺殺國師失敗后失憶,與阿宣(許仙的前世)踏上尋找記憶旅程中發生的愛情故事。《哪吒之魔童降世》則取材于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那拏天”,講述了生而為魔的哪吒逆天而行,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吶喊,與命運抗爭到底的勵志故事。
(二)化用傳統音樂
電影配樂在渲染劇情的感情基調、烘托人物心情以及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一種綜合性很強的藝術形式。中華民族傳統音樂以宮、商、角、徵、羽五個音階構成了豐富多彩的特色音樂,其中包括歌曲、戲曲、器樂、歌舞音樂以及說唱音樂五大類,為中國動畫的電影配樂提供了林林總總的音樂資源。
如《大圣歸來》中,制作方特意為每個角色的出場創作了獨一無二的配樂:在動畫的一開始,采用了說評書的形式引出了孫悟空的登場,交代了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的前因后果,讓觀眾仿佛置身于真實的聽評書之中,增添了孫悟空的傳奇色彩。在大鬧天宮一幕,采用的是由名曲《小刀會序曲》 改編而成的電影配樂,通過二胡、嗩吶以及琵琶等器樂的合奏,烘托出孫悟空在大鬧天宮時所向披靡的磅礴氣勢。此外,孫悟空大戰混沌時,混沌低吟淺唱而出的《祭天化顏歌》,其配音來自于國家京劇院的陳旭之,其地道幽怨的京腔,結合混沌酷似京劇姜派小生的打扮,表現出令人回味無窮的古韻,不但凸顯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渲染了決斗的氣氛,推動了故事的發展。
這種傳統音樂的化用在《白蛇:緣起》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通過琵琶、笙簫、古箏等傳統樂器的大量引用,營造出與場景設計珠聯璧合的情感意境,充分延伸了動畫的敘事空間,提升了影片的精神意境,給觀眾留下“余音裊裊,不絕如縷”的無限遐想,充分展現出中華傳統音樂的深厚底蘊,極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藝術含量。
在《大魚海棠》中,制作方在電影配樂中引入傳統音樂的同時,也將傳統樂器以道具的形式呈現出來,男主角“鯤”吹奏的樂器是一種古老的嗚嘟,據史書記載,春秋戰國時期便有了嗚嘟,其音色圓潤悅耳,特別擅長營造幽深靜謐、沉雄古逸的意境,是古代中國傳承下來唯一能吹奏和音的陶類樂器。又例如影片中靈婆給女主角“椿”佩戴的召喚鈴鐺,是一種重要的古老樂器——陶響球,同時也是一種兒童的聲音玩具,其由空心的陶質球形組成,里面裝上沙粒,搖動的時候會發出嘩嘩的聲音。
配樂是電影主題的重要表現形式,其在渲染環境氛圍、推動劇情發展等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別出心裁的有聲動畫不僅滿足了對白的表達以及情節的表現,還能催化電影的主題與動作,因此在創作中國動畫的過程中融入傳統音樂,不但能夠提升動畫題材內容的質量,而且可以有效地幫助動畫制作形成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電影作品。
(三)借用傳統符號
傳統視覺符號指的是從古至今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民通過采取各種手段或方式,逐漸在日常生活勞作中總結出來的關于事物構圖、色彩、內容等方面的規范經驗,如人物符號有三皇五帝、牛郎織女、女媧伏羲、觀音佛祖等,植物符號有松、梅、竹、蘭、菊等,這些視覺符號在形成的那一刻開始,便具備了鮮明的民族特征,以至于后世的人們在看到該視覺符號后,自然而然地將其與背后的象征意義聯系起來,由此可見,傳統符號是一種能夠有效地展現民族文化的形式。
(1)造型與服裝的設計
無論是《大圣歸來》中的孫悟空,還是《白蛇:緣起》中的白素貞,抑或是《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都是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人物符號,而《大魚海棠》在角色的命名上雖然推陳出新,但其中一百多個角色的名字,都能在《詩經》《山海經》《逍遙游》等經典中找到相關的原型,例如男主角“鯤”的名字出自《逍遙游》的“北冥有魚,其名為鯤”,而后續出現的句芒、靈婆、嫘祖、喇嘛鳥等形象,都是根據《山海經》《列仙傳》《搜神記》等書籍的記載進行設計而成。
在服裝設計方面,中國動畫電影也呈現出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服飾符號,增強了人物形象的親和力。例如在《大圣歸來》《白蛇:緣起》《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都出現了肚兜這個服裝的設計,在中國傳統的服飾穿搭理念中,肚兜是一種保護胸部和腹部的貼身內衣,上面多繡上各種各樣的圖案加以裝飾和寄托寓意,例如龍騰鳳翔、鴛鴦戲水、喜鵲登梅等,寄托著中國人民吉祥如意、飛黃騰達的美好愿望。《大圣歸來》中傻丫頭的肚兜上繡的花草圖案,是古代中國兒童常見的肚兜樣式,與傻丫頭的兒童身份十分吻合。《白蛇:緣起》當中小狐妖的肚兜則襯托出其狐媚的本性,《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肚兜繡上了蓮花,讓觀眾不由自主地聯想起《封神演義》中哪吒依托蓮花化身復活的故事,反映出創作團隊在細節上的把控程度。
(2)場景設計與敘事方式
《大魚海棠》的建筑場景,全方位參照了起源于唐朝的福建土樓建筑物,包括圓樓、八角樓等幾十種樣式,和云南的“一顆印”、廣西的“欄桿式”、廣東的“圍龍屋”、北京的“四合院”并稱為中國五大特色傳統民居。作為傳統宗法建筑物的代表,福建土樓體現出客家人團結友愛、互助依存的生活習俗,影片中把女主角“椿”生活的地方設計成福建土樓的模式,暗示了“椿”的祖祖輩輩都生活在一個制度森嚴、環境封閉的空間里,為后來劇情的發展埋下伏筆。
(3)色彩運用與審美觀念
色彩不但是傳統視覺符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動畫電影的主要構成部分,合理得當的色彩搭配不但能產生良好的視覺效果,而且會給觀眾帶來或多或少的心理暗示,黑、白、青、黃、赤乃是中國傳統的五行色彩,每一種色彩都被賦予了深厚的民族底蘊,如在京劇中,黑臉代表性格嚴肅的角色,白臉象征奸詐多疑的角色,紅臉代表忠義耿直的角色等。在上述的幾部中國動畫中,都充分體現了傳統色彩的審美觀念。
例如《大圣歸來》里的混沌以及《白蛇:緣起》中的國師,在色彩運用上都以白色為主,突出兩個反派角色的陰險狡詐,兩部作品中反派形象在色彩設計上的不謀而合,體現出五行色彩所形成的象征性意義已經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形成了約定俗成的審美觀念。《大魚海棠》以“中國紅”的色調為主,象征著喜慶,讓觀眾沉浸于中國式神秘而祥和的氛圍。
二、中國動畫對傳統文化元素的創新運用
這幾年中國動畫在傳統文化元素的創新運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不管是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比過去更加豐富多彩。可以看出,當下的中國動畫電影已逐漸擺脫以往機械搬運傳統文化元素的模式,更加積極主動地借助3D 等特效技術對傳統文化元素進行創新,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動畫電影的發展。
(一)提取傳統文化精髓,改革元素呈現形式
通過對這幾年傳統文化元素在中國動畫作品當中的運用進行深入研究,筆者發現其中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傳統文化重現再造形式的變化。在“中國社會學派”時期誕生的中國動畫,對傳統文化元素的運用可謂是信手拈來,無所不用其極,然而這時期的動畫電影幾乎全是將傳統文化照本宣科般呈現出來,例如1961 年萬籟鳴導演的《大鬧天宮》,無論是人物形象還是故事情節,都是原封不動地照搬原著,只是將書面的文字形式轉化成視覺上的動畫形式而已。到了2015 年之后,中國動畫掀起了一股“改編風”,通過各種創新手法,讓家喻戶曉的傳統文化元素在動畫電影當中歷久彌新,給觀眾帶來面目一新的感覺。
首先是敘事方式設計上的創新。這幾年來國產動畫出現了一種游戲化的敘事趨勢。《哪吒之魔童降世》就采用了游戲模擬與電影場景相結合的制作方式。如開啟寶蓮的機關采用的是密碼與指紋相結合的模式,讓觀眾忍俊不禁。再有哪吒與敖丙兩派在《江山社稷圖》里打斗的場景,制作方通過設計李靖夫婦在圖外觀戰的情景,將圖里面的打斗鏡頭轉換成即時戰略式的游戲地圖,充分展現出游戲與動畫之間的密切聯系。此外,哪吒的成長故事也借用了闖關游戲的模式,從“魔丸”到“兒童”再到“六臂哪吒”的進化,制作方設計了一種游戲關卡的模式,每當哪吒闖關成功一次,就能升級到下一階段。其次是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創新。從2015 年開始,中國動畫逐漸擯棄了以往對傳統文化形象照葫蘆畫瓢的做法,甚至對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形象進行了顛覆性的創新設計。如《哪吒之魔童降世》 一改以往哪吒俊俏魁梧的形象,將哪吒設計成一個沖天鬏、黑眼圈、塌鼻子的兒童,并且走起路來有點駝背,還喜歡將雙手插進褲腰帶。這一系列的設計,給觀眾呈現出一個調皮搗蛋的小孩子形象。而這部動畫中的太乙真人也一改以往仙風道骨、道行高深的形象,被設計成一個體型肥胖的老頑童。
(二)緊跟時代步伐,創新影像表達
通過對這幾年上映的中國動畫電影進行研究可以發現,制作方在汲取傳統文化元素的同時,更加貼合時代潮流和觀眾的審美觀念,做到與時俱進,創新影像表達。
首先是科技元素的引用。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太乙真人在打開寶蓮的過程中采用了密碼和指紋雙重解鎖這種現代化高科技的方式,讓觀眾產生一種時空錯亂感,充滿滑稽。而在《江山社稷圖》里面四人打斗的劇情中,制作方設計的現代化街機背景音樂與水墨山水畫雖然形成了巨大反差,但是卻沒有讓觀眾覺得別扭,反而烘托出滑稽的打斗氣氛。其次是年輕化的語言對白。在傳統文學作品當中,孫悟空和哪吒都代表了一種敢于抗爭專制的精神,然而時過境遷,在當今社會主義消費市場的背景下,如果再歌頌這種反抗專制的精神,很難引起觀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共鳴,因此在這兩部動畫電影中,制作方在保留角色敢于抗爭的精神前提下,賦予了影片更加年輕化的語言對白,哪吒喊出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成了年度熱門的語錄。
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影視創作源源不斷的源泉,中國動畫的發展,必須牢牢把握好傳統文化元素的創新運用,才能推動我國動畫產業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