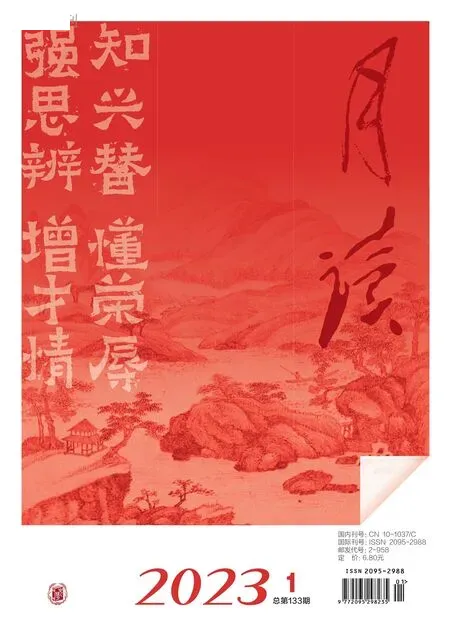雪
魯 迅
暖國的雨,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博識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艷之至了;那是還在隱約著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蠟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蝴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見冬花開在雪野中,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著,也聽得他們嗡嗡地鬧著。
孩子們呵著凍得通紅,象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因為不成功,誰的父親也來幫忙了。羅漢就塑得比孩子們高得多,雖然不過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終于分不清是壺盧還是羅漢,然而很潔白,很明艷,以自身的滋潤相粘結,整個地閃閃地生光。孩子們用龍眼核給他做眼珠,又從誰的母親的脂粉奩中偷得胭脂來涂在嘴唇上。這回確是一個大阿羅漢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紅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還有幾個孩子來訪問他;對了他拍手,點頭,嘻笑。但他終于獨自坐著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后,卻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粘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為屋里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彌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著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賞析】
魯迅的童年是在江南度過的,他寫江南的雪,必然會牽動、會引起他的關于兒時生活情趣、兒時心靈體驗的回憶。不管作者是否有心寓意,江南白雪的形象中分明凝聚著魯迅的童年;而這個童年,又是作者在特定的環境(這里用得著“北方的現實”了)和心境中作出反顧的。正是在色彩繽紛、生氣洋溢的童年和青春時代,魯迅才分外鮮明地感受了周圍世界的這種多彩與生動。
不過,這些只是魯迅的回憶和抒寫中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魯迅也沉重地感到和清醒地懂得:童年和青春雖然美麗多姿,卻也有它軟弱、不定、短暫的一面。和某些輕飄飄地沉湎在兒時回憶里的作家不同,魯迅愛惜童年和青春,但是并非愛不釋手。“曾經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魯迅《亥年殘秋偶作》),魯迅筆下的春溫,永遠是飽嘗秋肅的人心頭的春溫,是被秋肅嚴酷地錘煉過而又堅決地對抗秋肅的春溫。這就給全文定下了一個于深沉、清醒中見美好和純真的調子。
魯迅筆下的“朔方的雪”,摒棄任何溫情,“決不粘連”;它努力振作抖擻,“蓬勃地奮飛”,“燦燦地生光”,決不屈服,決不退出戰斗。它深深地蘊藏著那連自己都可能被它燒盡的熱烈得“如包藏火焰的大霧”,它的前身—活潑潑的雨“死”了,所以,“朔方的雪”再沒用皮毛點綴,只剩下那赤裸裸的“精魂”仍然頑強地、無法再被殺死地存在著,并且仍然光輝奪目,“閃閃地旋轉”,“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正是這朔方的雪,而不是江南的雪的形象,支配著全篇的主要情緒。表面上,這“精魂”沒有江南白雪那樣叫人舒服,其實,它更獨特也更有份量。它是江南白雪的對立面和合乎邏輯的發展,它揚棄了江南白雪的形象,它是受了傷的、蛻變過來的,甚至是曾經“死掉”過的,但仍然沒有污染,仍然不失其純潔的生命(這是江南的雪的形象的核心)的青年和青春。如果說,魯迅筆下的江南白雪的形象,并不算太稀罕;那么,像魯迅那樣去寫朔方的雪,又把這兩種雪聯結在一起寫,就非魯迅這樣的思想家、大手筆而莫辦了。(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