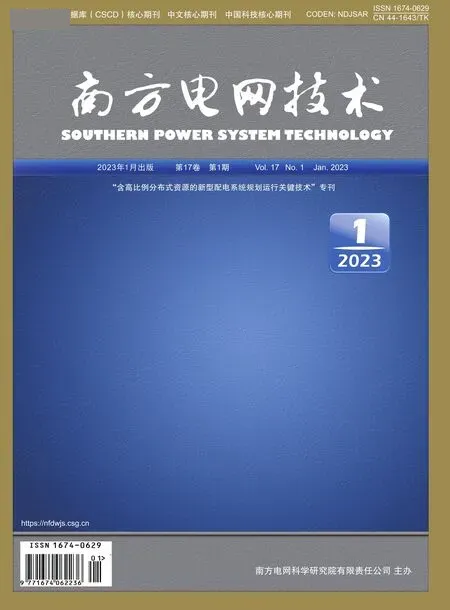基于VSC 的優質光伏資源區配電臺區柔性互聯規劃方法
曹昉,鄭金釗,鄭怡馨
(華北電力大學電氣與電子工程學院,北京 102206)
0 引言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能源結構轉型和清潔能源政策的不斷推出,部分區域低壓配電網中分布式光伏(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generation,DPVG)和以充電樁為首的直流負荷比例不斷上升,使得配電臺區的源、荷特性更加復雜多變。在此背景下,傳統交流配網的臺區鏈式獨立運行方式逐漸顯現出不適應。一方面,配電臺區的分布式電源與負荷水平的運行特性差異較大,部分臺區日內過剩光伏出力需要經變壓器倒送至上級電網,再傳輸至其他臺區消納,給配電系統的安全性和靈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會增加配電網的運行網損[1-5];另一方面,電動汽車充電高峰期與常規負荷高峰期重疊,使得臺區變壓器更容易出現瞬時重載/過載現象,不利于臺區的安全經濟運行[6-7]。
針對上述問題,目前常規解決方法可分為配網升級改造和儲能配置[8-10]兩類。由于低壓配電臺區的DPVG出力倒送和變壓器重載總體呈現出“短時、小功率”特性,為此進行配網規模化一、二次設備升級改造和變壓器容量升級會產生大量額外成本,并且升級后的設備利用率也較低。此外,儲能投資成本較高,多數地區的峰平谷電價尚無法支持儲能成本回收和獲利[11-12],以配電臺區為單位配置儲能的經濟性和可操作性較差。基于此,文獻[13-15]提出了低壓配電臺區柔性互聯概念和方法,旨在借助柔性電力電子器件實現臺區的交直流分區運行,并通過臺區之間的功率交互有效實現DPVG 跨臺區消納和瞬時重載負荷的轉移。其中,基于電力電子變壓器(power electronic transformer,PET)的臺區柔性互聯方法建設成本較高,更適合新建區域配網,而基于換流器的臺區柔性互聯方法建設成本較低,更適合已有配電臺區。
目前,關于臺區柔性互聯的控制方式和優化運行已經有相關研究。在控制技術方面,PET 和換流器可通過端口電壓控制和功率控制策略的組合實現交直流分區的能量協調互動[17-18],其運行穩定性可通過下垂控制、分層控制、主從控制等方式進行控制[19-21];文獻[22-24]著重研究柔性互聯系統的經濟調度策略,分析其在提升臺區運行經濟性和均衡變壓器負載率等方面的作用。而當前關于如何判斷區域配網中臺區的可聯性、確定柔性互聯方案的研究則相對較少。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基于電壓源換流器(voltage source converter,VSC)的臺區柔性互聯模式下DPVG 的消納方式與臺區間的負荷轉供能力,并建立互聯臺區的功率流動數學模型。之后,根據臺區互聯需求提出區域配網的臺區可聯性分析方法,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配電臺區柔性互聯方案及互聯裝置的雙層規劃模型:上層以區域配電網年綜合費用最小為目標,規劃柔性互聯方案以及對應臺區的VSC 容量;下層以包含10 kV 配網運行線損費用在內的從上級電網購電總費用最小為目標,優化互聯臺區的交換功率以及VSC端口的有功功率和無功功率,采用基于模擬退火—錐規劃混合優化算法求解。最后,以40 節點的區域配電網為例進行柔性互聯規劃,分析規劃前后區域配網的運行成本、光伏消納率以及臺區變壓器負載率情況,驗證了本文所提互聯規劃方案的經濟性和有效性。
1 基于VSC的配電臺區柔性互聯系統
1.1 臺區柔性互聯結構及運行模式
現階段,交流配電變壓器不具備PET 的交直流電壓等級轉換、多端口潮流調節功能,無法直接實現功率的跨臺區交流互濟,考慮到臺區內存在的直流負荷需求,借助AC/DC 換流器和聯絡線來實現臺區間的柔性互聯不失為一個較好的解決方案。其中,換流器用于區分臺區內的交、直流負荷,并實現兩個區域間的功率交換;聯絡線則通過直流線路將臨近配電臺區連接起來,實現臺區之間的功率互濟,減小上級變壓器的反向功率。在換流器的選擇上,電壓源型換流器VSC具有低系統成本、雙向功率流動的優勢,能夠實現潮流的四象限瞬時靈活控制,符合臺區柔性互聯的需求,故本文選擇VSC作為臺區柔性互聯裝置。
為提高功率傳輸效率和控制系統的可靠性,實現電能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本文采用圖1 所示的直流母線分段鏈式結構進行臺區互聯。互聯系統中,各配電臺區通過變壓器從10 kV 電網取電,VSC 接在380 V 低壓交流母線上,借助其交直流轉換功能,將原本的全交流臺區劃分出部分直流區域。此模式下,臺區交流負荷仍接入低壓交流母線,而臺區中的直流充電樁、DPVG 和儲能則直接接在VSC的直流側母線上,大幅減少了直流設備接入傳統交流臺區所需的AC/DC 換流器及其帶來的功率損耗,提升了臺區的運行效率。與基于智能軟開關的柔性互聯模式相比,圖1 所示的柔性互聯模式下VSC 獨立運行,功率交互策略更加靈活多變,并且因為在臺區中劃分出了直流區域,更能夠適應大量DPVG 和充電樁等直流源、荷接入低壓配電臺區的趨勢及運行需求。

圖1 基于VSC的臺區柔性互聯模式Fig. 1 VSC based flexible interconnection mode of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
為滿足不同場景下的源、荷接入需求,直流母線電壓采用±375 V。互聯臺區之間通過直流聯絡線相連,配合VSC進行臺區間的功率交換。多臺區互聯運行情景下,一端VSC 采用Q-Vdc控制維持直流母線的電壓穩定,其余端則采用P-Q控制,以便實現臺區內交直流區域的四象限功率交互。
互聯運行模式下,DPVG 由“點消納”擴展成“面消納”,當臺區DPVG 出力大于臺區直流負荷需求時,剩余電量可以通過VSC流入交流區域,由交流負荷進行消納,或是經直流聯絡線傳輸至相連臺區,由該臺區的負荷進行消納,避免了經臺區變的電能倒送,同時提高DPVG 消納率;當某臺區變壓器出現瞬時重載、過載情況時,系統中的其他臺區還可以通過直流聯絡線對其進行功率支援,達到提升配網運行安全性、降低配網運行線損的目的。
1.2 互聯運行臺區的功率流動模型
柔性互聯裝置中的VSC充當著能量轉換器的角色,承擔臺區內以及臺區間的功率交換職責。以圖2 所示的端口功率流通圖為例,t時刻VSC 端口功率需滿足式(1)的平衡約束。

圖2 VSC端口功率流動模型Fig. 2 Port power flow of VSC
式中:PVSCi,ACi(t)、PVSCi,ACo(t)分別為t時刻流入和流出VSC 交流端口的有功功率;PVSCi,DCi(t)、PVSCi,DCo(t)分別為t時刻流入和流出VSC 直流端口的有功功率;KVSC為VSC 的傳輸損耗系數。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功率流動特性,在t時刻PVSCi,ACi(t)和PVSCi,ACo(t)中總有一個為0,對應的PVSCi,DCi(t)、PVSCi,DCo(t)也總有一個為0。此外,VSC 端口還需滿足傳輸容量約束為:
式中:QVSCi,AC(t)為臺區i在t時刻流入VSC 交流端口的無功功率;Si,VSC為臺區i配置的VSC容量。
在上述基礎上,以圖1 所示的互聯臺區為例,運行時各臺區的低壓交、直流分區需滿足以下約束。
1)交流分區功率平衡約束
式中:PLi,T(t)和QLi,T(t)分別為t時刻臺區i變壓器低壓側的有功功率和無功功率;Ploadi,AC(t)、Qloadi,AC(t)分別為t時刻臺區i交流負荷有功功率和無功功率;PT0、PTk、IT0和UTk為分別為臺區i變壓器的空載損耗、額定負載損耗、空載電流百分比和短路電壓百分比;PHi,T(t)和QHi,T(t)分別為t時刻臺區i變壓器高壓側的有功功率和無功功率;βi(t)、Si,T分別為臺區i變壓器低壓側負載率以及變壓器容量。
2)直流分區功率平衡約束
式中:Pi,PV(t)為t時刻臺區i的DPVG 實際出力;Pi,DC(t)為t時刻臺區i的直流負荷;Plineij(t)為t時刻臺區i經聯絡線流向臺區j的功率;π(i)為與臺區i相連的所有臺區的集合。
3)聯絡線功率約束
功率在直流聯絡線上傳輸會產生一定損耗,該損耗與直流母線電壓以及傳輸功率等有關。由于直流母線電壓與互聯運行時臺區VSC選擇的控制方式有很大關聯,規劃過程中難以精確表示,為方便模型求解,本文借助損耗率來表示該傳輸損耗。在此基礎上,相連臺區i和j之間的功率交換滿足以下約束。
式中:Pmaxline為直流聯絡線允許的最大傳輸功率;Kline為傳輸損耗系數。
4)其他運行約束
本文中DPVG 功率因數設為1,即只向系統注入有功功率,其運行約束為:
式中Pmaxi,PV(t)為t時刻臺區i中DPVG最大出力。
臺區柔性互聯后,DPVG 出力盡可能在本臺區以及互聯臺區中消納,避免因變壓器倒送電引發的安全運行等問題。此外,互聯臺區之間能通過功率轉供避免臺區變壓器重載運行。因此,互聯運行時臺區還需滿足以下約束條件。
2 配電臺區可聯性分析
進行柔性互聯規劃之前,有必要對區域配網的臺區進行互聯需分析以及可聯性判斷,從而確定待互聯臺區集合,以降低后續互聯裝置容量及互聯方案的規劃難度。
對于區域配網而言,具備柔性互聯需求的配電臺區包含兩類:1)臺區變壓器在運行過程中出現瞬時重載或者過載,需要通過臺區互聯進行負荷轉供;2)臺區DPVG 接入量與其消納能力不匹配,大發時段光伏出力過剩,需要通過臺區互聯實現DPVG 跨臺區消納。因此,本文提出兩個互聯需求指標,用于判斷臺區的互聯需求并輔助臺區分類,具體如式(9)—(10)所示。
式中:Tloadi和Ppurei分別為臺區變壓器最大凈負載率和臺區最小凈負荷,分別反映臺區i的變壓器負載以及源、荷匹配情況;Ploadi(t)和Qloadi(t)分別為臺區i在t時刻的總負荷有功功率和無功功率;Pmaxi,PV(t)為臺區i分布式光伏在t時刻的最大出力;Si,T為臺區i的變壓器容量。
以上述指標為基礎,區域配網的臺區可聯性分析包含以下步驟。
1)統計各臺區的源、荷特性曲線、變壓器數據以及臺區間距離;
2)計算臺區的Tloadi。Tloadi>0.8說明臺區i存在變壓器重載情況,歸入集合Фf1,否則歸入集合Фt1;
3)計算臺區的Ppurei。Ppurei<0說明臺區i存在光伏出力過剩情況,歸入集合Фf2,否則歸入集合Фt2;
4)分別將Фf1與Фt1、Фf2與Фt2中的臺區進行配對,篩選出滿足臺區聯絡距離約束的可聯組合,構成配網的臺區可聯組合集合Ω。
集合Ω包含了滿足臺區互聯需求以及互聯距離約束的所有臺區可聯組合,后續互聯規劃模型可在此集合的基礎上,用0-1 變量表示各可聯組合中臺區的實際互聯狀態,組合得到的0-1 數組則代表待規劃配網的臺區互聯方案。
3 臺區柔性互聯雙層規劃模型
配電臺區柔性互聯規劃的目的是通過臺區間的功率交互實現DPVG 跨臺區消納以及重載變壓器的負載轉移,進而實現區域配網的優化運行。由于該規劃問題涉及規劃和運行兩個層面,且兩者的優化時間尺度以及決策變量數量級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本文采用分層的思想建立臺區柔性互聯規劃模型。其中,上層模型實現柔性互聯方案及互聯裝置容量的優化規劃,目標函數為配電網年綜合費用最小;下層模型實現柔性互聯配電系統的優化運行,目標函數為配網從上級主網的總購電費用最小。在求解時,上層決策臺區VSC容量以及柔性互聯方案為下層提供優化運行的初始條件,下層則將優化運行得到的包含線損在內的購電費用反饋給上層,作為上層目標函數的一部分參與尋優計算。
3.1 上層模型決策互聯規劃方案
互聯規劃模型從經濟性角度出發,目標函數為整個柔性互聯配電系統的年綜合費用最小,數學表達式為:
式中:CI為柔性互聯裝置的年化投資費用;COM為互聯裝置的年運行維護費用;Cbuy為柔性互聯配電系統從上級主網購電的費用。
1)互聯裝置的年化投資費用
式中:Si,VSC和CVSCI分別為臺區i安裝的VSC 容量及單位容量投資成本;N為區域配網的配電臺區總數;Ω為配網進行可聯性分析后得出的臺區可聯組合集合;xh為0-1變量,表示集合Ω中第h個組合的臺區是否相連,1 表示該組合中的臺區相連,0 表示該組合中的臺區不相連;lh為第h個組合中兩個臺區之間的距離;ClineI為單位長度直流聯絡線路投資安裝成本;yVSC、yline分別為VSC 和直流線路的經濟使用年限;r為貼現率。
2)互聯裝置的年運行維護費用
互聯裝置中直流聯絡線的運行電壓等級低、聯絡距離短,其維護費用基本可以忽略,因此年互聯裝置的年運行維護費用主要為VSC的運行維護費用。
式中CVSCOU為VSC單位容量的年運行維護成本。
3)互聯配電系統從上級主網購電的費用
互聯配電系統從上級主網購電的費用主要包括臺區從主網購電的費用以及配網10 kV線損費用兩類。
式中:CTbuy為全年所有配電臺區從主網購電的費用;Closs為全年配電系統10 kV線損費用。
上層規劃模型的約束條件為臺區VSC的接入容量約束為:
式中Smaxi,VSC為臺區i的VSC最大可安裝容量。
3.2 下層模型實現系統優化運行
下層優化運行模型以上層決策的規劃方案為基礎,通過優化臺區VSC 端口的有功功率及無功功率,進而優化臺區接入10 kV 配網節點的等效凈負荷,在滿足各類約束條件的前提下實現互聯配電系統從上級主網購電的費用最小,考慮到光伏出力和負荷水平的季節性差異,模型中的全年費用由各季節的費用疊加得到。
式中:Ds為季節s包含的天數;N為配網包含的配電臺區總數;T為運行周期;Nbus為配網包含的10 kV 節點總數;c(t)為t時刻電價;Pi(t)為t時刻注入節點i的有功功率。
除互聯臺區運行約束式(1)—(8)外,下層優化模型還需考慮配電網運行相關約束。其中,配網潮流約束、節點電壓約束如式(17)—(19)所示。
式中:Ui(t)、Uj(t)和θij分別為t時刻節點i、j的電壓幅值和相角差;Qi(t)為t時刻注入節點i的無功功率;δ(i)為與節點i相連的節點集合;Gij、Bij、Gii、Bii分別為節點i、j的互電導、互電納、自電導和自電納;Umaxi和Umini分別為節點i電壓幅值的上下限。對于柔性互聯配電系統中的非上級主網聯絡節點,存在:
3.3 規劃模型求解
本文基于交互迭代嵌套思想,綜合考慮上下層模型的變量類型以及優化需求,采用基于模擬退火和錐規劃的混合優化算法進行規劃模型求解[25]。其中,模擬退火算法作為規劃模型的整體優化框架,用于尋求配網的最優臺區互聯方案以及互聯裝置容量;錐規劃算法嵌入模擬退火算法的目標函數求解環節中,用于求解系統在給定規劃方案下規劃期內的最優運行方式,并輔助模擬退火算法計算單次迭代過程中的目標函數值。
由于下層模型包含關于節點電壓幅值和相角差的非線性函數,不滿足錐規劃算法對線性目標函數和可行域的嚴格要求,因此使用錐規劃算法前需要對部分約束進行線性化處理[26-27]。
在t時刻,通過式(21)引入變量Xi(t)、Yij(t)、Zij(t),用于替代原模型中的Ui(t)、Uj(t)和θij(t),將包含電壓和相角的非線性約束式(17)—(19)轉化為線性約束。
之后,將互聯模式下臺區變壓器以及VSC的非線性運行約束式(2)、式(8)轉換為旋轉錐約束。
針對含有絕對值項|Plineij(t)|的式(5)引入輔助變量Mlineij(t)進行線性化。
此外,為使優化模型在凸錐的約束范圍內,引入非線性二階旋轉錐約束條件對式(21)引入的變量進行約束[28],如式(27)所示。
經過錐轉化,式(1)—(8)、式(20)、式(21)—(27)構成下層配電網優化運行的優化模型。
以單次迭代過程為例,上層規劃模型以臺區互聯方案和互聯臺區VSC容量為決策變量,利用模擬退火算法生成符合約束條件的規劃方案。下層規劃模型則在該規劃方案基礎上,利用錐規劃算法求解最優運行方式并將優化結果返回給上層,用于模擬退火算法當前目標函數值的計算。之后,對模型和結果進行收斂性分析,決定是否進入下一次迭代。具體的算法流程如圖3所示。

圖3 規劃模型求解流程圖Fig. 3 Solution flowchart of planning model
4 算例分析
4.1 算例基礎數據
算例采用的10 kV 配電網結構如圖4 所示,圖中節點1 為與上級電網的聯絡節點,其余節點為臺區變壓器高壓側的接入節點,各支路參數見附錄表A1。考慮負荷水平和光伏出力的季節性差異,算例中的臺區負荷采用季節性時序負荷曲線,具體做法為:將配電網中所有節點(臺區)負荷劃分成5 種類型,各節點(臺區)的交、直流負荷、DPVG 容量、所屬負荷類型見附錄表A2;臺區變壓器容量見附錄表A3;不同季節各類負荷的時序特性曲線和光伏出力曲線見附錄圖A1—A7。求解時,不同時刻臺區的實際負荷由臺區交、直流最大負荷乘以負荷率后疊加而成。

圖4 10 kV配電網結構圖Fig. 4 Structure diagram of 10 kV distribution network

表A1 10 kV配電網線路阻抗Tab. A1 10 kV distribution network line impedance

表A2 配電臺區分布式光伏、負荷相關參數Tab. A2 DPVG and load related parameters of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s

表A3 配電臺區變壓器容量Tab. A3 Transformer capacity of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

圖A1 負荷類型1的時序特性曲線Fig. A1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load type 1

圖A2 負荷類型1的時序特性曲線Fig. A2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load type 2

圖A3 負荷類型3的時序特性曲線Fig. A3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load type 3

圖A4 負荷類型4的時序特性曲線Fig. A4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load type 4

圖A5 負荷類型5的時序特性曲線Fig. A5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load type 5

圖A6 直流負荷時序特性曲線Fig. A6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DC load

圖A7 光伏出力時序特性曲線Fig. A7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DPVG
VSC 和聯絡線的投資安裝及運維費用、分時電價、經濟使用年限等成本參數見附錄表A4—A5。配電系統額定電壓UN=10 kV,電壓允許波動范圍為0.95UN~1.05UN, 功 率 基 準 值SB=100 MVA,VSC 功率損耗系數和直流功率傳輸損耗率取0.02,交流負荷功率因數取0.9,變壓器重載率設為0.8。

表A4 成本參數Tab. A4 Cost parameters

表A5 分時電價Tab. A5 TOU electricity price
4.2 算例結果分析
4.2.1 配網可聯性分析及互聯規劃結果
對區域配網的所有臺區進行不同季節下的需求指標計算,得出具有柔性互聯需求的臺區如表1所示。

表1 配電臺區互聯需求Tab. 1 Interconnection demand of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s
之后,將其與符合互聯距離范圍的臺區進行匹配,得到區域配網的臺區可互聯組合集合Ω={(3,4)、(4,5)、(4,19)、(5,6)、(7,8)、(8,9)、(8,22)、(12,13)、(13,31)、(17,18)、(18,33)、(7,22)、(21,22)、(24,25)、(25,26)、(27,28)、(28,29)、(9,28)、(36,37)、(37,38)、(37,39)、(36,39)、(39,40)}。在此基礎上,采用本文所提規劃模型對區域配網進行柔性互聯規劃,得到臺區柔性互聯方案及互聯臺區的VSC 容量配置如圖5、表2所示。

表2 臺區VSC容量配置Tab. 2 Installation capacity of VSC in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s

圖5 臺區互聯方案Fig. 5 Interconnection scheme of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s
4.2.2 系統成本及臺區運行效率
表3 為互聯規劃前后區域配網的年綜合成本及其構成。從表3 看出,柔性互聯配電系統的年綜合成本相較于規劃前減少了23.54 萬元,其中10 kV網損費用減少了6.09 萬元,降低了29.43%,說明臺區柔性互聯能夠有效提高整個區域配網運行的經濟性。除此之外,臺區互聯運行實現了分布式光伏的跨臺區消納以及瞬時重載變壓器的負載轉移,既避免了配電系統因臺區功率倒送需求而產生的一次、二次設備改造費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臺區變壓器的容量升級改造。

表3 配電系統年綜合成本Tab. 3 Annual comprehensive cost of distribution system萬元
針對表1 所示的各種互聯需求類型,分別選擇代表性互聯臺區進行互聯運行分析。
根據規劃所得互聯方案,在互聯距離范圍內,單獨存在DPVG 出力過剩問題的臺區更傾向于和單獨存在變壓器重載問題的臺區互聯,如臺區4 和臺區5、臺區13 和臺區31、臺區37 和臺區39。此種組合下光伏跨區消納與臺區負荷轉供共用一條直流聯絡通道,既能提升臺區柔性互聯裝置的利用率,同時降低了裝置的投資及運維費用。以互聯臺區4、5 為例,不同季節下臺區間的日內交換功率以及重載臺區變壓器的負載率情況如圖6所示。

圖6 不同季節臺區4、5的交換功率以及變壓器負載率Fig. 6 Exchange powers and transformer loads rates of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 4 and 5 in different seasons
不同季節下,光伏大發時段臺區5 光伏出力均過剩,為避免棄光或者電力倒送現象,臺區5 經聯絡線將光伏出力余量傳輸至臺區4 消納;在午高峰或晚高峰時段,常規負荷與充電樁負荷疊加,臺區4 變壓器出現不同程度的重載甚至過載現象,臺區5 繼續通過聯絡線對臺區4 進行負荷功率支撐,配合VSC 的無功補償能力,將臺區4 的變壓器最大負載率控制在0.8及以下。
此外,由于不同季節光伏出力和負荷水平不同,臺區間的功率交換也存在季節性差異。其中,春、秋兩季光資源較好,臺區光伏出力水平高且負荷水平低,故日內臺區5 向臺區4 傳輸的光伏出力余量較多,而晚高峰時段對臺區4 的負荷功率支撐較少;受高溫對光伏組件的影響,夏季光伏出力不及春、秋兩季,并且負荷水平處于高位,故日內臺區5 向臺區4 傳輸的光伏出力余量相較于春、秋季有所下降,但在午高峰和晚高峰時段對臺區4 的負荷功率支撐大幅上升;冬季光伏出力最低且負荷水平偏高,故臺區5 向臺區4 傳輸的光伏出力余量最少,而其在晚高峰時段對臺區4 的負荷功率支撐水平處于春秋季和夏季之間。
對于僅存在光伏過剩問題的臺區28 和臺區18,由于在互聯距離范圍內沒有僅存在變壓器重載的問題的臺區與之匹配,優化規劃后分別與正常運行的臺區29 和臺區31 互聯。互聯臺區間的功率交換以消納過剩光伏功率為目的,交換量也隨著臺區負荷和光伏出力的季節性波動而變化,呈現春秋多,夏季次之,冬季最少的特點。
對于同時存在光伏出力過剩和變壓器重載問題的臺區,以互聯臺區7、8 和22 為代表進行分析。不同季節下臺區間的日內交換功率以及變壓器負載率如圖7所示。

圖7 不同季節臺區7、8、22的交換功率及變壓器負載率Fig. 7 Exchange powers and transformer load rates of distribution station area 7, 8 and 22 in different seasons
不同季節下,光伏大發時段臺區8 光伏出力均過剩,光伏發電余量經聯絡線傳輸至臺區7,并通過臺區7和22的聯絡線一部分傳輸至臺區22,由臺區7和臺區22共同消納,不僅起到縮小互聯臺區變壓器負載差異的效果,同時能夠解決夏季臺區22變壓器在午高峰時段的重載運行問題,如圖7(b)所示。而在負荷晚高峰時段,常規負荷與充電樁負荷疊加,各季節下臺區8和臺區22的變壓器均出現不同程度的重載或過載現象,此時臺區7 經由直流聯絡線分別對臺區8 和臺區22 進行功率支撐,加上VSC 的無功補償作用,將兩個臺區的變壓器最大負載率控制在0.8 及以下。同時,臺區間的功率交換也存在季節性差異:春、秋兩季臺區8 向臺區7 傳輸的光伏發電量最大,夏季次之,冬季最少;而臺區7 對臺區8 和臺區22 的負荷功率支撐在夏季最多,冬季次之,春、秋季最少。
總體來說,規劃前存在瞬時重載/過載的臺區配電變壓器負載率在柔性互聯后均降至0.8 及以下,并且在不允許臺區倒送電的前提下,互聯規劃后區域配電網全年的DPVG 消納率從94.09%提升至99.98%,說明臺區柔性互聯規劃能夠有效提升配電系統對分布式光伏的接納能力,并保障臺區變壓器的安全運行。
5 結論
本文針對主動配電網中臺區源、荷特性差異引起的DPVG消納以及臺區變壓器重載/過載問題,提出了區域配網的臺區可聯性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基于VSC的配電臺區柔性互聯雙層規劃模型。模型采用基于模擬退火和錐規劃的混合優化算法求解,并在40節點的配電系統上進行驗證,結果表明:
1)基于VSC的柔性互聯裝置具有功率空間轉移能力,通過對臺區VSC端口和聯絡線的功率協調控制,能夠有效實現DPVG 的跨臺區消納和臺區間功率互濟。
2)本文所提柔性互聯規劃方法基于配電臺區的實際互聯需求,通過規劃能夠有效提升區域配網的DPVG 消納率和運行經濟性,同時保證互聯系統配電臺區的安全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