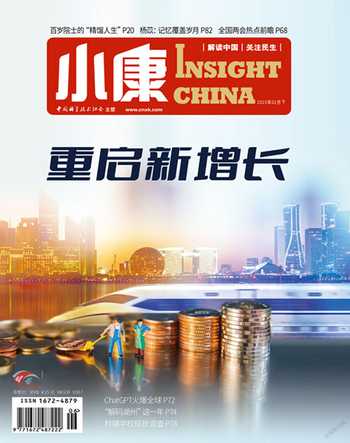中國科幻,中國價值
彭超
在面對全球危機時,如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開太平”?根植于中華文化的《流浪地球2》給出了中國的回答,“我在,我一直都在”。
時隔四年,《流浪地球2》在2023年春節(jié)檔上映,并成功引起觀影熱潮。不少觀眾在走出電影院的時候,都不禁感嘆道“只有中國才能拍出這種科幻片”。這并非是說技術(shù),而是指向影片所體現(xiàn)出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價值。何出此言?在看慣了好萊塢大片之后,我們驚喜地發(fā)現(xiàn),在面對未來生存危機時,中國給出了不同的回答。
《流浪地球2》的敘事大致可以分為三條線索,分別為李雪健飾演的周喆直作為聯(lián)合政府中國代表據(jù)理力爭堅持“移山計劃”(后更名為“流浪地球計劃”)、吳京飾演的劉培強被選拔成為領(lǐng)航員國際空間站航天員并在危難關(guān)頭挺身而出、劉德華飾演的圖恒宇在履行工程師職責(zé)時還希望在數(shù)字生命世界給因意外去世的女兒完整的生命。這三條線索最終匯集到一起,給出了中國的回答,“我在,我一直都在”。
影片呈現(xiàn)出中國負責(zé)任的大國擔(dān)當(dāng)形象。身穿中山裝出場的周先生是聯(lián)合政府中國代表,他目光堅毅、神態(tài)沉穩(wěn),在太空電梯遭遇襲擊、月球發(fā)動機瀕臨破產(chǎn)、聯(lián)合政府亂了陣腳的時候,是他委任中國科學(xué)家,扛下了建設(shè)月球發(fā)動機的重任。當(dāng)他的同事質(zhì)疑聯(lián)合政府處置不公時,“這公平嗎?”他給出的回答是“危難當(dāng)前,唯有責(zé)任”,擲地有聲!責(zé)任是使命的召喚,也是能力的體現(xiàn),在關(guān)鍵時刻,是中國勇挑重擔(dān),攻堅克難,成功地完成了任務(wù)。在面對分歧意見時,他以“人類股骨”為例發(fā)表演講,引導(dǎo)人類團結(jié)起來,擰成一股繩,共同面對人類所面對的生存危機。影片傳遞出重要信息,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也有足夠的智慧,在國際事務(wù)中承擔(dān)組織者和協(xié)調(diào)者角色。
“情感”是《流浪地球2》著力探討的話題。為此,影片給了劉培強更為完整的成長線,演繹了一位普通人在面臨危機時,是如何竭盡全力保護身邊摯愛之人。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對家庭成員的關(guān)愛成為行動的動力,他對身患癌癥妻子的深情、對幼子的不舍,也形塑了人物豐富而細膩的內(nèi)心世界。然而,電影沒有止步于此,而是將這種情感進一步擴大到人與人之間、人與地球之間。劉慈欣在第73屆雨果獎獲獎感言中曾說,“看到整個人類將力量聚合在一起,這是只有在科幻小說中才能見到的景象”。現(xiàn)在,影片告訴我們,是樸素而真摯的情感構(gòu)成了人類聚合的動力。為什么中國科幻非要帶著地球“流浪”?對親人的呵護、對家園的依戀,這種仁愛構(gòu)成了我們中國人生命的底色。
“數(shù)字生命計劃”是影片中另外一種解決地球危機的方案,利用的是意識上傳技術(shù),這種技術(shù)可以把人類的意識上傳到計算設(shè)備,計算設(shè)備能夠模擬大腦的運作,對外界輸入做出相應(yīng)的反應(yīng),甚至具備自主意識。在科幻作品中,意識上傳被視為重要的生命延續(xù)技術(shù),讓人類獲得永生,使人類能夠在全球災(zāi)變、星際旅行等極端情況下存活下來。雖然在影片中這項計劃被叫停,但在最后關(guān)鍵時刻,恰恰是進入數(shù)字生命世界的圖恒宇在女兒的超強計算能力協(xié)助下,輸入密碼圓滿完成組織交給他的任務(wù)。這也讓人類重新思考身體與意識、虛擬與現(xiàn)實、技術(shù)與倫理的關(guān)系。在影片片尾曲中,劉歡深情演唱“我在,我一直都在,哪怕遁入永遠的虛幻”。即便進入“虛幻”,中國人也一定牢記使命,一定行。
北宋大家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在面對全球危機時,如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開太平”?根植于中華文化的《流浪地球2》給出了中國的回答,“我在,我一直都在”。
(作者系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有限公司與清華大學(xué)聯(lián)合培養(yǎng)博士后,北京元宇科幻未來技術(shù)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科普作家協(xié)會科幻創(chuàng)作研究基地委員,中國石油大學(xué)(北京)文體學(xué)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