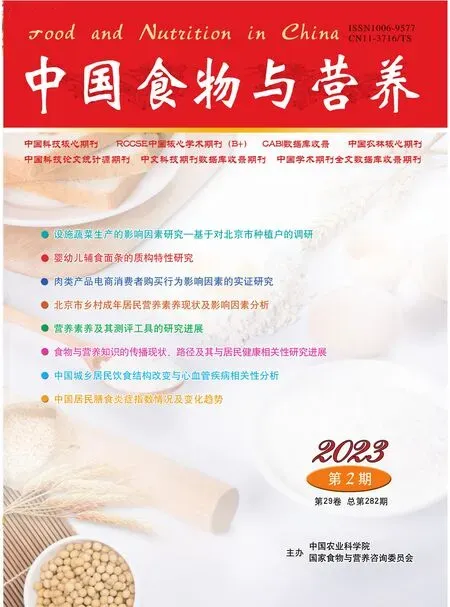設施蔬菜生產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對北京市種植戶的調研
張 龍,穆月英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
1 設施蔬菜生產的要素投入
本研究分別從勞動力投入、土地投入和資本投入3個方面分析北京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要素投入(附表)。

附表 農戶要素投入情況
1.1 設施蔬菜生產的勞動力投入
家庭是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蔬菜生產作為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方式,家庭的特征直接影響著生產中勞動力的供給狀況。農戶在設施蔬菜生產中,夫妻搭檔種菜、家庭同時照顧老人和孩子的情況較為普遍。農戶戶均人口數為3.5人,89.94%的農戶家庭人口為2~6個;農戶每個家庭平均勞動力人口為2.44,60.26%的農戶家庭勞動力人數為2個,其中從事蔬菜生產的勞動力個數平均為1.83個,71.15%的農戶家庭從事蔬菜生產的勞動力人數為2個。可以看出,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趨勢下,蔬菜生產勞動力供給存在不足。另外,從收入結構來看,家庭收入中農業收入占比平均為76.61%,農業收入中又以蔬菜收入為主,平均占比95.01%。同時,年內有外出打工經歷的戶數占39.74%,較2016年有大幅上升,打工地點主要集中在本縣區范圍內,因此可以看出農戶兼業程度開始提高,家庭收入對蔬菜生產依賴度逐步衰減。
分別從性別、年齡、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分析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人力資本投入情況。從性別來看,男性占全部農戶的77.56%,表明目前農戶設施蔬菜生產中,主要決策者為男性。從年齡來看,戶主平均年齡為57歲左右,比2016年提高了3歲,農戶設施蔬菜生產中缺少青壯年勞動力的加入。其中,85.26%的農戶年齡處于50~60歲,表明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勞動力老齡化傾向顯著。從戶主自評的健康狀況來看,81.41%的農戶認為其自身健康狀況較好,表明農戶設施蔬菜生產勞動力供給預期相對穩定。從受教育程度來看,以初中為主,76.28%的農戶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上,表明農戶受教育程度較高。生產經驗是設施蔬菜生產中人力資本投入不可測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戶蔬菜生產平均年數為19.67年,從事設施蔬菜生產的平均年數為15.49年,說明農戶在設施蔬菜生產中投入的勞動力雖然呈現一定的老齡化趨勢,但大多數農戶長期從事設施蔬菜生產,從而積累了豐富的設施蔬菜種植經驗,對設施內溫度濕度的控制以及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的經驗可能彌補生產中勞動力不足的缺陷。但不可避免的是,部分“經驗主義”的農戶同樣存在不合理的生產行為,如過量施肥、施藥以及對相關生產設備不正確的操作等,因此必須持續加強農民培訓,使其自身經營與現代化的、科學合理的生產行為模式相結合,綜合提高其設施蔬菜生產能力[3]。
1.2 設施蔬菜生產的土地投入
種植規模與農戶專業化程度乃至農戶蔬菜生產平均成本息息相關。從設施蔬菜種植規模來看,農戶平均家庭種植面積為0.36 hm2。從具體分布來看,有38.46%的農戶種植面積在0.3 hm2以下,這一經營規模下,農戶通常擁有2~3個大棚或溫室,這部分農戶蔬菜生產勞動力投入一般以家庭勞動力為主,且兼業化程度較低,屬于典型的傳統小規模蔬菜生產農戶。有53.85%的農戶種植面積在0.3~0.7 hm2,種植面積在0.7 hm2以上的農戶僅占8.98%。可以看出,設施蔬菜生產仍以小農戶為主,規模化程度較低。
土地的細碎化程度也會關系到設施蔬菜生產的勞動力以及其他要素的投入,從而直接影響生產成本。土地細碎化程度越高,農戶在不同地塊間的往返耗費精力越多,在經營和土地管理等問題上將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因此農戶往往選擇減少外出務工、雇傭勞動力等,甚至降低設施蔬菜生產經營標準,不利于蔬菜質量安全。農戶所經營土地的平均地塊數為2.08塊。有71.15%的農戶所經營的土地分布在1處,有16.67%的農戶所經營的土地分布在2處,僅有12.18%的農戶所經營的土地分布在3處或3處以上。這表明設施蔬菜種植的土地細碎化程度較低,土地較為集中,為設施蔬菜生產的適度規模經營奠定了良好基礎。
除此之外,農戶到田間的距離也可能關系到生產成本。部分農戶所經營土地的田間設施建設不健全,存在水電不匹配等問題,甚至需要農戶自行接電至田間以供設施蔬菜生產,如果農戶到田間距離較遠,則其生產經營也可能存在諸多不便。有55.77%的農戶在10 min以內即可步行至農田,有36.54%的農戶在10~20 min之間可步行至農田,還有7.69%的農戶則需要20 min以上。這說明大多數農戶的住宅距離農田較近,設施蔬菜生產和田間管理較為便利。
1.3 設施蔬菜生產的資本投入
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基礎,設施蔬菜生產的綜合能力提升、機械化水平提升和科技支撐水平提升均離不開資本投入。農戶中有49.36%的農戶擁有小旋耕機,說明設施蔬菜生產中,租賃機械進行耕地較為普遍,這與其較小的生產規模具有密切聯系;有37.82%的農戶擁有卷簾機,表明保溫被升降時仍采用人力,機械化水平較低;有91.67%的農戶擁有運輸工具,這不僅反應了農戶生產經營能力的提升,也體現出當今農村道路建設的完善,為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的流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與其他產業相比,設施蔬菜生產周期長、風險高和農戶抗風險能力弱等因素共同導致了農村金融市場發展欠缺。小農戶自身信用度低,沒有固定資產作為抵押,想進行農業投資的資金局限性大。雖然近些年來我國的普惠金融不斷發展,金融機構不斷進入農業領域,但是金融機構更傾向于和涉農企業合作,小農戶很難獲得金融機構的支持。有23.72%的農戶具有貸款需求,但僅有8.33%的農戶實際得到了貸款。在沒有抵押的情況下,小農戶難以獲得金融機構的貸款,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有農業生產投資和創新需求的小農戶難以實現生產經營能力的提升[4]。
分布在研究區東北部,分割為5塊,面積648.01 km2。以臺狀和趾狀淺丘為主,具有圓丘、塔狀丘、脊狀丘等多種形態,丘頂圓緩常呈條帶形或串珠狀,溝谷開闊、平緩或者以殘丘零星點綴,形若平原。海拔在350~442 m之間,平均海拔383 m,相對高差30~50 m,谷寬大于100 m,以緩丘谷帶小壩地貌相結合。
2 設施蔬菜生產的技術需求和采用
2.1 設施蔬菜生產的技術需求
在設施蔬菜生產過程中,農戶對技術的采用決定于供求兩方面,其中供給來自于技術的提供者,而需求則來自農戶對于技術的需要程度,是農戶尋求新技術的動機[5]。有69.23%的農戶具有這樣的動機,盡管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而難以實現,但農戶自身具有對新技術的需求。設施蔬菜生產技術十分多樣,因此農戶對不同生產技術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優先技術需求比例代表農戶選擇該技術作為最需求的技術的比例,而總技術需求比例代表農戶在所選擇技術組合中包含該項技術的比例。從優先技術需求比例來看農戶最需求的技術是優良的種子和優質的菜苗,占全部農戶的44.44%,這反映出農戶對種苗的重視程度。農戶第二需求的是病蟲害防治,占到全部農戶的40.74%,他們認為病蟲害防治是當前最需要的技術。其余技術的優先需求比例均不足10%。從總技術需求比例來看,選擇病蟲害防治技術的農戶最多,占全部農戶的63.89%,其次是優良種子和優質菜苗,占48.15%。農戶對施肥指導和節水灌溉技術的需求次之,分別占全部農戶的17.59%和12.04%,說明雖然施肥指導和節水灌溉技術并不是當前農戶最為迫切需求的技術,但仍然受到了農戶的重視。農戶對設施溫度控制技術和設施采摘及機械運輸等技術同樣具有一定需求,但需求比例相對較低,分別占全部農戶的8.33%和9.26%。在農戶決定是否采用新技術時,技術采用的風險是農戶首先要考慮的一方面,但由于農業生產周期較長,在采用技術時往往難以判斷技術采用的效益能否超過其成本,由于這一過程的未知性,農戶的風險態度往往直接決定了其是否采用技術[6]。農戶中有33.97%的農戶屬于風險偏好型,即為了較高的收益而嘗試具有一定風險的新技術。排在第二的農戶屬于風險中性,占農戶總數的29.87%,這部分農戶認為只要有人使用過該技術,則自己也可嘗試。風險厭惡型農戶占總農戶的21.15%,這部分農戶認為技術的采用以穩妥為主,不愿意過多承擔風險。
2.2 設施蔬菜生產的技術采用
設施蔬菜生產屬于技術密集型生產方式,農戶技術的采用與其蔬菜種植的效率具有直接的聯系,也是造成農戶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技術采用效果可以將蔬菜生產技術劃分為3類:增產增效型技術、質量安全型技術以及環境保護型技術。如圖1所示,在增產增效型技術中,地膜覆蓋和穴盤育苗2項技術的采用率最高,分別達到了91.03%和75.00%。其次是土壤消毒、遮陽網和雄蜂授粉,3項技術的采用率均在40%左右。再次是深耕保墑和植物生長調節劑,采用率接近20%。在質量安全型技術中心,高溫悶棚的采用率最高,超過了60%;其次是防蟲板和防蟲網,采用率均介于50%~60%,這可能與各區縣政府對蔬菜生產的物化補貼有關。同時,分別有48.08%和44.23%的農戶采用了生物菌肥和生物農藥,由此可見,相較2016年,農戶對蔬菜質量安全意識有了顯著提升。在環境保護型技術中,采用率最高的是節水灌溉技術,采用率為50.00%,其次是渠道防滲(軟管引水),采用率為36.54%,再次是測土配方施肥,采用率不足20%,這可能與農戶得不到有效反饋信息有關。秸稈(生物有機質)還田和秸稈生物反應堆采用率分別為6.41%和4.49%,這可能是由于技術難度或技術實施條件等問題造成的。

圖1 農戶技術采用情況
3 設施蔬菜生產的成本收益
農戶的經營管理能力、生產決策和技術采用最終都以設施蔬菜生產中的實際投入成本和獲得收益的形式表達出來。成本收益不僅是農戶作為理性決策單元所追求的最終目標,同時也關系到生產是否能夠經濟可持續。結合設施蔬菜生產的各個環節可以將其成本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包括種苗費、機耕費、肥料費、設施使用和維修費、地膜費、棚膜費、農藥費、水電費、雇工費、銷售費、地租。利潤和成本之比及成本利潤率可以反映設施蔬菜生產的經濟效益,該比例越高說明蔬菜生產的經濟效益越好。
如圖2所示,從總成本來看,4種蔬菜中青椒生產成本最高,達到9 677.42元,番茄、黃瓜和茄子的生產成本較為接近,分別為6 312.46、5 833.48、5 876.11元。從成本構成來看,青椒生產成本中雇工費和種苗費是4種蔬菜中最高的,分別占其總成本的25.52%和15.96%,其次是肥料費,占總成本的15.77%,設施使用和維修費與農藥費相近,分別占總成本的8.49%和8.27%,其余費用均不足總成本的1%;番茄生產成本結構較為均衡,占總成本最高的是肥料費,達到25.50%,其次是雇工費和種苗費,分別占總成本的14.88%和13.48%,再次棚膜費、設施使用和維修費,分別占總成本的10.88%和10.02%,其棚膜費處于4種蔬菜中最高水平;黃瓜的生產成本構成與番茄較為相似;茄子的生產成本構成中,肥料費占比最高,達到42.77%,也是4類蔬菜中的最高水平,其次是農藥費,占總成本的17.3%,再次是雇工費,占總成本的13.56%,其他成本相對較少,均在總成本的10%以下。從經濟效益來看,番茄和黃瓜經濟效益最好,其成本利潤率遠高于其他兩類蔬菜,分別為1.58和1.62;其次是茄子,成本利潤率為0.54;最后是青椒,成本利潤率僅為0.26。因此,從不同種類蔬菜來看,番茄和黃瓜生產更具優勢,青椒的相對經濟效益最低。

圖2 設施投入結構與經濟效益
4 設施蔬菜生產投入產出的綜合效率
成本收益從成本經濟核算的角度分析了蔬菜生產的經濟可持續性。但在實際生產中,一些要素的投入換算成統一的資本投入難以體現要素投入之間的互補或互斥性。因此,對設施蔬菜生產技術效率的分析更能夠在體現要素投入之間關系的基礎上對農戶蔬菜生產經營的情況加以描述。在對技術效率進行測算時,按照要素投入的不同性質,同時考慮到設施等費用中存在大量補貼的情況,最終將投入要素選定為土地、種苗費、肥料費、病蟲害防治費、農膜費、雇工費,產出要素則選擇產值和產量2個變量,分別代表蔬菜生產過程中產量和經濟效益生產目標。
利用DEAP 2.1軟件對技術效率進行測算,得到農戶的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其中純技術效率代表農戶蔬菜生產經營管理和技術水平,規模效率代表農戶生產規模是否達到最優規模,而技術效率是前兩者之積,代表了農戶的綜合生產效率水平,也就是在既定生產條件下的最大化產出能力。3類效率是處于0~1之間的值,越接近1則效率水平越高。根據測算結果,農戶平均技術效率為0.437,平均純技術效率為0.930,平均規模效率為0.470。這表明,總體來看,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效率水平偏低,而效率的損失主要來自規模效率,即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整體經營規模距離適度規模尚有距離。同時,平均純技術效率接近于1,說明農戶在設施蔬菜生產中具有較高的經營管理和技術水平。
對規模報酬階段的測算也印證了規模效率較低的結果。農戶中處于規模報酬不變階段的占8%,表明這部分農戶的設施蔬菜生產規模已滿足最優生產規模水平。大多數農戶(91%)都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的階段,代表這部分農戶仍需要通過擴大設施蔬菜生產規模,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還有1%的農戶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這部分農戶在設施蔬菜生產中存在投入規模過大的問題,從而造成了邊際效應遞減。
分品種來看,如圖3所示,青椒的技術效率相對較高,達到0.76,番茄、黃瓜、茄子較為接近,分別為0.58、0.59、0.59。從技術效率的分解來看,純技術效率方面,番茄和黃瓜最高,其中番茄為0.98,黃瓜則達到了1,青椒和茄子次之,分別為0.94和0.96,這表明4類蔬菜中生產管理技術和經營水平普遍較高,其中黃瓜最高,番茄次之,茄子和青椒相對較低。從規模效率來看,青椒規模效率最高,為0.81,表明所調查青椒生產農戶的生產規模多數達到相對適度的經營規模,其次是茄子,為0.61,番茄和黃瓜略低,分別為0.59和0.58,這表明農戶在設施蔬菜生產中,番茄和黃瓜的生產規模仍有待改善。

圖3 不同品種蔬菜生產效率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第一,從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要素投入來看,勞動力投入中缺乏青壯年以及高學歷勞動力,但生產經驗較為豐富;種植規模普遍較小,土地分布較為集中,土地細碎化程度較低,且農戶距離農田普遍較近;在農機具等資產方面擁有率較低,運輸工具擁有率較高。
第二,從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技術需求和采用來看,有較多農戶屬于風險偏好型,對新技術的需求較高,從優先技術需求比例來看,農戶最需求的技術是優良的種子和優質的菜苗,病蟲害防治技術次之。地膜覆蓋、穴盤育苗、高溫悶棚、生物菌肥、生物農藥和節水灌溉等技術采用率均較高。
第三,從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成本收益來看,生產成本主要包括種苗費、機耕費、肥料費、設施使用和維修費、地膜費、棚膜費、農藥費、水電費、雇工費、銷售費、地租,在各項成本中構成比例最大的為肥料費,其次是雇工費。從品種來看,青椒生產成本最高,而番茄和黃瓜經濟效益最好,生產番茄和黃瓜更具優勢。
第四,從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綜合效率來看,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綜合效率水平偏低,主要來自規模效率的損失,即農戶的設施蔬菜生產經營規模距離適度規模尚有距離。從品種來看,青椒的技術效率最高,番茄和黃瓜的純技術效率最高,而規模效率較低,因此推動番茄和黃瓜的適度規模經營更有利于其優勢的發揮。
5.2 對策建議
第一,持續加大農民培訓力度,綜合提升農戶設施蔬菜生產能力。勞動力老齡化已成為蔬菜產業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之一,因此,應該堅持不斷加強農民培訓,包括農機培訓、技術培訓等,使農戶蔬菜生產的經驗優勢充分發揮,全面提升農戶設施蔬菜生產能力[7]。
第二,不斷強化質量安全意識,切實提高蔬菜質量安全水平。一方面,要加強農產品質量監管,加強產地和銷地的協調配合,完善聯防聯控和準入準出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廣蔬菜優良品種、集約化育苗、頻振式殺蟲燈、性誘劑等生態栽培技術,使農戶設施蔬菜生產逐步轉向綠色生產方式。
第三,科學引導要素投入,避免生產資料浪費或過度使用。規范肥料、農藥等要素的利用方式,提高各類生產資料的利用效率,逐步優化設施蔬菜生產的成本結構,在保質保量的基礎上穩定降低設施蔬菜生產成本。
第四,擴大設施蔬菜種植規模,推動農戶適度規模經營。目前,設施蔬菜生產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應適當擴大蔬菜生產規模,充分利用先進的管理和技術手段,發揮比較優勢,推動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適度規模經營,全面提升農戶設施蔬菜生產的綜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