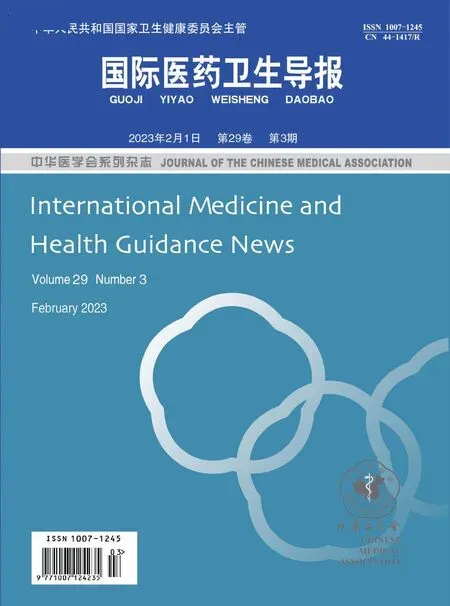特發性肥厚性硬腦脊膜炎1例
詹霞 李志霞
1威海市中心醫院神經內科,威海 264400;2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德州醫院神經內科,德州 253400
臨床資料
1.病史及查體
患者男,66歲,農民,因“周身無力4 d”于2021 年10 月入住威海市中心醫院。患者因4 d 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周身無力,右側重于左側,左上肢可平舉上抬,可持物,握力稍差,不能獨立行走,無肢體麻木,無頭痛、惡心、嘔吐,無頭暈、復視,無飲水嗆咳和吞咽困難等不適。神經系統查體:意識清,精神正常,言語流利,智能正常。眼球震顫(-),雙側鼻唇溝對稱,伸舌居中,左上肢肌力3+級,右上肢肌力3-級。雙下肢肌力4+級,四肢肌張力正常,無感覺障礙,腱反射(++),病理征(-)。頸軟,雙側克氏征(+)。
2.輔助檢查
血常規:白細胞計數11.02 ×109/L,血小板計數536 ×109/L,血小板壓積0.38 ml/L,中性粒細胞絕對值8.13 ×109/L;血凝常規5 項:纖維蛋白原4.55 g/L;全套生化:乳酸脫氫酶328 U/L,尿素8.5 mmol/L;血沉:45 mm/h;普通感染性疾病篩查(輸血常規4 項)正常。男性腫瘤標志物未見異常。抗核抗體(ANA)譜15 項、體液結核-DNA、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ANCA)、類風濕2 項[ANA、抗環瓜氨酸肽(CCP)]、抗雙鏈DNA 測定(定性+定量)正常。免疫球蛋白(Ig)G4 未見異常。
腰椎穿刺測腦壓200 mmH2O(1 mmH2O=9.8 Pa),腦脊液常規:顏色無色,白細胞計數0.026 ×109/L,蛋白定性++;腦脊液生化:微量白蛋白639 mg/L,微量總蛋白1 254 mg/L,氯116 mmol/L。肌電圖:未見異常。骨髓穿刺:骨髓呈局部增生輕度活躍。(1)粒系原早未見,形態大致正常。(2)紅系比值形態大致正常。成熟紅細胞呈正細胞正色素。(3)淋巴細胞比值形態大致正常。(4)全片見巨核細胞8個,血小板成堆易見。(5)未見寄生蟲及其他異常細胞。意見:血小板增多癥。頭顱MR+增強(圖1):考慮肥厚性硬腦/脊膜炎可能性大。小腦扁桃體下疝。幕上腦積水伴室旁間質水腫。頸椎MR+增強(圖2):考慮肥厚性硬脊膜炎可能性大,請結合臨床。C2~4 水平脊髓變性。小腦扁桃體下疝。治療14 d后復查頭顱及頸椎MR(圖1、圖2)提示硬腦脊膜增厚及小腦扁桃體疝均明顯好轉。

圖1 頭顱MR。A~D(治療前平掃):雙側半卵圓中心、放射冠及雙側腦室周圍散在斑點、斑片狀等長T1 長T2 信號影,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FLAIR)呈高信號,磁共振彌散加權成像(DWI)信號不高,小腦扁桃體向下移位;E~H(治療前增強):大腦鐮下部、小腦幕及小腦周圍硬腦膜彌漫性增厚,呈稍長T1,稍低短T2 信號,DWI 呈低信號,增強后明顯強化;I~L(治療后平掃):幕上腦白質可見多發斑點狀等T1、稍長T2信號,小腦扁桃體向下移位較前明顯好轉

圖2 頸椎MR。A~D(治療前平掃+增強):C4水平椎管內等T1、等/長T2信號影,增強后呈較均勻的明顯強化,硬膜腔變窄,病灶壓迫相應水平脊髓,脊髓見條狀長T2 信號;E~F(治療后平掃):2~4 水平椎管前方異常信號較前明顯減少,硬膜腔變窄較前明顯改善,脊髓條狀長T2信號較前明顯減少
3.診斷及治療
結合患者癥狀、影像學、腰椎穿刺等臨床診斷為肥厚性硬腦脊膜炎。起始給予甲潑尼龍500 mg 靜脈滴注,1 次/d,每3 d減半量,第10天改潑尼松片60 mg 口服逐漸減量至每日5 mg 維持,患者肢體無力明顯好轉,可緩慢下地活動,肢體也可上抬。
討論
肥厚性硬膜炎(HP)是一種累及局部或彌漫硬腦膜和(或)硬脊膜的神經系統少見疾病,表現為局限或彌漫性纖維增生伴發炎性反應[1]。多為慢性起病,可出現于各個年齡段,但以成人多見。按照累及部位不同分為肥厚性硬腦膜炎(HCP)、肥厚性硬脊膜炎(HSP)、硬腦-脊膜炎,兩者同時出現比較罕見。按照病因分為特發性肥厚性硬膜炎(IHP)和繼發性肥厚性硬膜炎(SHP)。IHP無明確病因。繼發性的多繼發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血管炎、系統性紅斑狼瘡、結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也見于中耳炎、慢性鼻竇炎或咽炎等,常見的病原體可能有金葡萄球菌、真菌、結核桿菌及梅毒螺旋體,機制可能是炎癥及感染累及硬腦膜或波及硬腦膜或者感染后機體免疫失調所致[2-5]。另外,SHP 其他的病因還有外傷、腫瘤、藥物等。該病糖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治療有效,目前大部分學者認為其發病機制與自身免疫相關。SHP 與ANCA 相關血管炎和IgG4相關疾病最為密切,有學者認為ANCA 相關的HSP 是ANCA 血管炎的中樞系統表現[6]。Chan等[7]學者則認為其是IgG4 疾病譜系疾病之一。近年也有長期服用非甾體抗炎藥后引發HSP的報道[8]。本例患者同時累及腦和脊髓硬膜,篩查未發現腫瘤,ANCA 等免疫性指標及IgG4 均為正常,僅發現血小板增多,考慮兩者之間可能有關系。
HP 的臨床表現多樣無特異性,可以表現為頭痛及顱神經受累、局部腦實質受損(癲癇、偏癱等)、腦積水、脊髓受壓、神經根刺激、尿便障礙等癥狀為主。頭痛和顱神經麻痹是硬腦膜炎中最常見的癥狀,可能與慢性炎癥刺激及顱內壓增高有關。頭痛無特異性,呈慢性,多出現于顳枕部,呈脹痛,行頭顱磁共振增強檢查前與良性頭痛無法鑒別。12 對顱神經均可受累,而且約有70%的患者均有該表現,相關文獻報道受累頻率由高到低分別為Ⅲ、Ⅳ、Ⅵ腦神經、后組腦神經和視神經,且常不對稱,其機制可能與肥厚硬膜壓迫、炎癥刺激及顱內壓增高相關[9]。累及脊膜時多位于頸胸段,可累及1 個或多個脊髓節段[10]。主要表現為神經根痛和脊髓受壓,表現為頸胸背痛、雙下肢無力、肌肉萎縮、下肢無力,可伴發有尿便障礙。本例患者雖累及硬腦膜,但未出現后顱窩神經受累,僅表現為脊膜受累導致的脊髓受壓癥狀,即四肢無力,且上肢重于下肢,僅為運動系統受累,未發現感覺異常,也符合頸椎核磁病灶特點。
HP 實驗室化驗無明顯特異性,可有血沉、C-反應蛋白增高,也可見到自身免疫指標,比如P-ANCA、髓過氧化物酶、ANCA、ANA 及類風濕因子等升高,即使本身不合并免疫性疾病也可能出現上述免疫指標異常,因此,對于懷疑該病的患者應常規進行免疫指標篩查。本例患者自身免疫指標僅發現抗心磷脂抗體IgM 陽性,但未發現血栓及血小板數減少等,考慮為HP 本身所致。腦脊液檢查無特異性,顱內壓可增高也可降低,白細胞計數、蛋白可升高,糖和氯化物多為正常。本例患者腦壓增高,白細胞計數及蛋白增高,也符合文獻報道。有學者研究提示腦脊液蛋白升高程度越高,硬脊膜受累越廣[11]。而核磁增強是診斷HP 的有效方法,可以評估累及部位、范圍、嚴重程度,還可以用于評估治療效果和預后。肥厚的硬膜在T1上呈等或略低信號,T2上呈明顯低信號,是因為肥厚增生的硬膜主要成分是纖維組織,大腦鐮和小腦幕的硬腦膜強化則多表現為軌道征。T2 序列上有時低信號周邊可伴有高信號,是因為增生的硬脊膜周圍伴發炎癥細胞所導致的。局部病灶多位于小腦幕、大腦鐮、雙側額部、鞍旁、海綿竇等處,可見線性或結節性強化,結節樣強化相對少見,提示預后不好[12]。大腦鐮和小腦幕強化后所呈現的“奔馳征”和“埃菲爾鐵塔征”是HP的特征性征象[13]。如果伴有靜脈竇血栓、腦實質受累時可有相應的影像學表現,此外還可探查到腦水腫、繼發性腦白質改變、腦積水、腦梗死及繼發性顱內出血等。
現HP的治療尚缺乏循證學依據,但是首先是對各項感染指標進行分析后進行病因治療,針對病原菌感染需行抗病原菌的治療。對于IHP 目前主要以糖皮質激素或免疫抑制劑治療為主。糖皮質激素可以選用甲強龍、氫化可的松、地塞米松,沖擊治療后根據病情逐漸減量,減量過程應慢,改為口服維持數月至數年,其療程長短目前也無統一結論。少數患者在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時病情惡化,若在減量過程中有病情加重,再次加大糖皮質激素劑量也可以獲得良好的療效。目前多數觀點認為,單用糖皮質類固醇激素治療病情易復發,聯用免疫抑制劑則可以減少這種情況的發生[14]。當肥厚的硬膜產生明顯的神經壓迫癥狀或者對糖皮質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無反應者時可考慮外科手術治療,椎板成形術要優于椎板切除,術后輔以糖皮質激素或免疫抑制劑治療[15]。關于HP的自然病程的研究很少,多數患者經糖皮質激素治療其臨床癥狀及影像學表現得到明顯緩解,且可以保持長時間病情穩定,預后較好,但臨床癥狀完全恢復較困難,遺留神經障礙的程度與治療前的病程呈正相關,但也有糖皮質激素治療無效,病情逐漸加重的患者。本例患者應用甲潑尼龍治療,后改為口服,癥狀改善明顯,其遠期預后以及是否有復發仍需進一步隨訪觀察。
綜上,HP 臨床表現不典型且多樣、病因多樣,臨床易漏診、誤診,當臨床出現頭痛、顱神經受損、神經根痛或脊髓受壓時應當想到該病可能,盡早完善實驗室及核磁影像學檢查,必要時可行病理檢查協助診斷。并盡早進行病因和免疫抑制等相關治療,改善患者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