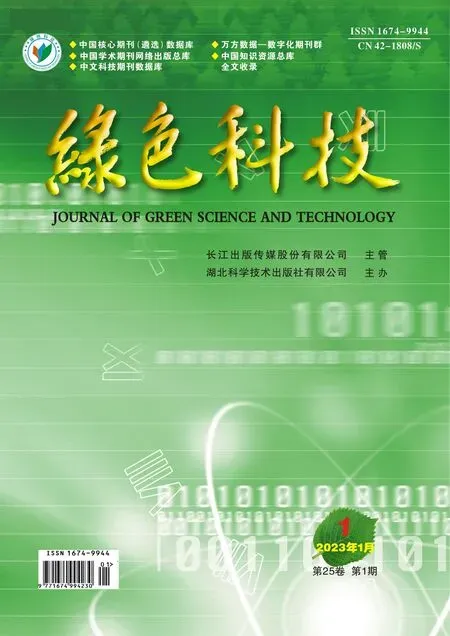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發展的增收效應研究
王夢月,邱守明
(1.西南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4;2.西南林業大學 地理與生態旅游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4)
1 引言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促進農戶持續增收始終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中心任務。《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要把維護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把實現農民共同富裕作為落腳點,推動農民不斷增收[1]。生態旅游扶貧作為中國脫貧攻堅戰略的重要手段之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為自然保護區周邊農戶脫貧發揮了巨大作用,對于我國實現鄉村振興具有重大意義。因此,研究自然保護區周邊農戶的生態旅游增收效應,對于理清生態旅游的增收途徑,鞏固和提高生態旅游成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學者們普遍認為,發展生態旅游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減緩當地貧困程度,并給當地農戶帶來就業機會,進而增加個人及家庭經濟收入[2~5]。從宏觀角度上來看,Kiernan認為,在某些自然資源富集的國家可通過發展生態旅游來創造經濟效益和保護地方生態環境[6];Snyman將生態旅游視為一種促進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高效可持續土地利用方式[7];溫彥平等分析了生態旅游開發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生態旅游開發既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又能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發展注入活力[8]。從微觀角度來看,不少學者認為生態旅游發展能夠顯著增加農戶收入,并指出了社區農戶參與的重要性[9~14]。然而,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生態旅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與地域有關,景區內農戶呈現正面影響,而對景區周邊(景區外)農戶呈現負面影響[15];還有學者指出生態旅游發展可能會引起景區周邊物價水平上漲,降低農戶的生活水平[16];韓鋒等[17]和Mahadevan R等[18]認為生態旅游發展可能會增加農戶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段偉等基于922份農戶調研數據,分析自然保護區周邊農戶對保護收益及損失的感知,發現就業機會更多和從生態旅游中獲益的農戶擁有更高的家庭收入,自然資源利用受限和發生野生動物致害的農戶擁有較低的收入[19]。學者們關于生態旅游對農戶收入影響的研究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與方法,為研究開展起到了參考和借鑒作用。
本研究通過分析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增收效應有助于鞏固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扶貧效果,防止已脫貧農戶返貧,促進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對全國各地的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提供發展經驗。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2017年10月調研組選取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邊的行政村,涉及烏蒙鄉和轉龍鎮2個鄉鎮3個村委會4個村小組。調查對象為參與生態旅游農戶和未參與生態旅游農戶,調查方式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以座談、訪談等方法。收集調查問卷80份,其中有效問卷68份,問卷有效率為85%,樣本村中大村子、大麥地、何家村、炭山村各收回有效問卷數29份、13份、13份和13份。在調查的68個樣本中,從性別來看,男性所占比重73.5%,女性所占比重26.5%,男性比例高。從年齡分布來看,農戶年齡在30歲以下的占比10.3%,31~45歲的占比26.5%,46~59歲的占比35.3%,60~75歲的占比27.9%。從學歷分布看,文化程度小學以及以下的占比72.1%,初中文化的占比22.0%,高中(或中專)文化的占比5.9%,大專及以上的占比0%,反映了當地農戶受教育程度低的特征。
2.2 研究方法
雙重差分模型(Diffferences-in-Diffferences,DID)是評價某項政策或項目執行后效果的有效方法[20],本研究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將參與生態旅游農戶設置為試驗組,將未參與生態旅游農戶設置為對照組,評估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開發前后農戶的增收效應。用虛擬變量D來定義是否參與保護區生態旅游發展,D=1代表參與生態旅游,即實驗組,D=0代表未參與生態旅游,即對照組;用虛擬變量T來定義生態旅游發展時期,T=0代表生態旅游發展前,T=1代表生態旅游發展后。因此,參與生態旅游農戶和未參與生態旅游農戶在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發前后收入的差異的差值即為參與生態旅游發展農戶的增收效應,即為:
DID=[E(Y|D=1)-E(Y|D=0]-[E(Y|T=1)-E(Y|T=0]
(1)
建立DID模型為:
Y=β0+β1T+β2D+β3TD+ε
(2)
式(1)、(2)中:Y為被解釋變量;TD為交互作用;ε為隨機擾動項。
3 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旅游發展前后農戶收入變化
按照收入來源分類,農戶家庭收入可以劃分為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以及財產性收入[21]。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大規模開發生態旅游的時間為2010年,因此選擇2009年作為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邊農戶未參與生態旅游前的收入水平,參與戶和未參與戶在生態旅游開發前后各項收入變化情況見表1。

表1 農戶家庭各項收入變化情況 元/人
從表1可以看出,參與戶和未參與戶在生態旅游開發前后的總收入有著明顯的增加。其中,參與戶在生態旅游開發前后的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增加,未參與戶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增加,但是轉移性收入下降,參與戶和未參與戶的財產性收入變化差異分別為0和1.67元,因此可以忽略不計。參與戶的總收入、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幅度都要大于未參與戶,凈變化差值分別為15675.1、9224.69和1209.62元。由圖1所示,從各項收入來源對農戶總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來看,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對農戶總收入的貢獻率較高,分別為58.85%和33.42%,其次是工資性收入,為7.72%,財產性收入的貢獻率最小,僅0.01%。

圖1 總收入凈變化的貢獻率
3.2 雙重差分模型結果
運用公式(2)對DID模型結果的顯著性進行檢驗,表2為DID模型檢驗結果,其中,模型(1)代表人均總收入的檢驗結果,模型(2)代表人均經營性收入,模型(3)代表人均工資性收入,模型(4)代表人均轉移性收入,模型(5)代表人均財產性收入。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別在5%、1%和5%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模型(4)和模型(5)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生態旅游發展對于農戶人均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影響不顯著。

表2 DID模型回歸結果
模型(1)的DID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生態旅游發展對農戶人均總收入起到正向促進作用,即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的發展顯著提高了參與戶的總收入水平。模型(2)的DID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生態旅游發展對農戶人均經營性收入起到正向促進作用,即與未參與戶相比,參與戶在轎子山保護區生態旅游開發前后的經營性收入有著顯著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開發生態旅游后,農戶可以利用自有房屋為游客提供一些餐飲和住宿服務,大大提高了農戶的自營收入。
4 結論
本研究以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邊農戶調研數據為支撐,通過構建DID模型分析生態旅游發展對農戶的增收效應。研究結果顯示:生態旅游發展對于提高人均總收入和經營性收入都有顯著影響,參與生態旅游發展的農戶家庭的人均總收入顯著增加了15675.1元,其中,經營性收入顯著增加了9224.69元,轉移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分別增加了5239.17元和1209.62元,但不顯著;從收入構成情況來看,人均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貢獻率較大,其次是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貢獻率最小。
研究中發現,轎子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邊農戶對生態旅游的參與度仍然較低,但是農戶參與意愿較為強烈,農戶普遍存在能力不足、資金有限、參與渠道狹窄等問題,如果沒有政府、企業或合作社的組織和引導,多呈現出自發參與、規模小、無法形成規模效應等現象,僅有極少數家庭位置優越的農戶能夠獲得較好收益外,其他農戶要么無法參與生態旅游發展,要么即使參與生態旅游,收益也極其有限,難以通過生態旅游發展有效帶動家庭增收。一方面,可以通過農旅結合的方式來解決農戶參與渠道狹窄的問題,應充分挖掘當地生態旅游資源,培養當地農戶參與生態旅游的自主意識,通過生態旅游結合生態農業和當地民俗活動等方式實現農旅結合;另一方面,針對農戶經營分散、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對游客吸引力不足的問題,可以通過政策指導、政府引導、村民參與等形式,在生態旅游景區入口處尋找合適村莊或規劃一定區域打造“入口社區”,合理規劃、引導農戶家庭提供住宿、餐飲、購物等產品,進行規模化管理,對農戶進行專業知識、技能培訓,讓農戶在基礎設施完善、資源集中整合、良性市場開放的環境下進行經營,這樣既可以吸引游客,為有餐飲、住宿、購物等需求的游客提供良好的場所,為周邊農戶家庭提供增收機會,同時可以潛移默化地培養農戶對當地自然和文化的保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