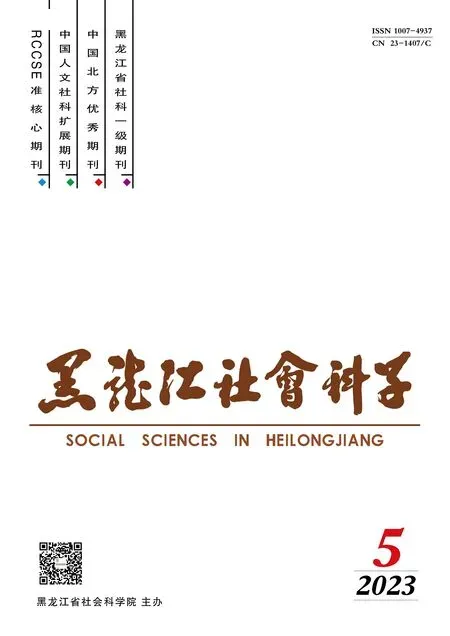以文制武:明代九邊武官所處的權力與輿論世界
程 彩 萍
(廊坊師范學院 社會發展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有明一代,沿邊始終面臨著嚴峻的軍事形勢,因此邊防事務備受重視。北邊衛所設置較早,朱元璋時期利用衛所守土實邊、管理軍民事務,形成了初步的軍事防區:“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西北邊境與胡虜密邇、慮為邊患,故于甘州設立陜西行都司,寧夏設立五衛所,大同設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設立萬全都司,古營州設立大寧都司,于遼東古襄平設立遼東都司:各統屬衛,如臂指之相使,氣脈之相屬,以捍御夷虜。”(馬文升:《為經略近京邊備以豫防虜患事疏》)[1]卷64,545永樂以后,中央逐漸派遣勛臣或都督充當總兵鎮守北邊,衛所軍職受總兵節制、聽從調度,九邊防御體系也由此逐漸完善:“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萬里,分地守御。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為九邊。”(《明史》卷91《兵志三》)[2]2235可見,九邊武官處于衛所、軍鎮多層管理體制之下,而且隨著以文統武格局的形成,除了要遵守軍紀、軍法外,九邊武官又受到文臣節制、內官監督、言官彈劾等多重約束,增加了九邊軍事司法運行的復雜性。目前學界對明代九邊的整體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3],本文擬對明代九邊武官在日常軍政及作戰過程中受到的行政監督、軍法威懾、輿論壓力進行探討,以期深化對九邊事權分配與制衡所帶來影響的分析。
一、日常軍政中九邊武官所受監督與約束
明代軍政事務涉及較廣,衛指揮使司“凡管理衛事,惟屬掌印、僉書……分理屯田、驗軍、營操、巡捕、漕運、備御、出哨、入衛、戍守、軍器諸雜務”(《明史》卷76《職官志五》)[2]1873。九邊武官須遵守相應規定、履行職責,這些內容明確記載于接受朝廷任命的敕書中。如宣德元年(1426)八月,朝廷命指揮芮勛守居庸關,其敕曰:“今命爾守關,軍士必勤訓練,關隘屯堡必嚴守備,譏察奸偽不可懈怠,或有警急即遣人馳奏,一切邊務必與附近總兵官協謀審處,毋慢毋忽。”(《明宣宗實錄》卷20,宣德元年八月丁卯)[4]528
邊鎮武官是否認真履行了以上職責,一方面會通過軍政考選進行考核,另一方面則通過中央巡視制度進行監督。巡視邊鎮或邊關制度始于明初,明成祖給成山侯王通的敕書中強調了巡視軍政的重要性:“修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為急務,而各衛所比年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陜西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務俾隊伍整齊,甲兵堅利,備御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明太宗實錄》卷200,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4]2083
隨著九邊防御體系的建設以及以文馭武格局的發展,九邊職官體系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除了使用武官鎮守邊關、經營軍鎮外,明廷開始陸續派遣文臣與內官前往九邊,對武官進行監督和考察,加強對武官的行政約束。朝廷曾“每季遣官巡視居庸、山海等處關隘,有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士未足、守卒年久未更者,逐一理之”,后來停罷,宣德十年經兵部尚書王驥奏請,再次命監察御史、給事中巡視邊關(《明英宗實錄》卷2,宣德十年二月乙巳)[4]40。
明代中央巡視或閱視制度至弘治時期被確定為三年舉行一次。弘治三年(1490)兵部奏請敕各邊守臣及時修理墩墻,并每三年仍特遣大臣閱視以行勸愆,孝宗批準曰:“邊備事重,正宜以時修葺,其如所奏,令各邊守臣整理,仍三年一遣大臣閱視,不得虛應故事。”(《明孝宗實錄》卷42,弘治三年九月乙卯)[4]867巡視期間,會考察軍馬、器械、城堡等軍政是否修舉,并對不稱職的武臣進行彈劾。嘉隆時期又進一步細化了巡視的內容以及對邊臣是否稱職進行衡量的標準。隆慶五年(1571),高拱奏準賜敕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又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眀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5]從高拱所述內容看,涉及軍餉供應類的包括錢糧、屯田、鹽法,防御工事類的則如關隘、城堡等,以及軍隊人數和裝備等,皆為日常軍政建設中的重要內容。為了提高武臣修舉軍政的積極性,高拱建議將其提高到與指揮作戰同一層次,對懶于修舉軍政者,與失誤軍機同等處罰。張居正亦指出,閱視時以“八事”為最緊要者,即使遇到三年一次的貢市亦不能撤銷,可同時進行:“然閱視以八事為殿最,貢市以款虜為勤勞;閱視優于要職,貢市逮于卑官,固自并行而不悖。”[6]
明代派遣中央大臣巡視九邊的制度亦時有變化和調整,主要是圍繞時間和人員安排,比如選擇三年一次派遣大臣閱視還是令巡按御史每年一次閱視。楊嗣昌認為令巡按御史閱視邊關與其本身職責并行不悖,可謂一舉兩得,而針對有些人對巡閱頻繁產生的顧慮,他則指出年年閱視的必要性:“兵馬錢糧,年年有銷耗,季季有開除。戰守機宜,時時有變更,事事有因革。將領賢否,應處罰者,尚不待于時刻,豈可淹于三年,人情積玩,邊事積壞。巡邊御史果能務行實事,不徒虛文,則一年一閱,其關于整飭,鼓勵不小。”[7]崇禎十年(1637)九月十九日,皇帝批準了其建議。
除了巡視與監督制度之外,明代建立的巡撫、總督制度對九邊武官形成了更為全面和固定的行政約束。《明史》卷73《職官志二》載:“巡撫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撫陜西。永樂十九年,遣尚書賽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后不拘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畢復命,即或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2]1767此時巡撫的派遣并未固定,其職責亦未明確規定,對武官節制與否尚難確定。至明英宗時期,巡撫制度逐漸成熟和固定,從巡撫蘇松江浙一帶擴展到北邊。正統八年(1443)九月,命監察御史李純巡撫遼東,令其專門整理屯田之事。遼東位于邊遠地帶,地域廣闊、軍馬眾多,糧草則俱憑屯種供給。而彼時都司衛所官往往占種膏腴,私役軍士,虛報子粒,導致軍士饑寒,因而逃避軍役,故特遣巡撫予以革除弊病。敕書中寫道:“今特命爾代浚總督屯糧,比較子粒,提調倉場,收支糧草,務在區畫得宜,尤在敷宣德意,扶植良善。遇有官吏酷害,私役占種等事,除軍職具奏,其余就行拿問。”(《明英宗實錄》卷108,正統八年九月戊寅)[4]2195
隨著巡撫職權的不斷擴大,逐漸具備“從宜處置”“便宜處置”的權力,遂也兼及提督軍務、節制兵馬等事項。天順二年(1458),升陜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芮釗、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陳翌、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王宇俱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分別巡撫甘肅、寧夏、宣府。賜之敕曰:“今特命爾等巡撫各邊地方,訓練軍馬,整飭邊務,撫恤士卒,防御賊寇,務令衣甲齊備,器械鋒利,城堡、墩臺修治堅完,屯田、糧草督理充足。禁約管軍頭目,不許貪圖財物、科克下人及役軍余、私營家產,違者輕則量情發落,重則奏聞區處。凡一應邊務事情、軍馬詞訟及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悉聽從宜處置。”(《明英宗實錄》卷291,天順二年五月壬寅)[4]6219巡撫芮釗等人須禁約管軍頭目科斂、私役軍人,輕罪可以直接發落,遇緊要之事,仍然要與鎮守、總兵等官會同處理。成化九年(1473)頒給巡撫遼東、大同等處都御史彭誼、鄭寧的敕書中,對其管轄權限有明確交代:“中間若役占軍士、委用非人,以致軍旅不精、守御無備者,指實具奏。管軍頭目自都指揮而下有貪懦無為者,從公罷黜,別選材武智能者代之。應逮問者,就爾逮問區處,以示警戒。”(《明憲宗實錄》卷120,成化九年九月壬子)[4]2321
縱觀嘉靖至萬歷時期頒給巡撫的敕書,與上述成化年間的敕書內容基本一致。嘉靖十五年(1536),御史張景總結頒給各邊巡撫敕書中涉及的職權說:“敕內有防御虜寇、修理城池、整飭軍馬、區畫糧餉、謹關隘、明賞罰諸事。”(《明世宗實錄》卷184,嘉靖十五年二月乙巳)[4]3907隆慶五年,在給遼東巡撫張學顏的敕書中寫道:“有警則公同鎮守、總兵等官,調度官軍,相機殺賊。禁約管軍頭目,不許科擾、克害及隱占、私役,有誤戰守。違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毋畏勢豪,徑自參奏拿問。”(《敕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學顏》)[8]286安撫軍民、監督武臣是巡撫的重要職權,遼東“守邊官員行事乖方,以致地方不靖”,故有必要派巡撫前往處理。萬歷時期,頒給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荊等關孫丕揚的敕書中亦提到:“所屬官員廉能干濟者量加旌獎,貪酷不才者從公黜罰。軍民人等詞訟即與受理,軍職及文職五品以上有犯,奏聞區處,其余就便拿問,或發巡按御史究治。”(《敕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丕揚》)[8]278可見,巡撫掌握著賞罰大權,雖不能直接按律處置武臣,但具有監督、約束、舉劾武臣的權力。事實上,在任的巡撫確實彈劾了很多不稱職的武官。如遼東巡撫胡本惠彈劾鐵嶺等處守備都指揮僉事皇甫英不嚴設備,“以致虜寇入境殺掠人畜”,并將其發遣到巡按御史朱暟處審理。皇甫英論罪當斬,最終給予降三級、于當地立功的處分(《明英宗實錄》卷354,天順七年秋七月丙申)[4]7079。
成化年間,由于西北戰事緊張,為了更有效地調度軍馬,朝廷開始派遣專門統轄軍務的總督。成化十年正月,首加王越以總制之名,統馭各處總兵、巡撫。此為臨時性質,戰事稍息,即將總制召回。總制兼有文臣提督軍務、武臣節制軍馬的雙重權力,其設置成為文臣總督軍務的一個重要嘗試。而陜西三邊總制的出現,也遵循了明代先由武臣統軍、后添設文臣參贊軍務,文武制衡,最終實現以文馭武的發展趨勢。據《明會典》記載:“總督陜西三邊軍務一員。弘治十年議遣重臣,總制陜西、甘肅、延綏、寧夏軍務。十五年以后,或設或革。至嘉靖四年始定設。四鎮兵馬錢糧一應軍務從宜處置。鎮巡以下悉聽節制,軍前不用命者,都指揮以下聽以軍法從事。”嘉靖十五年,宣大延寧皆有虜警,復設宣大總制官,并更名為總督,陜西三邊總制亦更名為總督(《明世宗實錄》卷193,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甲寅)[4]4069。自后,一直沿用總督之稱。
總督較巡撫而言,具備直接節制總兵官等武臣的權力。弘治十四年,命秦纮總制陜西固原等處軍務,其敕曰:“命爾總制,凡軍馬錢糧等項,宜逐一從新整理,俱許便宜處置。遇有虜寇侵犯,即便隨宜調遣各路軍馬相機剿殺,各該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明孝宗實錄》卷179,弘治十四年九月甲辰)[4]3311隆慶二年,譚綸以兵部左侍郎出任薊遼總督,其敕曰:“其薊、遼、保定鎮巡并各鎮參游所屬地方,各道兵備添設修筑墩堡等項官員,俱聽爾節制。各領兵等官敢有臨陣不用命者,自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其余軍衛、有司官員有犯,輕則徑自提問,重則參奏究治,庸懦不職者一體糾劾。凡軍中一應事宜,并敕內該載未盡者,悉聽爾便宜區處。”(《敕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譚綸》)[8]245均可見一斑。
萬歷二年(1574),升楊兆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其對武官的節制具體到“薊遼、昌平、保定鎮巡、協守、分守、副、參、兵備及統領、入衛領班等項官員”,“許以軍法從事”的范圍擴大到參將以下:“各領兵將官有臨陣退縮、承遣逗遛、抗違軍令,及沿習舊套割取死首冒功脫罪者,參將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副總兵以上先取死罪招由,奏聞處治。”(《敕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8]247顯然,總督被授予轄區內最大軍權,不僅督察日常軍政,而且有權節制武臣、調度軍隊。
晚明時期總督制度進一步發展,出現了比總督轄區更廣的經略。萬歷十八年,朝廷命兵部尚書鄭雒經略陜西、延綏、寧夏、甘肅、宣府、大同、山西七鎮軍務,兼理總督。經略鄭雒因管轄范圍太廣,欲辭去其任:“臣欲往甘肅,則洮河難顧,欲驅流寇,則套虜難防。恐四夷聞之,謂臣一人之身,忽然而經略,又忽然而總督,邊事日去,國體益輕。”然神宗不允所辭(《明神宗實錄》卷230,萬歷十八年十二月己巳朔)[4]4259。兵科給事中薛三才亦力薦鄭雒兼管總督事務:“論事權,經略之權重于總督,論責任,總督之責專于經略,一人操其重權,又一人分其專責,事體未便。乞敕該部酌議,仍敕鄭雒兼理總督,庶事權不分,而雒亦得以安心,殫力于西陲矣。”(《明神宗實錄》卷230,萬歷十八年十二月己巳朔)[4]4259可見經略之事權更大,明末遼東戰事頻仍,熊廷弼、王在晉皆曾擔任過遼東經略。
明廷除了派文官赴邊地整理邊務、節制官軍外,還派遣鎮守內官與總兵協同鎮守。如派御馬監太監王清前往寧夏鎮守,其敕曰:“今特命爾與總兵官都督同知張泰鎮守寧夏地方,修理邊墻、城池,操練軍馬。遇有賊寇,相機戰守。凡事須與總兵、巡撫等官公同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拗己見,有誤事機。爾為朝廷內臣,受茲委托,尤宜奉公守法、表率將士。”[9]藩鎮,32從敕書規定的鎮守內官的職權來看,其可參與邊鎮軍政、管理軍務,但并無節制總兵的權力;內官作為皇帝的心腹更多的是起到監督邊將的作用[10]。這樣就將邊鎮武官置于文官節制、內官防備的制度約束之中:“自設立武衛之后,次第添置,撫之以臺臣,馭之以將領,佐之以裨監,贊之以督理。尤慮安攘之術未盡,首命中臣寅同鎮守,蓋欲參知戎務、心腹朝廷、防閑內外之深意也。”[9]公署,40
二、戰時九邊武官所受“軍法從事”之權的威懾
戰時面對緊急形勢,有些總督、經略被授予尚方寶劍,對于臨陣退縮的武臣可以先斬后奏。萬歷二十年,寧夏哱拜發動叛亂,明廷命三邊總督魏學曾統率大軍鎮壓,然因賞格未明、軍威不振,致延宕數月尚未平息。神宗下旨切責“威令不肅,諸將生玩其間,復有希功忌能、觀望之念”,并“賜學曾劍一口,將帥不用命者,軍前斬首以殉”(《明神宗實錄》卷249,萬歷二十年六月己丑朔)[4]4630。然總督魏學曾仍然師久無功,遂“以(葉)夢熊代,賜劍專征,用蠟書約城中內應,遂擒哱拜、哱承恩以獻”(《明神宗實錄》卷323,萬歷二十六年六月庚午)[4]6006。萬歷四十六年,女真南侵,攻打清河,而總兵杜松等尚未出關,而其他各鎮除了宣大、山西總兵官率兵起程外,大多按兵不動。兵部奏稱形勢緊急,一旦清河失守則危及全遼、延及畿輔,因此必須嚴督各總兵前往增援:“我皇上起用經略,雖責以征剿之重任,而未嘗畀以生殺之大權,是以臣前具末議,首請賜上方劍正為閫外之制。權不重則令不遵,非是無以震懾人心,而使之爭先效命耳……伏乞皇上查照往例賜劍尚方,凡將帥有不用命者,自總兵以下,經略俱得以軍法從事。”[11]神宗予以批準:“爾部便遵屢旨,并各鎮兵馬都催他星馳出關,以聽調度。著賜劍一口,將帥以下有不用命者,先斬后奏,務期剿滅狂虜,以奠危疆。”(《明神宗實錄》卷573,萬歷四十六年八月庚申)[4]10821熊廷弼經略遼東時亦曾賜尚方劍:“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而下先斬后奏,兵餉額解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明熹宗實錄》卷12,天啟元年七月甲辰)[4]588此類奉命專征,皇帝旨在通過賜尚方劍以重事權兼隆禮數。
上述總督、經略被授予“軍法從事”與“便宜處置”乃至“先斬后奏”的權力,也即無須經過奏聞、審理等司法程序,依照軍法律令便可施以相應的懲罰措施。正統九年,命左副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其敕曰:“爾等整搠見操官軍,務要人馬精健……遇賊近邊即相機剿殺,飛報附近邊軍互相策應,敢有怠慢誤事者,悉以軍法從事。朝廷以爾廉公有為,諳練兵務,特簡拔委任,一應軍務,悉聽爾便宜處置。”(《明英宗實錄》卷118,正統九年秋七月丁卯)[4]2386弘治十四年,西北有警,孝宗命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總兵官朱暉等率京軍前往,繼而朱暉奏乞假以便宜之權,授其敕書遂曰:“參將而下及所在各該鎮巡等官悉聽節制,官軍頭目人等敢有違犯號令者,重以軍法處治。其有臨陣退縮、不用命者,指揮以下就便斬首示眾,然后奏聞。其斬獲首級,俱送紀功官處審驗明白,從實開報,以憑升賞,不許冒濫。”(《明孝宗實錄》卷173,弘治十四年四月戊子)[4]3154
所謂“軍法從事”,即以軍令、律法為依據,此外還有專門的號令,往往比較嚴厲。如永樂十二年(1414)所頒“軍中賞罰號令”有很多詳細規定,包括是否盡力殺敵、隊伍是否整齊、軍器物資是否愛惜、有無擄掠無辜以及是否泄露軍機等多個方面,獎懲力度較大。其中規定:“臨陣交鋒,務要一時向前殺敗虜賊,如不盡力殺敗虜賊者,全伍皆斬。”(《明太宗實錄》卷150,永樂十二年四月己酉)[4]1747又規定:“有將軍器故意拋落遺失及盜賣者,治以重罪。”(《明太宗實錄》卷150,永樂十二年四月己酉)[4]1748《大明律》則載:“凡將帥關撥一應軍器,征守事訖,停留不回納還官者,十日杖六十,每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輒棄毀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二十件以上斬。遺失及誤毀者,各減三等,軍人各又減一等,并驗數追陪。”[12]
陣前軍法的實施,自明太祖時就受到重視。當時浙江左丞胡德濟在大將軍徐達軍中,因臨事畏縮被械送至京。明太祖念其舊勞特命宥之,同時遣使敕諭徐達以后要在軍中嚴格執行軍法:“邇者浙江左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眾,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明太祖實錄》卷51,洪武三年夏四月乙酉)[4]1008
軍法能否得以實施關系到全軍紀律是否嚴明,因此除了總督等擁有“軍法從事”之權外,朱鑒還主張給予總兵一定的生殺大權:“況總兵既無擅殺之權,軍壯又無畏法之心,以致調往避難者相繼而逃,臨陣畏死者成隊而退,習為常事,全無紀律。再不假以威權、申以軍令,誠恐因循月久,姑息日深,草場不敢放收,糧道不得速通,馬必瘦死,人不聊生,必墮賊計,致誤事機。”(朱鑒:《陳言邊務疏略》)[1]卷35,269夏良勝亦提出:“軍威以殺為主,故曰軍旅之后,必有兇年,全勝之功,古今幾見……我屢敗而未戮一將與卒,故進則死,而退則可生,勝敗之異,職此之由。伏望陛下申令主帥,使副屬而下,俱得按法行誅。”(夏良勝:《論用兵十二便宜狀》)[1]卷154,1542成化元年九月,陜西巡撫項忠也上疏請求授予總兵“軍法從事”之權:“今陜西三邊掛印總兵,遇敵逗遛,無一人肯當前者,雖云智勇未能如古名將,蓋亦委任有未專焉。況鋒鏑交于原野,機會變于斯須,呼吸之間有生有死,若不委以軍法從事之柄,孰肯輕生以御敵哉!今軍士但聞敵之可畏,而不畏總兵之號令,以總兵之權輕也……宜敕各邊總兵官,今后聞有大敵在前,軍中有違主將號令者,悉以軍法從事,庶幾成功。”(《明憲宗實錄》卷21,成化元年九月壬戌)[4]417
遼東巡撫畢自肅曾因遼事不靖長達十年,導致中央與地方苦于籌備軍餉,將士苦于艱險,士卒苦于鋒鏑,就如何解決戰事提出若干建議,其中一條為“嚴賞罰之令”,建議兵部刊行專門的軍法,以備賞罰:“聞之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圣王無以治天下,況兵兇戰危……今當敕兵部考定軍法,刊之為令,何者宜賞,何者宜罰,使彼眾自曉然無疑,一遇賞罰求之于令足矣。而又矢公虛斷以信,必賄賂、情面舉無所施,然后人知法在必行。”[13]軍法的嚴格實施顯然有利于防御力量的加強,如賈俊巡撫寧夏,“持憲度、嚴軍法,數年虜不敢犯”[14]。
然而,因“軍法從事”之權關系到官軍生死,故皇帝對此極為謹慎,并不輕易授予,且授予時一方面會在敕書內寫明,另一方面還要強調所謂軍法并不專殺,也要依據律法,按照輕重論處。如弘治十年九月,孝宗召見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人,討論大同總兵官吳江奏請“臨陣以軍法從事”之事。孝宗認為如準其所奏,“恐邊將輕易啟妄殺之漸”。劉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孝宗曰:“雖然,亦不可徑許。若命大將出師,敕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御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而李東陽堅持認為:“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卻恐號令從此不行。”孝宗最終采納了謝遷的提議:“今遵圣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15]
可見,戰時厲行“軍法從事”雖然可以嚴明軍紀,促使官軍勇無直前、進而取得勝利,然而實際上留給總督、巡撫、將帥等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對總督、巡撫而言,通常情況下武官有罪仍要奏請處置,自行斬殺則犯了擅殺之罪。弘治時期宣府巡撫雍泰即因責罰參將而被罷官。時參將李稽不法,部下上告其惡,雍泰“具草將聞于上”,結果“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太(泰)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由于雍泰當庭杖打參將,“言官遂劾太(泰)以擅辱命官罷”[16]。李稽則奏雍泰“凌虐將官,貽患邊徼”。通過稽查,法司議奏:“雍泰凌虐李稽,雖云過當,而稽實以罪系獄,其致死人命雖不以私,而用刑非制。”隨后雍泰被勒令致仕,最終被革職為民。其自陳“公罪律應免問,乞垂矜宥”,不允(《明孝宗實錄》卷177,弘治十四年閏七月辛卯)[4]3253。
綜上,不論日常軍政中對九邊武官的監督與約束,還是戰時對其的軍令制約,皆體現了明代以文馭武的發展趨勢。“軍法從事”的實施對象不僅包含軍士,亦包含武臣,甚至總兵以下皆受制約,從理論上突破了軍職有犯須奏請處置的司法程序。然而獲得“軍法從事”之權并不等同于完全掌握了生殺大權,總督、巡撫不經皇帝批準、未經法司勘問,直接按軍法處置武官,稍有差池就會引來非議,甚至被處罰。可見授予總督、巡撫等“軍法從事”之權,主要意在產生威懾力量,有利于立軍威、行軍紀,宣示將兵之權。
三、朝野輿論對邊將所受司法約束的影響
邊將犯公罪尤其犯“失誤軍機”罪的司法審判,往往涉及功過的評定,其關系到軍中賞罰是否嚴明,因而備受關注,其處理甚至超出了司法領域的范疇,受到朝廷政治的影響。而朝廷的言官則會對涉事官員進行劾奏,以阻止其逃脫罪責,言官群體對九邊武官的牽制與影響即由此顯現出來。
隆慶初年大同失事一案的審判便體現了群臣的政治輿論作用。事情起因為蒙古入犯大同,持續七日方撤離,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而總督陳其學、巡撫李秋卻虛報軍情:“本鎮探得虜情,預為之備,以故虜無所利,總兵趙苛等先有邀擊,皆有俘斬功,宜加賞錄。”而巡按御史燕儒宦所言則與其相反:“虜自入境來,我兵無敢發一矢與之敵者,攻陷堡塞,殺擄人畜甚多,宜正諸臣玩愒之罪。”這件事迅速引起朝廷文官的注意,都給事中張鹵等率先劾奏:“邊臣欺罔,請嚴究如法。”由于雙方各執一詞,于是兵部奏請下御史勘實以聞。而穆宗卻令總兵官趙苛等戴罪防秋,參將袁世械等交由御史提問。言官如給事中查鐸、御史王圻等則再次提議將其治罪。隨之巡按御史燕儒宦更詳述事發經過:“(趙)苛遂提兵遠屯,參將方琦等皆不設備,游擊施汝清等又畏縮不前,遂令懷、應、山陰之間任其蹂躪,陷堡塞大者二所,小者九十一所,殺掠男女及創殘者數千人,掠馬畜糧芻以萬計。我軍雖嘗出邊,稍有擒斬,然竟未接一戰。”(《明穆宗實錄》卷38,隆慶三年十月甲辰)[4]955
針對此事,穆宗令內閣發表看法,大學士趙貞吉主張順應群臣公論,依照律法嚴懲失機將官:“邊事為平章第一要務,于今反漫然視之。國家之事最重者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又安可不勉乎?今正大同之罪,只以‘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個字斷之足矣。八字理明詞嚴,‘主將不固守’,祖法也;隆慶元年皇上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守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哉!”面對“今兵部題覆,仍循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之意”的情形,趙貞吉以打算隱退表明自己的立場,據理力爭(趙貞吉:《議邊事疏》)[1]卷255,2691。最終得旨:“趙苛避事殃民,本有常刑,姑降實級三級,陳其學降俸二級,李秋奪俸半年,胡鎮、文良臣各降一級。麻貴賞銀二十兩,麻錦、葛柰各十兩,方琦等六人皆謫戍,施汝清等九人下御史問,又以鎮巡官或不宜于本鎮,命兵部同吏部議更置之。”(《明穆宗實錄》卷38,隆慶三年十月甲辰)[4]
隆慶三年大同失事一案的處置引起較大反響,除兵部與司法機關外,言官、閣僚也紛紛發表意見,最終皇帝面對輿論壓力,選擇給予失機邊將一定的懲罰。由此可見,對于九邊武官犯罪的審判不僅屬于法律體系,還牽扯監察、輿論等多重體系。明朝的各種權力因素紛繁復雜,交織在一起,或促進或阻礙,從不同方面影響著軍事司法實踐的運行。
因軍事形勢所迫,文臣要員紛紛就防御戰略各抒己見、為皇帝獻計獻策,明初以來便不鮮見,至中后期逐漸形成了“談兵”之風:“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對兵學的熱情甚至超越了對詩文的熱情,其中還夾帶有彰顯風雅的色彩。”[17]文臣對九邊的關注,不僅包括時政軍情、用兵部署,還涉及九邊用人、武將優劣等各個方面。除了在某一案件中對九邊武官施加輿論壓力外,文臣對功過評定的標準亦產生一定影響,并形成了不同看法。
一種看法為“使功不如使過”。如分守遼陽副總兵都指揮使孫文毅坐守備不設當死罪,巡撫都御史張鼐則引用宗澤成就岳飛之事,認為孫文毅雄健驍勇、武藝精絕,為一時將才,當給予立功贖罪的機會:“宋岳飛犯法將刑,宗澤奇之,使立功贖罪。今遼陽賊巢遍野,聲息不絕,殺此壯士,誠為可惜,且使功不如使過,文毅系于囹圄已三年,若獲再用,必有后效。乞不為常例釋送總兵處聽調領軍,如遇賊能斬獲首級五顆者,宥其死,或立奇功破賊全勝,則仍復其原襲祖職。”由于張鼐的保薦,孫文毅被免于發遣,以平虜衛軍身份存留本處聽用,候有功如例升賞(《明孝宗實錄》卷200,弘治十六年六月辛亥)[4]3716。劉健上疏陳奏安邊之策,其中亦提到:“各處守邊官員,有因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為事罷黜者,中間多系曾經戰陣,諳練邊事之人。合無令兵部通查,送赴軍前立功,其有才堪領軍者,就領軍殺賊。”(劉健:《御虜安邊事宜疏》)[1]卷52,407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功不掩過,須按律處置。如胡世寧引用《大明律》中“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除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理遠近,發各衛充軍”的記載,提出不應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又如針對法司所奏征討官當論功定議的處理辦法,胡世寧表示反對,其引用明太宗的敕諭提出賞罰分明的重要性:“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胡世寧又認為:“今論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太祖定律之意。”(胡世寧:《備邊千策疏》)[1]卷136,1354
守邊、征戰的武官是否可以按照軍功論賞罰,而忽略其他罪行,明代文臣士大夫并未達成一致。有些守邊武官在文官的幫助下獲得了重新立功升遷的機會,但亦有武官在文官的非議中被罷官。如陜西莊浪衛土官指揮魯氏家族,據徐階所述,可知其由盛轉衰即與文官誹謗有關:“臣聞魯姓系陜西莊浪衛指揮,其家舊有名于西邊,號曰魯家人馬,后因人疑之謗之,不敢收養家丁,漸亦衰弱。近年有魯聰者,任古北口參將,頗驍勇,被劾革任。凡武官之善戰者,多粗率,而撫按、兵備等專要責其奉承,一不如意,便尋事論劾,輕者罷官,重者問軍問死。”(徐階:《答重城諭二》)[1]卷244,2548明代中期以后武官地位逐漸下降,在朝堂之上漸失影響力,在邊境亦處處受到制約,處境可謂艱難。
余 論
古語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體現了將官的軍權之大,君主亦因此對將官有所忌憚。明朝邊將無調兵之權,在中央要聽從兵部部署,在地方則要服從總督、巡撫調配,事權被一再分割。從九邊官員的陸續增設可以看出邊將逐漸受制于各類文官的情況:“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于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后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伍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后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贊理軍務之文,于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事權輕,而各鎮軍馬難于調遣,又設總督都御史,如薊遼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計,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督矣。至于失事之后,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該道委府縣官……至于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吳時來:《目擊時艱乞破常格責實效以安邊御虜保大業疏》)[1]卷384,4165
黃宗羲總結明代文臣將兵制度曰:“有明雖失其制,總兵皆用武人,然必聽節制于督撫或經略。則是督撫、經略,將也,總兵,偏裨也。”[18]明代在九邊施行以文馭武的統治策略,欲使各方協同防御,然而現實中卻往往互相掣肘,妨礙邊務。馮琦在給呂坤的書信中即言:“且如陜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略大臣……昔之總督,即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為重,久之亦為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煩,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眾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于此。”(馮琦:《答呂新吾方伯》)[1]卷440,4827兵部尚書毛伯溫亦評論曰:“屬者陛下軫疆圉之急,總督大臣并置,文武謀勇相資,事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閫外之臣彼此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師,最忌中制,若往復奏請,必致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后,可慮者三。總督大臣得專生殺,諸將往往不遵約束,遂求故引去,即加以罪,亦所甘心,可慮者四。”有鑒于此,毛伯溫奏稱“臣請特詔文武二臣同心決策,共濟時難,軍中一切機宜,不從中覆,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明世宗實錄》卷273,嘉靖二十二年四月丁酉)[4]5366,世宗嘉納之。
針對武官與文官之間的矛盾,除了勸誡九邊文武大臣和諧相處外,明人還從制度設計的角度想方設法,試圖解決因官員掣肘出現的弊端。一種辦法為支持文臣將兵,加重總督之權,進一步完善總督巡撫制度,使事權歸一。如趙伸提議:“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并也。且用兵之道,妙于變化,主于奇正,彼己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趙伸:《籌邊疏》)[1]卷234,2459
另一種辦法為使責有所歸,施行分責制度。如汪道昆對九邊主要官員的職責進行了詳細劃分:“臣惟分布調度,理餉程功,總督事也;繕邊防、固城守,實行伍、輯士民,巡撫事也;明間諜、謹烽堠、精教練、嚴約束、勒部曲、審機宜,料敵制勝,總兵事也;慎出納,給餉以時,戶部分司事也;足食利兵,巡工訓士,慎聽閭伍之訟,毋失其和,兵備事也;治一旅之師,當一面之守,守必固,戰必勝,諸將事也。凡此則皆功能相濟,體統相維……故臣請自督撫而下,各分責成:調度失宜,功罪失實,罪在總督;完繕不豫,罪在巡撫;虜形不察,軍政無紀,戰陣無勇,罪在總兵;芻餉不給,致失機事,罪在戶部分司;信地不嚴,專責不舉,罪在監司部將。”(汪道昆:《薊鎮善后事宜疏》)[1]卷337,3609
上述兩種方案從不同角度,針對九邊軍權運行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建議。然而事實上,文臣統兵的趨勢越演越烈,分權制衡的態勢達到了一個又一個高峰。守邊將官不僅受到兵備道、巡按御史、都察院、兵部等機構與官員的監督與考核,還要受到來自朝野包括言官、其他文人士大夫的輿論壓力。邊將事權雖被削弱,責任卻未減輕,一旦失事,或所轄軍官出現失誤,則要承擔失誤軍機之責,隨之而來的便是各種彈劾。左都御史吳時來認為,邊方失事只怪罪于將官顯然不妥:“總兵官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于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于此,誠非事體。”(吳時來:《目擊時艱乞破常格責實效以安邊御虜保大業疏》)[1]卷384,4165
在以文馭武的政治環境下,“武職多要仰仗文臣的垂青與庇佑方能在軍中立足”[17],總督、巡撫、鎮守內官具有保奏之權,可使犯過武官減輕甚至避免處罰。如西安左衛指揮使楊宏最初“以失機問擬充軍”,總制秦纮為之論辯,后又薦其知兵練事、才任統馭,故特宥之,降二級為指揮僉事(《明武宗實錄》卷4,弘治十八年八月壬申)[4]139。可見,對于九邊武官的司法約束與實踐,因政治因素的影響出現了較多的不確定性;邊將功過的評定以及是否能夠以功抵過,一定程度上掌握在皇帝與朝臣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