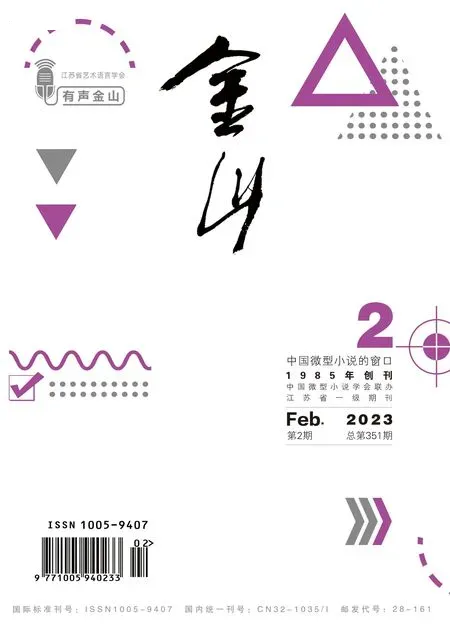啼笑皆非的兩全其美
湖南/王臘忠
舌系帶過短是否需要手術,什么時候適合手術,一千個專家就有一千種說法。而我作為有30多年工齡的口腔科醫(yī)生,根據臨床經驗總結和現實需要考量,認為舌系帶手術應該成為一種常規(guī)手術,越早越好,無年齡限制,既能改善舌的運動度,又可卸下家長的擔憂,一舉兩得。沒有牽絆的舌就像一匹脫韁野馬,怎能不巧舌如簧,口若懸河。
從醫(yī)這些年,遇到過很多疑難雜癥,舌系帶修整術于我當然不在話下。而就是這個我做過無數次,而且從心里認為很簡單的小手術,差點成為我平順醫(yī)路的一個埂,幾乎創(chuàng)造了一個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患者馬奮一家和我算是老朋友了。她老公是本市知名企業(yè)家,哥哥是市級領導,女兒已在北京安家落戶。在來我們醫(yī)院住院之前,她已經因為右舌緣反復潰爛疼痛去北京一家大醫(yī)院做了門診活檢手術,診斷為舌部黏膜不典型性增生,建議行原發(fā)灶擴大切除手術,據說已花費六萬多元。不過我覺得有點夸張,一個門診活檢而已,就算北京專家水平高超,也不至于貴得這么離譜,估計七七八八連來去的路費和專家“慰問費”都算上了。
因為我工齡長、職稱高,平時又喜歡舞文弄墨,在我們這個四線城市還算小有名氣,且她老公以及哥哥我都熟悉,最后她還是選擇回家鄉(xiāng)做手術,一來人熟好辦事,二來方便實惠一些。為解除她的擔驚受怕,顯示鄭重其事,我們特意邀請省城數一數二的口腔頜面外科教授過來主刀。
手術室里,無影燈下,一位來自省城的口腔科教授、一位本市知名教授、一位高年資主治醫(yī)師、兩位麻醉科教授、兩位副主任護師組成的豪華天團閃亮登場。全麻起效后,不到20分鐘手術就做完了。手術細節(jié)不再贅述,真是沒啥可以大書特書的,就像我們穿上盔甲,拿起武器,敵人卻不戰(zhàn)而退,這樣的勝利,心里總有些許的不甘和失落。
一個舌部不典型增生腫物,頂多也就算癌前病變,只需要行原發(fā)灶切除及拉攏縫合,根本用不著做皮瓣轉移及頸部淋巴結清掃。手術完成之后,大家談笑風生,意猶未盡——這么大的陣容出征,不至于這么“小兒科”吧?我們總感覺哪里不對,遲遲沒有卸下裝備。省城來的老教授再一次走到馬奮身邊,掰開她的嘴,用探照燈似的眼睛在她嘴里掃射,發(fā)現她的舌系帶超短,連連嘆息這么多年講話受限,表達不清晰,患者居然沒有察覺。隨后,我們趁她全麻未醒干脆做了舌系帶延長術,免得以后在門診做還得局部麻醉,幾分鐘就完成了。一口氣完成兩個手術,并且沒有增加病人的痛苦和額外負擔,我們心里也就釋然了,成就感妥妥地回來了。
一周后,馬奮出院,此時傷口已基本愈合,只是還有點局部潰瘍,我叮囑她用康復新含漱,安心等待恢復。一個月后,我正在門診忙得不亦樂乎,馬奮怒氣沖沖跑了進來,說整個舌頭都不舒服,有嚴重受壓感,我仔細檢查之后才明白,她的整個牙床向口腔內側傾斜,且還有部分牙齒參差不齊。先前舌系帶短,舌頭運動受限不靈活,講話也是輕聲細語,所以感覺不明顯,現在舌系帶修剪后,舌頭可以天馬行空,無拘無束,但因為牙齒問題處處碰壁,自然不適應。她來找我討說法了。
好在這個手術不是我做的,好在都是熟人,沒有鬧。不過從此以后,我也就沒有安生日子過了,甚至一度徘徊在深淵的邊緣。我在小心翼翼給她矯正牙齒的同時,還要接受她無休無止的咨詢、質疑、質問,不分場合、不看時間,讓我一度對職業(yè)價值產生了懷疑。
我本從事頜面外科專業(yè),不太擅長牙齒矯正,現在要給一位年近五旬的女性做隱形矯正,無疑攤上大事了。好在有同事和廠家協助,技術層面沒有問題。最難過的就是每天要回答她的N次提問,忍受她的N次埋怨,加之她本就處于一個女性容易敏感的年齡段,況且人家是大戶人家的大小姐,我只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對于馬奮,我的技術和耐心可以說發(fā)揮到極致,從她滿面冰霜到笑靨如花,我苦捱了兩年。有時候,感覺自己就是病人的一個容器,盛著快樂,盛著悲傷,而自己的悲傷和快樂卻沒有導管流出。當然,我也得到一個意外的驚喜,為了更好地給馬奮進行情緒疏導,我自學了《心理學》等多門課程,竟然輕而易舉拿到了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證。
舌系帶過短到底要不要行修剪術,這把雙刃劍讓我再度陷入迷惘:張揚或者保守,傾吐或者隱忍,敬畏亦或放任。好像只有一個答案:醫(yī)者仁心,溫柔敦厚。“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