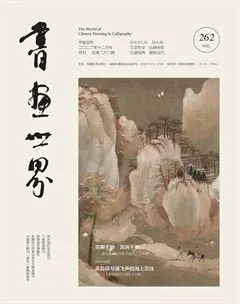沛澤劍氣開紫云
田秉鍔

“以文會友”,語出《論語·顏淵》的“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章開篇,即引曾子語,并無自炫之意。在我,僅僅是表達(dá)了身處沛縣文化群體的自幸與自珍。“文”,是個(gè)頗為寬泛的概念。在曾子眼里,凡“五經(jīng)”“六藝”之道,皆為“文”;而在我眼里,凡“文學(xué)”“藝術(shù)”之道,皆為“文”。于是,在沛縣大文化的“文友”之會中,我認(rèn)識了紀(jì)偉。這種“認(rèn)識”是那么自然而順?biāo)欤质悄敲从H近而玄遠(yuǎn),在了無功利、了無掛礙的淡然一笑中,我以直觀的感受面對紀(jì)偉先生的書道和書品、人道和人品。
初識紀(jì)偉和他的書法是在2000年舉辦的一次書畫展上,而再一次近距離欣賞紀(jì)偉書法則是在2010年之春的“劉邦文化萬里行”活動中。這次相遇仍然是無須言說、淡然一笑,仿佛穿越了五百年宿命,這讓我相信相識即是善緣。略去一切燈光、布景的烘托,我認(rèn)識的是一個(gè)單純的書法家紀(jì)偉,是一個(gè)在筆墨點(diǎn)畫中釋放自我而又找回自我、呈現(xiàn)自我而又超越自我的紀(jì)偉。此外,還需要做什么理性的抽繹嗎?人們也許會說,讓認(rèn)識在“第一印象”停步總免不了有幾分朦朧吧。而自信的判斷總是堅(jiān)持:連“第一印象”的認(rèn)可都無法立足,何以再有“相期百年”的祈盼呢?這正契合我“君子交”的理念。“君子交”頗有“中庸”之風(fēng)。中之不偏,庸之不倚,使我們在不親不疏的觀照中更易受到藝術(shù)純粹的感染。近之則親,親則易褒;遠(yuǎn)之則疏,疏則易貶。而褒貶失度正是這個(gè)“粉絲”時(shí)代的通病。后來,承孟昭俊先生指教,我便分外注意紀(jì)偉的書法動向。
紀(jì)偉,1972年11月生于沛城一個(gè)頗有文化氛圍的家庭。民國時(shí)期,其曾祖便在沛城中心的鼓樓旁邊開有一家文房四寶與古玩店,家風(fēng)傳承,紀(jì)偉自幼即喜于藝事。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始,孟昭俊先生在沛縣文化館舉辦書法教學(xué)班,紀(jì)偉聞訊,報(bào)名聽課,遂登堂入室。1996年,他畢業(yè)于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書法大專班,現(xiàn)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沛縣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自1996年參加全國首屆行草書展至今,紀(jì)偉已參加省級以上全國書法、篆刻大賽數(shù)十次,獲全國各級大獎(jiǎng)三十余次。瀏覽日多,印象日深,在“第一印象”的好感之外,我又心生了一份驚詫的悸動。

每每讀紀(jì)偉書法,我總能感受到劍氣橫空的浩然,自然而然聯(lián)想起杜甫《劍器行》中的名句:“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 如羿射九日落,嬌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這只是一種個(gè)人化的藝術(shù)聯(lián)想。因?yàn)椋P的輕柔與鋼劍的峻利是無論如何也搭不上茬的啊!但是,我分明已感受到紀(jì)偉書法撲面的劍氣弧光和那劍氣弧光背后所屏蔽的書劍情懷。這在書風(fēng)俗媚、書魂飄搖、書道陵替的今天,任何個(gè)別書家的探索或都可歸入“非主流”的獨(dú)唱。而從“書在江湖”“書在民間”的視角眺望,如紀(jì)偉這樣“獨(dú)唱”的書家,在中國或許正是沉默的多數(shù)。一旦擺脫了“工程文化”的誘導(dǎo)或“名家分爨”的排序,中國書法新時(shí)代的自由與輝煌定然是由今天這沉默的多數(shù)來書寫。于“書道”內(nèi)悟出“劍道”,或于“劍道”內(nèi)悟出“書道”,并不是欣賞者的飛狐夜鳴。因?yàn)楣湃艘苍鴷r(shí)不時(shí)將“書”與“劍”相提并論。王實(shí)甫《西廂記》一本一折,張生出場,即自報(bào)家門曰:“小生書劍飄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書指書籍,劍指寶劍,連用則指讀書做官、仗劍從軍。而最有力的例證則見于《史記·項(xiàng)羽本紀(jì)》:“項(xiàng)籍少時(shí),學(xué)書不成,去學(xué)劍,又不成。項(xiàng)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xué),學(xué)萬人敵。”當(dāng)項(xiàng)羽將“書”與“劍”對立起來時(shí),“書家”與“劍客”便分別在對方的技藝?yán)锊蹲降搅顺錾袢牖撵`感。唐代,張旭曾與裴旻、吳道子相遇于洛陽,各顯其能。裴旻舞劍一曲,張旭草書一壁,吳道子繪制一壁,時(shí)人認(rèn)為是一日獲睹“三絕”。而唐文宗則在這江湖的“三絕”之外,特降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書道”與“劍道”結(jié)緣,淺言之,僅是書法史的一段神奇佳話;深思之,則是天人感應(yīng)、內(nèi)圣外王之學(xué)的一種顯現(xiàn)。須知,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操“管”與仗“劍”,僅為“器”之差別,于“道”則為一也。

紀(jì)偉學(xué)書,師事泗上孟昭俊先生。由漢隸入門,上臨甲骨籀篆,下習(xí)唐楷行草,尤傾心研磨張旭、懷素諸家碑帖,積二十年寒暑,最后結(jié)撰于老隸而揮灑于行草。這正好玉成了他拙巧相輝、動靜相宜的二元風(fēng)格或雙峰優(yōu)勢。展卷生輝,煙霞滿紙,觀者每于俊逸中見其剛勁、于舒放中見其收納、于開合處見其圓融、于掩映中見其連貫,而靈光一閃的則是其抑之愈揚(yáng)的書劍情愫。觀其作于五年前至去歲的《有酒須邀客飲,無詩且抱書眠》《國色天香獻(xiàn)瑞,富貴花開呈祥》《憑欄看遠(yuǎn)岫,倚石聽流泉》《漢之源楚風(fēng)漢韻茶香里,龍飛地虎嘯龍吟青史中》等隸書聯(lián)句作品,多有本色,而漸趨老健蒼雄;觀其作于八年前至三年前的《天高云淡》《大風(fēng)起兮》《學(xué)如逆水行舟》等草書條幅作品,蛻變升華之跡尤為顯著,運(yùn)筆濡墨,如風(fēng)行水上,行其當(dāng)行,止其當(dāng)止,盡得“紅雨隨心”“青云著意”之妙。如果將《一弦飛矢鳴畫戟,十萬雄兵卸征衣》聯(lián)作為紀(jì)偉草書成熟期的標(biāo)志性作品,則可以判定:近兩三年來,紀(jì)偉草書真正進(jìn)入了揮灑由我、心外無物的“自由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