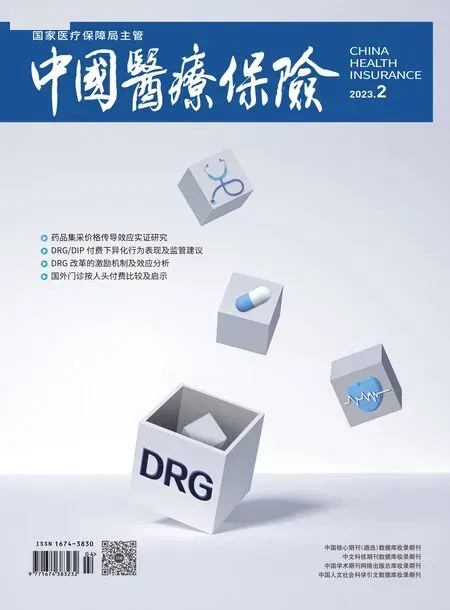中西部農村地區醫療救助基金緩解因病致貧的非線性關系研究
——基于PSTR模型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
李建國 趙玉梅 梁詩童
(廣州中醫藥大學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 廣州 510006)
1 引言
社會醫療保險的財政投入在反貧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已形成社會共識。目前我國各地醫療救助基金有限,實質的反貧困效果無法彰顯。隨著我國財政收入逐步增加,醫療救助基金對因病致貧家庭的扶貧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因此,加強醫療救助基金在因病致貧家庭中的減貧作用是緩解因病致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必要舉措。
當前,我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在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上,都是東部地區在反哺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在充分利用大病醫療保險解決因病致貧國際難題的同時,也需要發揮醫療救助基金在緩解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因病致貧中的作用。中西部地區醫療救助基金如何支付才能發揮最大的反貧困效率,有待進一步研究。
醫療救助基金具有實質的反貧困效應,然而世界貧困史表明,醫療救助基金的持續投入所帶來的減貧效果并不會持續、穩定地增加,投入到一個臨界點后,其減貧效果逐漸弱化。
本文應用2010年—2018年中西部地區省級農村醫療救助基金數據,利用面板平滑轉換模型(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PSTR)尋找發生非線性轉換的閾值,探討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醫療救助基金緩解因病致貧的作用關系及特征,分析結果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 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2.1 理論基礎
PSTR 模型是由Gonzales、Terasvirta 和Dijk[1]開發的一種模型。它比面板閾值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PTR)[2]優越的地方在于平滑在節點處的突變。
本文認為醫療救助基金對中西部農村地區因病致貧家庭的反貧困非線性閾值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救助基金投入規模、家庭的收入能力、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等。對于那些陷入疾病與貧困惡性循環的家庭,較低的醫療救助基金投入規模無法實現穩定脫貧。較低的醫療救助基金投入規模會導致發生二次貧困以及跌入貧困陷阱的家庭增加,使得未來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去進行救助,而且會一定程度上抑制市場有效需求,阻礙宏觀經濟更有效的增長。
因病致貧的家庭越多,國家層面縮小收入差距、緩解相對貧困的目標就越難以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醫療救助基金投入越多,其反貧困的效果就會越顯著。如果受到資金資助的那方形成了對醫療救助基金的依賴,其反貧效果反而會因為其他指標和激勵機制的下降而跌入低效率區間。因此,本研究利用PSTR 模型測算發生非線性轉換的閾值很有必要。
2.2 模型構建
本文建立的模型是:
(1)式中yit代表各省2010年—2018年的貧困發生率,i=1,2…N;t=1,2…T,yit為被解釋變量;μi代表個體固定效應;β0,β1為回歸系數,γ 為用于決定轉換速度的平滑參數,εit代表隨機擾動項;xit代表自變量和控制變量,自變量是每個中西部省份每個年度的醫療救助基金額,包括資助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醫療救助基金和資助門診及住院醫療救助的基金;xit是含有時變外生變量的k 維解釋變量;控制變量包括:(1)各省2010年—2018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Rate,RUUR);(2)城鎮化水平(Urbanization Level,UL)兩個變量;εit為殘差項。G(qit;γ,c)是關于轉換變量qit的值域為[0,1]的有界連續函數,qit可以是xit向量的組成部分或組成函數,也可以是一個不包含xit的外生變量。
本文旨在研究中西部農村地區醫療救助基金的反貧困效應,因此選取各省貧困發生率作為因變量,選取各省醫療救助基金額作為自變量,選取各省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作為轉換變量。G(qit;γ,c)為關于qit的連續有界(0 ≤G(qit;γ,c)≤1)的轉換函數,其Logistic函數的設定形式為:
(2)式中,c 為轉換發生的位置參數,也稱門檻水平,決定轉換發生的位置;γ 為平滑參數,也稱斜率系數,決定轉換的速度或調整的平滑度;m 表示轉換函數G(qit;γ,c)含有的位置參數的個數,通常取值為1 或者2。當m=1 時,轉換函數G(qit;γ,c)含有一個位置參數:
模型中轉換函數可以但不必相同,是否適用于PSTR 模型需要進行截面異質性檢驗,即判斷模型是否存在非線性效應。若異質性存在,則估計的就是PSTR 模型,否則估計的就是線性固定效應模型。即檢驗H0:γ=0 或H1:β1=0 一般在γ=0 處對(1)式運用泰勒一階展開式解決存在未能識別的參數而導致檢驗變得復雜的問題,在輔助回歸模型中,檢驗參數聯合約束為零的,與H1等價的假設H02,然后在輔助回歸模型中構造漸進等價的LM(拉格朗日乘數統計量)、LMF(F 統計量)進行檢驗。
其中,SSR0為原假設(即線性假設)的面板殘差平方和,SSR1為備擇假設(即PSTR 模型)的面板殘差平方和。在原假設下,LM 檢驗統計量服從x2分布,而F 檢驗統計量服從F(1,TN-N-1)分布。如果檢驗拒絕原假設,則表明截面異質性存在,模型存在非線性效應。接下來進行剩余非線性檢驗,即檢驗是否存在唯一一個轉換函數(H0:γ=1)或者至少存在兩個轉換函數(H1:γ=2),與前面的分析類似,同樣構造輔助回歸函數,利用LM 檢驗或者F 檢驗考察是否還有“剩余”的體制轉換效應,依次類推,直到不能拒絕原假設為止。
PSTR 模型的參數估計主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的組內回歸和非線性最小二乘法(Nonlinear Least Square,NLS),而平滑參數γ 和位置參數c 的確定則采用模擬退火法或網絡搜索法進行迭代估計,其中使殘差平方和最小的估計即為最優估計:
2.3 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考慮到2018年后我國很多中西部省份的貧困發生率很低,本研究模型需要連續、平衡的面板數據,且對數據的質量要求較高,本文選取《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中23個省2010年—2018年共9年的面板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由于2018年東部地區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8 個發達地區農村貧困發生率統計上不顯著,因此,本研究未納入這些地區。東部地區的河北和海南無論從GDP 總量還是從人均GDP 來看,都處于相對不發達地區水平,甚至落后相當部分的中西部省份,因此也納入分析。
本文選取的主要變量如下:
(1)以貧困發生率(Poverty Headcount Ratio,PHR)作為因變量,用PHR 表示,指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絕對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300 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絕對貧困標準。本文各省的貧困發生率數據來自于歷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2)以中西部各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PCDI)占當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作為轉換變量,用PCDI來表示。
(3)以中西部各省人均醫療救助基金(Per Capita Medical Assistance Fund,PCMAF)與對應年份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自變量,用PCMAF 來表示。本文各省的醫療救助基金額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基本醫保的人均籌資額來自歷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
(4)在控制變量方面,分別以中西部各省城鎮登記失業率(RUUR)和城鎮化水平(UL)作為控制變量。城鎮登記失業率(RUUR)與農村地區貧困之間的傳導關系非常密切,因為農民在家務農有土地,土地收入變化不大,但到城鎮務工每年收入變化很大,隨著中西部各省城鎮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變化,而且與城鎮登記失業率密切相關。城鎮化水平(UL)指城鎮人口占城鄉總人口的比例,它可以衡量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趨勢,隨著居民向更高效率和更高文明程度的城市轉移,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會減少。表1 是各變量的描述統計情況。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3 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首先對面板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采用LLC 檢驗、PP 檢驗和ADF 檢驗得出各變量對數具有平穩性特性。然后進行協整檢驗,發現它們之間具有長期協整關系。
3.1 線性檢驗與剩余非線性檢驗
利用MATLAB 軟件對模型進行了非線性檢驗。表2 給出了線性檢驗與非線性檢驗結果。對于原假設(H0:γ=0),檢驗統計量LM、LMF、LRT 均能在1%的水平上拒絕線性關系的原假設,說明醫療救助基金緩解因病致貧具有明確的非線性特征。而對于原假設(H0:γ=1),模型的檢驗統計量都接受原假設,而不接受備擇假設(H1:γ=2),說明該模型存在兩個機制的非線性模型,醫療救助基金和因病致貧的貧困發生率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從剩余非線性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三個檢驗統計量均不能拒絕γ=1 的原假設,因此最優的轉換函數個數為1,適合采用含有單個轉換函數的PSTR模型。

表2 線性檢驗與非線性檢驗結果
當r=1 時,由于m=1 和m=2都接受剩余非線性檢驗的原假設,因此需確定位置參數究竟是m=1還是m=2。 根據AIC 和BIC 準則,以及表3 的結果,當m=1 時,AIC 值和BIC 值都小于m=2 時的對應值,而且模型更簡單,因此位置參數選擇m=1 更為恰當。

表3 位置參數個數的確定
3.2 非線性模型的參數估計
本文選用非線性最小二乘法(NLS)估計PSTR 模型的未知參數,所得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估計結果,PSTR 模型發生非線性轉換的位置參數的值為0.6714,由于是對數模型,真正的位置參數為exp(0.6714)=1.9570,即模型的門限值為195.70%,說明各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當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195.70%時,發生了非線性轉換。其中,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70%的樣本有195 個,占所有樣本比例的94.20%;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70%的樣本有12 個,占所有樣本比例的5.80%。模型在低體制與高體制的平滑參數為10.8617,說明它們之間的轉換是緩慢并且平滑的。本文將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當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195.70%的地區稱為低收入地區,反之稱為高收入地區。

表4 PSTR模型估計結果(NLS)
4 結論及啟示
本文在非線性框架下構建PSTR 模型,對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醫療救助基金緩解因病致貧的非線性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醫療救助基金對農村因病致貧具有顯著的非線性關系和雙門限非對稱特征。雖然我國在2020年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是由于這種非線性關系的存在,對各種救助政策進行細化的政策設計并沒有完成,本研究在目前仍具有普遍的意義。
4.1 在門限值前后,醫療救助基金對緩解中西部農村地區因病致貧具有顯著性差異
通過門限值的計算發現,最優門限值在195.70%。在門限值前后,醫療救助基金對緩解中西部農村地區因病致貧存在顯著性差異。在收入低于門限值的中西部地區,醫療救助基金的反貧困效果不顯著;而在收入高于門限值的中西部地區,醫療救助基金具有很強的反貧困效應。
與此同時,在收入低于門限值的中西部地區,城鎮就業率與反貧困存在替代效應,即城鎮就業率高,貧困發生率低;城鎮就業率低,貧困發生率高。而在收入高于門限值的中西部地區,城鎮就業率與反貧困是互補效應,即城鎮就業率高,農村貧困發生率高;城鎮就業率低,農村貧困發生率低。從城鎮化來看,收入高于和低于門限值的地區,其城鎮化水平對反貧困均具有顯著影響,但收入低于門限值的地區,影響系數更大。
4.2 收入高于門限值的中西部農村地區,醫療救助基金的反貧困效果好
在中西部相對高收入的農村地區,醫療救助基金比例對貧困發生率的影響系數為-13.46%(-30.157%+16.6983%),也就是醫療救助基金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每提高1 個百分點,會帶來地區貧困發生率下降13.46 個百分點,表現為醫療救助基金對因病致貧具有良好的反貧困效應。主要原因如下。
(1)中西部低收入地區主要采用低標準廣覆蓋的辦法,多年的醫療救助基金的標準變化不大;而中西部相對高收入地區,醫療救助基金額的增加主要反映在人均補助標準的提高。(2)越是相對貧困的地區,投入的醫療救助基金的規模和人均值越小,存在相對巨大的因病致貧所需的資金缺口,其反貧困功能非常有限;越是相對富裕的地區,醫療救助基金的規模比較大,能夠起到一定的醫療反貧困作用。(3)越是貧困的中西部農村地區,政府的財政能力越弱,需要保障的方面越多,政府通過保險、就業等形式投入財政資金脫貧,效果可能更為明顯,而單純的醫療救助基金的轉移支付,可能會形成投入多、見效少的局面。由于資金有限,醫療救助基金過度的給付會使得地方財政陷入困境。(4)越是貧困的地區,其貧困發生率越高,多種貧困、復合貧困越明顯,政府需要投入的領域會越多,醫療救助基金所緩解的反貧困還不是政府關注的主要領域。
4.3 城鎮登記失業率對中西部農村地區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在不同收入地區也有巨大差異
從表4 來看,收入低于門限值的地區,城鎮登記失業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當地農村的貧困發生率將會升高5.75 個百分點。而對于收入高于門限值的地區,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1 個百分點,將會使得貧困發生率輕微下降0.59 個百分點(-6.3415%+5.7481%)。 主要原因如下。
(1)中西部低收入地區農民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周邊城鎮的務工收入,如果城鎮登記失業率越高,說明當地農民在城鎮的就業機會下降,會提高貧困的發生率。(2)中西部相對高收入地區,農村本身的產業經濟比較發達,城鎮失業率提高,將會促使在城鎮就業的農民返鄉和投資,反而會推動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使得貧困發生率下降。說明在相對高收入的地區,城鎮就業和農村反貧困產生了互補效應;而在低收入地區,城鎮就業和農村反貧困產生了替代效應。
4.4 城鎮化率對中西部農村地區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在不同收入地區影響有差異,但差距較小
從表4 來看,在收入低于門限值的地區,城鎮化率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農村的貧困發生率,城鎮化率每上升1 個百分點,貧困發生率下降1.68 個百分點。而在收入高于門限值的地區,城鎮化率提高的反貧困作用沒那么大,城鎮化率每提高1 個百分點,貧困發生率下降1.45 個百分點(-1.6807%+0.2306%)。 說明在中西部低收入地區,城鎮化率提高的反貧困作用更大;在中西部相對高收入地區,城鎮化對反貧困的影響在減弱。城鎮化率的提高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是密切相關的,沒有工業化就不會有城鎮化。中西部落后地區,仍然要加大力度推行工業化戰略,才能提高城鎮化水平,繼而降低農村貧困發生率。
只有在收入超過閾值門限的中西部農村地區,醫療救助基金才能夠起到顯著的反貧困效果。這個政策含義就是,中西部農村低收入地區反貧困的主要作用機制不是對單個的貧困救助機制進行改良,而是要針對地區的系統性貧困提供方案,讓整個地區的平均收入增長上去,才能通過宏觀政策及經濟的外溢效應大規模地降低本地區的各類貧困發生的水平及比例。所以,我國中西部農村落后地區應使用系統的反貧困計劃替代單一的醫療救助基金反貧困計劃,細化整體的運作模式[3],將產業和金融扶貧、醫保扶貧、醫療救助扶貧看作一個相互支撐的系統,優化制度組合并強化醫療救助核心地位[4],才能真正取得實效。而對于收入超過閾值門限值的中西部農村地區,普通性的扶貧政策難以取到很好預期效果,需要制定包括醫療救助基金等在內的專項扶持政策[5-10],扶貧效果會更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