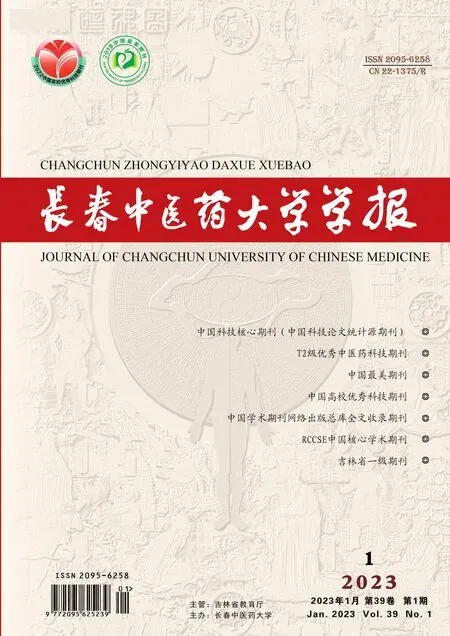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流行現狀、耐藥機制及抗菌藥物診療進展
武亞鑫,趙 敏,李浩然,王 珂
(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長春 130041)
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KP)是腸桿菌科克雷伯氏菌屬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其所致疾病占克雷伯氏菌屬感染的95%。碳青霉烯類抗生素是目前治療耐藥細菌感染的臨床一線藥物,但隨著抗生素的過度使用,出現了耐碳青霉烯類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CRKP感染影響患者的精神狀態,降低患者生活質量,嚴重威脅患者的預后,研究[1]表明,住院患者CRKP感染后的死亡率達35%,CRKP的耐藥機制尚未完全明確,探尋CRKP的耐藥機制及高危因素已成為研究的熱點。本研究擬對CRKP的流行現狀、高危因素、耐藥機制及診療進展進行概述。
1 CRKP的流行現狀
KP已成為臨床常見的致病菌,它可以引起住院患者的肺炎(HAP)、菌血癥、尿路感染和手術部位感染[2],隨著各種耐藥菌的不斷出現,1997年MACKENZIE等[3]首次報道了CRKP,在之后的數十年中出現了CRKP的全球傳播,美國已將CRKP列為21世紀最具威脅性的病原體之一,CRKP已成為美國發現的最常見的耐碳青霉烯腸桿菌(carbapenem-resistantent erobacteriaceae,CRE) 菌種,HAN等[1]進行的一項納入3 846例KP菌株的回顧性研究發現KP的總碳青霉烯耐藥率為24.6%,經過分析發現美國LTACHs網絡中近25%的KP臨床分離株是CRKP。CRKP還在世界其他地區流行,包括中國、以色列和一些南美洲國家。歐洲范圍內的一些國家也相繼報道了CRKP的流行,特別是希臘和意大利,從2005-2011年,希臘KP對碳青霉烯類抗生素的耐藥比例從28%上升到68.2%[4]。在我國,2006年WEI等[5]首次報道了CRKP,而在這之后的數年中,CRKP在我國的檢出率也不斷升高,在過去12年中,CRKP的臨床分離率從0.9%上升到19.9%[6],有調查[7]顯示2019年河南省及上海市CRKP檢出率最高,分別為 32.8% 和 28.7%,西藏檢出率最低,為0.6%,2019 年全國兒童醫院、三級醫院及二級醫院CRKP檢出率分別為 14.0%、11.6% 及5.5%,2019 年全國重癥醫學科患者CRKP檢出率最高,為23.0%,高于住院、急診及門診患者。根據CHINET中國細菌耐藥性監測結果顯示2015-2018年KP對亞胺培南的耐藥率分別為15.6%、16.1%、20.9%、25.0%,對美羅培南的耐藥率分別為14.4%、18.8%、24.0%、26.3%,而在2005年對亞胺培南和美羅培南的耐藥率僅為3.0%和2.9%,耐藥率上升幅度超過8倍,同時從2015-2017年肺炎克雷伯菌對厄他培南的耐藥率分別為11.2%、11.7%、14.4%[8-11],其在革蘭氏陰性桿菌中的檢出率占比也在逐年升高。
據統計,到2050年抗生素耐藥性感染將導致全球每年1 000萬人死亡,其中最嚴重的威脅是CRE,其中CRKP在成人中的感染致死率為40%至50%[12],在新生兒血液感染中的死亡率可高達75%[13]。自CRKP在全球流行以來,序列類型ST258已成為北美、拉丁美洲和歐洲最流行的CRKP克隆類型,而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ST11是優勢克隆,占CRKP的60%[14]。超強毒力肺炎克雷伯氏菌(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HvKP)株最早于1982年在臺灣發現[15],后來美國、澳大利亞、墨西哥和韓國報道了它的存在[16-17]。HvKP菌株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它能夠在年輕、健康的個人中引起感染,其侵襲力和致死率較高,此外,它還可能引起許多并發癥,包括肝膿腫、壞死性筋膜炎、眼內炎和腦膜炎[18],顧丹霞等[19]在《柳葉刀傳染病》上報道了一起呼吸機相關肺炎的致死性暴發,該事件即由HvKP引起,同時,研究發現HvKP是屬于ST11型的CRKP。不可否認的是隨著CRKP及HvKP的不斷出現,在治療中曾經被認為是治療KP最后防線的碳青霉烯類抗生素可能失去抗菌作用。
2019年末至今,由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SARS-CoV-2)引起的冠狀病毒病2019(COVID-19)在全球范圍內大流行,新冠肺炎患者繼發細菌感染(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s,SBIs)對其預后有很大影響,LI等[20]回顧性研究了2020年1月27日-3月17日在中國武漢協和醫院住院的所有COVID-19患者的資料,發現在1 495例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102例(16.8%)患者有獲得性SBIs,其中近一半(49.0%)患者在住院期間死亡,分離的159株菌株前三位分別為鮑曼不動桿菌(35.8%,57/159),肺炎克雷伯菌(30.8%,49/159)和嗜麥芽窄食單胞菌(6.3%,10/159),其中CRKP分離率為75.5%。另一項來自意大利的回顧性研究[21]發現重癥監護室收治的35例COVID-19患者中有7例直腸拭子中發現CRKP,其中2人在28天內死亡,5人在ICU死亡,CRKP感染性休克相關死亡率為28.6%,且具有CRKP獲得性感染的新冠肺炎患者的住院時間更長,住院死亡率更高,以上數據表明在新冠肺炎感染者中,我們似乎有必要重視CRKP的獲得性感染。
2 CRKP的危險因素
抗生素耐藥性是一種日益嚴重的危機,也是對人類健康的嚴重威脅,一項研究收集了醫院2006-2020年3 054株KP,發現KP菌株亞胺培南、頭孢唑林、慶大霉素、妥布霉素、環丙沙星、頭孢他啶的耐藥率分別由2.33%、27.91%、16.28%、13.95%、18.60%、9.30%上升至12.83%、40.82%、21.57%、25.07%、44.61%、17.78%[22],因此,了解與CRKP感染發展相關的危險因素對于識別高危患者預防CRKP感染非常重要,一項納入6項研究共涉及3 627名參與者的薈萃分析指出,16個危險因素中包括較長的住院天數、ICU治療、既往使用抗生素和接觸碳青霉烯類抗生素與CRKP感染的發生有關[4]。ZHU W M等[23]的研究,選擇2個對照組即碳青霉烯敏感的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sensitive Klebsiella pneumoniae,CSKP)感染的患者和未感染CRKP的患者,CSKP感染與CRKP感染患者,兩項比較發現收治于重癥監護病房、中心靜脈導管、機械通氣、氣管切開、尿管使用、抗生素使用、碳青霉烯類抗生素暴露和氨基糖苷類藥物暴露是感染CRKP的高位因素。識別可改變的危險因素可在預防CRKP感染中發揮重要作用。
3 CPKP的耐藥機制
CRKP的耐藥機制尚未明確,已知的機制有產碳青霉烯酶、高產AmpC/ESBLs酶合并外膜孔蛋白缺失或表達不足、作用靶點的缺失或數量不足、外排泵作用增強、整合子和質粒介導的耐藥、生物被膜的形成、免疫逃逸策略等,其中最主要的機制為產碳青霉烯酶,碳青霉烯酶主要包括A類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酶如KPC,B類為金屬β-內酰胺酶(Metallo-β-lactamases,MBLs) 如 NDM、IMP 及VIM,D類OXA-48碳青霉烯酶及其衍生物。
3.1 產KPC酶
產生KPC的肺炎克雷伯菌通常與侵襲性高風險克隆有關,如序列ST258和ST11。產生KPC的ST258和ST11現已成為美國以及許多歐洲和亞洲國家的流行克隆,而NDM和OXA-48碳青霉烯酶也相繼在各種KP克隆中被發現[13]。KPC主要與轉座元件Tn4401相關,表現出廣泛的地理變異,KPC酶能夠水解除頭霉素類[24]以外的青霉素類、頭孢菌素類、碳青霉烯類、氨曲南等幾乎所有β-內酰胺類抗生素,它可以被阿維巴坦、瓦博巴坦和瑞來巴坦等β-內酰胺酶抑制劑抑制,而克拉維酸和他唑巴坦的抑制作用較弱[25],在CRKP中介導blaKPC-2基因傳播的質粒主要為IncFII,同時除產碳青霉烯酶耐藥基因外,CRKP均含有2~3個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基因如blaCTX-M、blaSHV和blaTEM等,這些耐藥基因的表達,共同導致了CRKP的耐藥。KPC-2和KPC-3是最為常見的KPC,在美國,blaKPC-3是主要的基因類型[26],而在中國,blaKPC-2是最常見的基因類型。KOBAYASHI等[27]的研究發現ST258序列的CRKP可以攜帶編碼膠囊多糖(capsule polysaccharide,Cps)的基因,在世界范圍內的ST258臨床分離株中主要為Cps-1和Cps-2兩種衣殼類型,攜帶有Cps基因的CRKP能夠抵抗中性粒細胞的吞噬作用,從而促進細菌在人體內的播散。BAND等[12]的研究發現在74株CRKP中,85.1%的菌株KPC-2產生陽性,與非ST11菌株相比,ST11 CRKP菌株對blaKPC-2的檢出率較高。
QIN X等[26]的一項為期3個月的前瞻性隊列研究中,對243名ICU患者在入院時和入院之后每周進行一次腸道和鼻咽部肺炎克雷伯菌攜帶的篩查,發現與入院時無肺炎克雷伯菌定植的患者相比,入院時有CSKP定植的患者在ICU期間更容易獲得CRKP定植,且在ICU中ST11-blaKPC-2-CRKP的攜帶率和感染率較高。我國一項研究數據揭示2008-2018年浙江地區CRKP患病率從2.5%上升到15.8%,2018年浙江省報告的耐藥率(CRKP>50%)是中國最高的,特別是ST11-blaKPC-2-CRKP的發病率和耐藥性明顯上升[28]。
3.2 產NDM酶
產NDM的CRKP在南亞國家、中東和巴爾干地區的流行率最高[29],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有零星報告。NDM已在11科60種細菌中鑒定出24個變異體,而在KP中常見的序列為ST11、ST14、ST15[29]。產NDM的細菌通常對青霉素類、碳青霉烯類和頭孢菌素類抗生素耐藥,MBLs不被臨床上可用的β-內酰胺酶抑制劑抑制,在體外可以被鋅結合劑EDTA和二吡啶甲酸以及新型抑制劑如杜洛巴坦、那庫巴坦和齊德巴坦等抑制[30],此外MBLs不能水解氨曲南,所以其對單菌素類抗生素仍敏感。CRKP中的blaNDM基因存在于INCA/C、INCF、INCK、INCH、INCN、INCL/M和INCX等質粒中,而介導blaNDM-1耐藥基因在菌株間傳播的主要質粒類型是INCA/C,與此同時INCA/C質粒上也可以攜帶有其他類抗生素的耐藥基因,例如與氨基糖苷類抗生素耐藥相關的16SrRNA甲基化酶基因RmtA和RmtC,與廣譜頭孢菌素耐藥相關的CMY型β-內酰胺酶基因,及與喹諾酮耐藥相關的QnrA基因,這些耐藥基因可隨著質粒介導的水平轉移在細菌間廣泛傳播。XU等[31]研究報道,從中國杭州血液感染患者中分離的一株CRKP,屬于序列ST11,共發現8個耐藥基因其中包括2個碳青霉烯酶基因即blaKPC-2和blaNDM-1,該CRKP對除替加環素和黏菌素外的所有抗生素均耐藥。LIU等[32]對四川省12家醫院的74株CRKP進行基因組序列分析,其中有26株產B類酶,包括22株攜帶blaNDM,4株攜帶blaIMP,其余48株均攜帶blaKPC-2。SHERCHAN等[33]從尼泊爾住院患者中分離到6株對碳青霉烯類和氨基糖苷類高度耐藥的KP,均攜帶blaNDM-5、blaOXA-181或-232和甲基酶rmtB,與NDM-1相比,NDM-5有2個氨基酸替代(Val88Leu和Met154Leu)對碳青霉烯類和擴譜頭孢菌素具有更強的耐藥性。BAHMANI等[34]的一項回顧性研究發現在收集的400份臨床標本中,鑒定出114株KP,28個(24.6%)分離株對亞胺培南具有抗性,而其中15個(53.6%)分離株的MBLs酶生產呈陽性,PCR結果顯示,blaNDM-1、blaVIM-1和blaIMP-1基因的頻率分別為10(66.7%)、4(26.7%)和1(6.7%)。
3.3 產OXA-48酶
產生OXA-48的CRKP主要在土耳其、北非和歐洲流行,而它們的衍生物OXA-181在印度次大陸較常見[33]。OXA-48可以水解苯唑西林和青霉素類抗生素,還能夠抵抗β-內酰胺酶抑制劑的抑制作用[35],OXA-48基因的傳播與INCL質粒上的Tn1999轉座子相關,攜帶有blaOXA-48的INCL質粒(pOXA-48a)是高度可傳播的,其轉移頻率比帶有blaNDM-1的INCL質粒(pNDM-OM)的轉移頻率高50倍[36],OXA-48可被頭孢他啶/阿維巴坦抑制,因為該酶不能水解頭孢他啶[37]。
3.4 耐黏菌素CRKP
黏菌素分為多黏菌素B和多黏菌素E兩類,均為多肽類抗生素,均為濃度依賴性快速殺菌劑,通過改變細菌細胞膜通透性導致細菌死亡,對革蘭陰性菌如大多數腸桿菌科、鮑曼不動桿菌和銅綠假單胞菌等有靶向活性,CRKP在體外對于多黏菌素B仍是最敏感的[6],多黏菌素E敏感率為80.62%[38],其次是替加環素,但是隨著多黏菌素、替加環素等抗菌藥物的使用,耐多黏菌素、耐替加環素和頭孢他啶-阿維巴坦耐藥的CRKP相繼出現,給臨床治療帶來巨大挑戰。NGUYEN等[13]通過調查越南胡志明市一家醫院爆發的兩起高死亡率院內疫情,發現了具有碳青霉烯類和黏菌素耐藥性的CRKP,黏菌素耐藥的主要機制包括由pmrA/B、PhoQ/P和crrA/B等雙組分系統(two-component systems,TCS)突變引起的細菌內毒素的改變,以及mgrB基因(TCS調節器)的突變或中斷,導致黏菌素耐藥性激活。同樣,NISHIDA等[39]在日本發現的一株泛耐藥CRKP對廣譜頭孢菌素、碳青霉烯類、氨基糖苷類、氯霉素、磷霉素、氟喹諾酮類、多黏菌素、四環素和磺胺甲惡唑均耐藥,通過探尋其耐藥機制發現黏菌素耐藥性與調節Phop/PhoQ的mgrB基因突變有關。HUANG等[40]的研究也發現質粒IS介導的mgrB基因突變是黏菌素耐藥的主要機制,而黏菌素暴露是黏菌素耐藥的唯一獨立危險因素。
3.5 耐替加環素CRKP
替加環素屬于新一代四環素類衍生抗生素,通過可逆結合細菌核糖體30s 亞基,阻斷tRNA進入核糖體A位點,從而抑制細菌蛋白質的合成,由于其單獨使用極易產生耐藥且其在血液和尿液中藥物濃度較低,因此,有研究表明替加環素應采用聯合用藥且不應單藥治療嚴重的血液感染和尿路感染[41]。替加環素在CRKP中仍相對敏感,耐藥率大多<10%,但隨著產生超廣譜β-內酰胺酶(ESBL)和多重耐藥(multi-drug resistance,MDR)CRKP的出現,替加環素的耐藥性也逐漸升高。YANG等[42]從9所醫院的血液感染患者中分離出耐替加環素CRKP,均為ST11-KP-2-CRKP,發現ISKpn26在耐替加環素分離株中廣泛阻斷acrR,導致AcrAB-Tolc外排泵激活,通過外排泵的主動外排作用將藥物排出細菌體外,從而降低了對替加環素的敏感性。還有研究發現耐替加環素CRKP的耐藥機制主要通過RND轉運蛋白和AcrAB外排泵發揮作用[43],同時質粒攜帶的tet(A)突變基因和rpsJ突變基因,也會導致替加環素不敏感[44]。
3.6 耐孢他啶/阿維巴坦CRKP
β-內酰胺酶抑制劑通過促進酶的水解發揮抗菌藥物活性,主要包括克拉維酸、舒巴坦和他唑巴坦以及新型β-內酰胺酶抑制劑阿維巴坦,可以與其他抗菌藥物制成復方制劑,如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哌拉西林/舒巴坦、頭孢哌酮/舒巴坦和頭孢他啶/阿維巴坦等。隨著抗生素的大量使用,近幾年有大量關于耐頭孢他啶/阿維巴坦CRKP的報道。ZHANG等[45]收集了872株CRKP,其中頭孢他啶/阿維巴坦的耐藥率為3.7%(32/872),研究發現MBLs的產生、blaKPC-2點突變和KPC的高表達是其主要耐藥機制。VENDITTI等[46]發現26株對頭孢他啶/阿維巴坦耐藥的KP,其中有14株同時對頭孢他啶/阿維巴坦和碳青霉烯類抗生素耐藥,blaKPC基因的突變,特別是KPC酶的omega環和兩個熱點突變區的突變是其耐藥的主要原因,另外還有研究指出OmpK35孔蛋白缺乏可以增加頭孢他啶水解率,從而增加其耐藥性[47]。
3.7 CR-HvKP
超強毒力相關基因通常編碼在毒力質粒上,也可以作為整合子結合元件的一部分在染色體中編碼,毒力基因包括rmpA/rmpA2(與高粘性表型有關)、iroBCDN、iuta、iuacABCD、ybt基因(編碼多個鐵載體及其受體)和clb基因(編碼粘連蛋白基因毒素)[18]。HvKP通常對碳青霉烯類抗生素敏感,然而FENG等[48]表明有ST11序列CRKP通過獲得類似pLVPK的毒力質粒來獲得超強毒力,GU等[49]的研究也發現典型的CRKP獲得了一個約170kbp的pLVPK毒力質粒,從而變成耐碳青霉烯類超強毒力肺炎克雷伯菌(CR-HvKP)。AHMED等[50]在埃及一名60歲ICU住院女性患者的血液中分離出了CRHvKP株,其同時具有攜帶blaNDM-1和超強毒力基因的新型雜交質粒與攜帶blaKPC-2的質粒,綜上所述,碳青霉烯耐藥和超強毒力的結合極大地影響了抗菌劑的選擇,給臨床治療、感染控制和公共衛生帶來嚴峻挑戰。
4 CPKP的診療進展
目前,CRKP 的治療措施比較局限,初期抗感染治療尤為重要,可影響預后,應遵循早期、足量的原則。治療分單藥和聯合抗感染治療,有多項研究表明,聯合抗感染治療療效優于單藥治療。常用的藥物有多黏菌素、替加環素、β-內酰胺酶抑制劑、磷霉素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新型藥物如頭孢他啶—阿維巴坦、碳青霉烯類—新型酶抑制劑等。
單獨使用多黏菌素易產生異質性耐藥,故推薦與碳青霉烯類、替加環素、磷霉素、利福平等抗菌藥物聯合用藥,有協同抗菌作用。有研究[51]報道,多黏菌素B與美羅培南或利福平聯用在體外對CRKP表現為協同和相加抗菌作用。在無嚴重藥物副作用或肝腎功能不全的情況下,對于嚴重感染建議使用高劑量替加環素的聯合治療[41],GENG等[52]的一項臨床試驗,將40名ICU收治的CRKP患者分為2組,一組給予高劑量替加環素(200 mg負荷劑量,隨后每12 h服用100 mg),另一組給予標準計量(100 mg負荷劑量,然后每12 h服用50 mg),結果發現高劑量替加環素治療方案與CRKP感染患者的生存時間延長和死亡率降低有關。頭孢他啶-阿維巴坦由于其強大的體外活性、低毒性和優于傳統治療方案的臨床優勢,已成為美國產生KPC的CRE的首選治療方法,但單一治療可能導致攜帶KPC基因的CRKP產生耐藥性。ZHANG等[53]通過體內體外試驗發現頭孢他啶-阿維巴坦對產KPC-2和OXA-232的CRKP有明顯的殺菌作用,與氨曲南聯用時,對產NDM的CRKP也有較強的協同殺菌作用,同樣,PRAGASAM等[54]也證明頭孢他啶-阿維巴坦與氨曲南聯用對于產NDM及OXA-48的CRKP抑制作用明顯升高。另外有研究[55]發現,孢他啶-阿維巴坦與碳青霉烯類抗生素聯用有協同作用,可以用于嚴重CRKP感染,特別是對于頭孢他啶/阿維巴坦最低抑菌濃度(MIC)接近敏感點的分離株,然而還有一些研究[56]證明頭孢他啶/阿維巴坦與多黏菌素聯用并不能提高體內外抗菌活性及生存率。OJDANA等[57]發現頭孢他啶-阿維巴坦與磷霉素聯合對產NDM的CRKP協同作用最強,頭孢他啶-阿維巴坦與厄他培南的聯合對產KPC的CRKP協同作用最強,此外,頭孢他啶-阿維巴坦與厄他培南、頭孢他啶-阿維巴坦與替加環素的聯合用藥能使所有產KPC和OXA-48肺炎克雷伯菌的MIC降至敏感點以下。BARNES等[58]的試驗證明那庫巴坦-美羅培南聯合治療對產KPC-2和KPC-3的CRKP有效。ZHAO等[59]則發現卡托普利可以增強美羅培南的活性,并恢復其對產MBLs的CRKP的療效。Erdem等[60]通過聯合用藥試驗發現雙碳青霉烯類抗生素與多黏菌素聯合應用可能是治療多黏菌素和碳青霉烯耐藥肺炎克雷伯菌的一種有潛力的選擇。最近,還有研究發現針對ST258膠囊多糖的兔抗體顯著增強了人血清的殺菌活性,并促進了人中性粒細胞對這種病原體的吞噬和殺滅,即開發一種針對CRKP感染的免疫療法(疫苗)是可行的[27]。
5 小結
全球范圍內CRKP的檢出率明顯升高,且耐藥情況顯著,醫院院內感染的控制以及CRKP的篩查需要得到加強,還應重視控制患者住院期間的CRKP獲得性感染,尤其是免疫力低下、較危重患者及COVID-19患者,新型抗菌藥物的研發也迫在眉睫,現有治療藥物如多黏菌素及替加環素的實驗室及臨床試驗數據仍不夠充分,在明確多黏菌素及替加環素的最佳給藥方式及治療模式上仍需進一步研究。